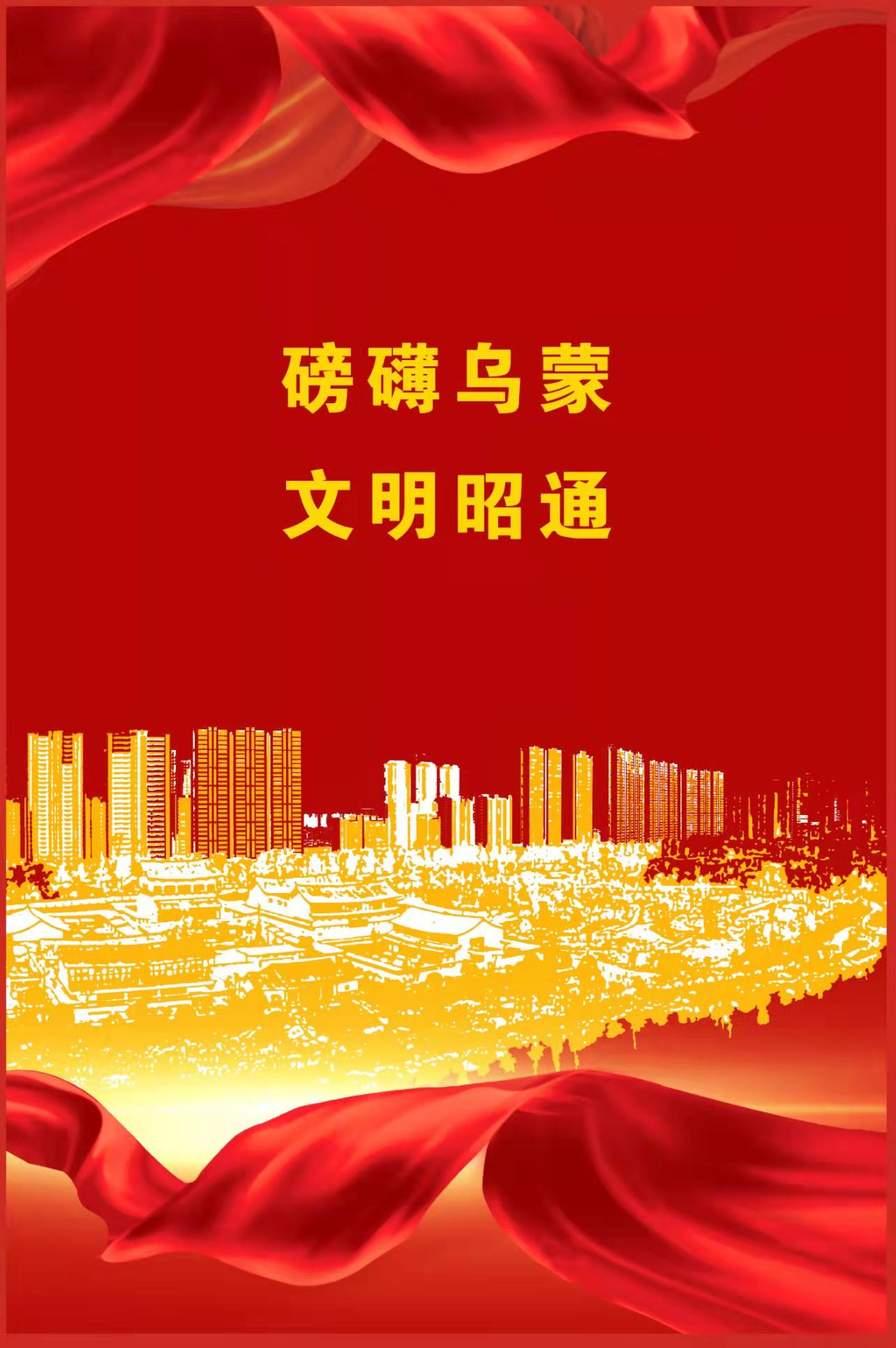2023-06-25 10:53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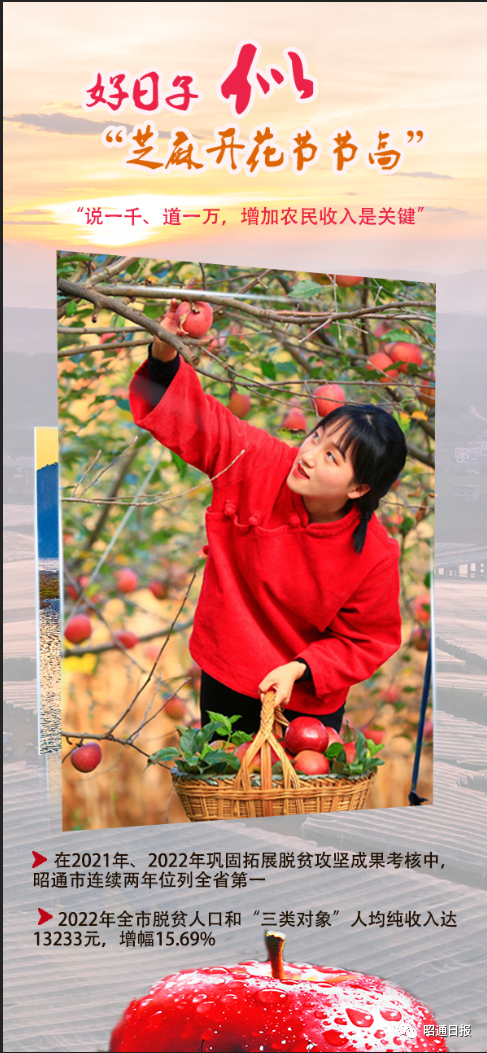
海報設(shè)計:劉仕川 黃山敏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出務(wù)工是昭通農(nóng)村年輕人的一種生存方式,他們?nèi)缤昂蝤B”一樣,在務(wù)工地和鄉(xiāng)村往返。
昭通市威信縣雙河苗族彝族鄉(xiāng)半河村垕房村民小組的陶曉旭就是這樣一只“候鳥”。
2008年,陶曉旭高中畢業(yè),選擇了離鄉(xiāng)外出打工,這一去就是10年。“幾乎每年都回來過春節(jié),然后又走。”往返之間,陶曉旭并未意識到,戀鄉(xiāng)情結(jié)已經(jīng)固化下來。
2017年,脫貧攻堅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陶曉旭看到垕房發(fā)生的變化,萌發(fā)了回鄉(xiāng)的想法,最后在雙河鄉(xiāng)集市上開了一家小吃店,得以近距離地感受垕房的變化。
2019年,陶曉旭報名參加了半河村村民委員會選舉,成為一名村委委員,他見證了脫貧攻堅帶來的巨變,他認識到鄉(xiāng)村變化與國家政策息息相關(guān)。
2022年初,垕房被列為鄉(xiāng)村振興示范點建設(shè)。“因為他是垕房人,也善于做村民工作,村上派他聯(lián)系垕房工作。”陶曉旭不負眾望,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不遺余力地推動鄉(xiāng)村振興示范點建設(shè)工作,也為自己回到垕房找到了答案。陶曉旭說:“村里的年輕人重復(fù)著我走過的路,要吸引他們回來,把垕房建設(shè)得更好。”
在現(xiàn)代詩人余光中看來,鄉(xiāng)愁是郵票、船票以及海峽,但對于苗族青年陶曉旭來說,鄉(xiāng)愁是古宅、蘆笙舞以及蠟染,甚至是少年離開垕房之前那一條可以走出村莊的坑坑洼洼的山路。
如今,這條坑坑洼洼的山路不經(jīng)意間變成了平整的柏油路。
2008年,陶曉旭高考落榜,像村里的大部分年輕人一樣,他選擇外出務(wù)工,來到江蘇常州一家三輪車制造廠做焊工。
學(xué)歷不高,沒有技術(shù),焊工這一職業(yè)并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樣,帶來自己想要的收入。兩年之后,不甘于一輩子做焊工的陶曉旭和朋友一起承包工程做鋼筋工,先后輾轉(zhuǎn)于江西、廣東、浙江、內(nèi)蒙古等地。正是這些漂泊的日子,喚起了他對垕房的思念。“有一年我一個人在江蘇過年,從微信朋友圈看到老家花山節(jié)熱鬧的場景,那時,特別地想家。”陶曉旭說。
從那一刻開始,陶曉旭反復(fù)問自己,何時才能結(jié)束漂泊的日子?回家的想法開始萌芽。

2017年,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推進,垕房泥濘坑洼的土路變成了寬闊平整的水泥路,破舊的瓦房經(jīng)過加固、重建后,變成另外一種新面貌。和威信縣革命老區(qū)的其他地方一樣,垕房村民正在向“吃不飽穿不暖”的時代告別。
時代的變化給陶曉旭帶來了驚喜,他從逐漸變好的鄉(xiāng)村看到了商機。于是,他選擇在雙河鄉(xiāng)集鎮(zhèn)上開了一家小吃店。
來來往往的食客多數(shù)是本鄉(xiāng)本土的人,閑暇之余,陶曉旭會和他們聊聊垕房的變化和未來發(fā)展,甚至在腦海中會冒出“規(guī)劃”這一詞語。
“這一段時間,我一有機會就近距離觀察家鄉(xiāng),思考垕房發(fā)展,萌發(fā)了想為家鄉(xiāng)做點事的想法。”但現(xiàn)實并未讓陶曉旭的想法落地。后來因為家庭原因,他又到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開了一家云南風(fēng)味的米線店。2019年,受各種因素影響,米線店以關(guān)門告終,他也真正回到了垕房。
從打工者到包工頭、餐飲老板,陶曉旭在求變的人生歷程中學(xué)會了堅韌也懂得了變通。他說:“我沒有積攢到財富,但我積累了人生閱歷,知道怎么去理解一件事,并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回到家鄉(xiāng)后,恰逢村委會換屆選舉,陶曉旭當(dāng)選為村委委員,為家鄉(xiāng)發(fā)展做點事的想法有了坐標。
距離陶曉旭家不到50米的地方,是建于清末1901年的垕房陶氏老宅,依山而建的垕房陶氏老宅是一座由石頭構(gòu)建而成的城堡。進入城堡的大門由石條砌成,四合天井全用巨石鋪筑,老宅背后的堡坎也是用石頭砌成。

有120多年歷史的垕房陶氏老宅,在鄉(xiāng)村振興示范點打造的政策背景下得以修繕,城墻、照壁、窗雕經(jīng)過修復(fù)重現(xiàn)了昔日的輝煌,而房檐滴水把四合院石板砸出的一個個深坑則訴說著歷史的滄桑。
在鄉(xiāng)村振興示范點打造的過程中,無論是作為垕房村民還是村委委員,陶曉旭很清楚,垕房只是一個示范,最終還是要由村民自己來管理,“把垕房建好,讓村民意識到,不是到外邊務(wù)工才有機會和出路。”陶曉旭說。
陶曉旭注冊成立了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專業(yè)合作社,鄉(xiāng)村振興示范點核心區(qū)的75戶農(nóng)戶參與合作社運營。
“單打獨斗的方式已經(jīng)過時了,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抱團,尤其是在經(jīng)濟基礎(chǔ)比較薄弱、觀念比較落后的地方。”陶曉旭說。他期盼著更多的年輕人回到垕房,只有年輕人回到鄉(xiāng)村才能釋放鄉(xiāng)村動能。
“讓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在家鄉(xiāng)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賺更多的錢。”這是陶曉旭對鄉(xiāng)村振興的理解,共同致富已經(jīng)成為他返回垕房要擔(dān)起來的責(zé)任。
在陶曉旭的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專業(yè)合作社打出生態(tài)牌之后,有沒有其他年輕人回到垕房,將技能和運營結(jié)合在一起,打一張民族文化牌?

2023年暮春時節(jié),陶曉旭離開又回來的垕房開滿了油菜花,這片土地也在等待著游子歸家,把鄉(xiāng)村顏值轉(zhuǎn)換為經(jīng)濟價值。
 昭通日報記者:汪舒
昭通日報記者:汪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