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2 11:05 來(lái)源:學(xué)習(xí)時(shí)報(bà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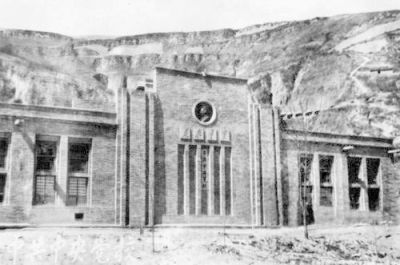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guò)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深化黨和國(guó)家機(jī)構(gòu)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guó)家機(jī)構(gòu)改革方案》。時(shí)代雖然不同,但今天重溫延安時(shí)期的精兵簡(jiǎn)政,對(duì)于我們做好這項(xiàng)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編 者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qū)二屆一次參議會(huì)期間,毛澤東把一份提案整個(gè)抄到了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還用紅筆圈起來(lái),并且加了一段批語(yǔ):“這個(gè)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jī)關(guān)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duì)癥藥。”毛澤東所說(shuō)的這個(gè)“對(duì)癥藥”,就是精兵簡(jiǎn)政。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qǐng)?bào)》寫(xiě)的社論中也說(shuō):“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jiǎn)政的政策,是一個(gè)極其重要的政策。”
?“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0年和1941年,各個(gè)抗日根據(jù)地遭遇到空前的物質(zhì)困難。正如毛澤東所說(shuō):“我們?cè)?jīng)弄到幾乎沒(méi)有衣穿,沒(méi)有油吃,沒(méi)有紙,沒(méi)有菜,戰(zhàn)士沒(méi)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méi)有被蓋。國(guó)民黨用停發(fā)經(jīng)費(fèi)和經(jīng)濟(jì)封鎖來(lái)對(duì)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陜甘寧邊區(qū)出現(xiàn)這樣的困難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個(gè)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脫產(chǎn)人員大量增加。1937年陜甘寧邊區(qū)成立時(shí),黨政軍脫產(chǎn)人員僅1.4萬(wàn)人,1938年亦僅1.6萬(wàn)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國(guó)民黨發(fā)動(dòng)兩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圍邊區(qū),并伺機(jī)大舉進(jìn)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被迫從前線(xiàn)陸續(xù)調(diào)回軍隊(duì),保衛(wèi)邊區(qū),導(dǎo)致脫產(chǎn)人員(主要是軍隊(duì))從1939年起直線(xiàn)上升。1941年邊區(qū)脫產(chǎn)人員達(dá)到7.3萬(wàn)人。脫產(chǎn)人員猛增,邊區(qū)財(cái)政支出隨之大幅增加。
第二,陜甘寧邊區(qū)財(cái)政收入銳減。當(dāng)時(shí)陜甘寧邊區(qū)財(cái)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外援主要包括海外華僑的捐款、國(guó)內(nèi)民主人士和抗日?qǐng)F(tuán)體的捐助,以及國(guó)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等。外援在邊區(qū)的財(cái)政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據(jù)統(tǒng)計(jì),外援在財(cái)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38年為51.6%,1939年為85.79%,1940年為74.7%。但是從1940年10月起,國(guó)民黨停發(fā)了八路軍的軍餉,同時(shí)對(duì)邊區(qū)實(shí)行斷郵,國(guó)民黨對(duì)邊區(qū)的這種封鎖政策,造成在當(dāng)時(shí)環(huán)境下外援的大部斷絕,邊區(qū)財(cái)政極度困難。
第三,人民負(fù)擔(dān)加重。中央曾經(jīng)規(guī)定,黨政軍脫產(chǎn)人員不能超過(guò)人口總數(shù)的3%,但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已經(jīng)達(dá)到了5.4%,這樣勢(shì)必會(huì)增加人民的負(fù)擔(dān)。以人民的公糧負(fù)擔(dān)為例,從1939年的5萬(wàn)石劇增至1941年的20萬(wàn)石。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qū)召開(kāi)縣長(zhǎng)聯(lián)席會(huì)議討論征糧問(wèn)題。突然天下大雨,電閃雷鳴,延川縣一位姓李的代縣長(zhǎng)遭雷擊身亡。同時(shí),一位農(nóng)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這個(gè)農(nóng)民逢人便說(shuō):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個(gè)農(nóng)民的話(huà)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毛澤東后來(lái)曾說(shuō):“那年邊區(qū)政府開(kāi)會(huì)時(shí)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zhǎng)打死了,有人就說(shuō),哎呀,雷公為什么沒(méi)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diào)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gè),就是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shí)確實(shí)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如何克服困難呢?當(dāng)時(shí)的辦法之一是開(kāi)展以農(nóng)業(yè)為中心的大生產(chǎn)運(yùn)動(dòng),另一個(gè)辦法就是實(shí)行精兵簡(jiǎn)政。1941年11、12月間,陜甘寧邊區(qū)召開(kāi)第二屆參議會(huì),李鼎銘等11人提出了精兵簡(jiǎn)政的議案。這個(gè)議案經(jīng)過(guò)參議會(huì)討論通過(guò),迅速實(shí)施。正如毛澤東所說(shuō):“我們必須克服這個(gè)困難,我們的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jiǎn)政。”
精兵簡(jiǎn)政“必須是嚴(yán)格的、徹底的、普遍的”
邊區(qū)參議會(huì)結(jié)束后不久,194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為實(shí)行精兵簡(jiǎn)政給各縣的指示信》,要求切實(shí)整頓黨、政、軍各級(jí)組織機(jī)構(gòu),精簡(jiǎn)機(jī)關(guān),充實(shí)連隊(duì),加強(qiáng)基層,提高效能,節(jié)約人力物力。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邊區(qū)進(jìn)行了三次精兵簡(jiǎn)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941年12月中旬,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根據(jù)中央的指示擬定整編方案,開(kāi)始了第一次精兵簡(jiǎn)政,到1942年4月基本結(jié)束。經(jīng)過(guò)精簡(jiǎn)裁減掉了駢枝機(jī)構(gòu)百余處,縮減了工作人員數(shù)千名,收獲很大。但是由于缺乏經(jīng)驗(yàn),對(duì)精簡(jiǎn)工作的重要性也認(rèn)識(shí)不足,在思想認(rèn)識(shí)上提高不多,工作整體上改進(jìn)不明顯。
為此,1942年6月30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務(wù)會(huì)議討論通過(guò)《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系統(tǒng)第二次精兵簡(jiǎn)政方案》,第二次精兵簡(jiǎn)政開(kāi)始。這次精簡(jiǎn)工作的重點(diǎn)是建立邊區(qū)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上級(jí)機(jī)關(guān)也精簡(jiǎn)了一些人員,但又都充實(shí)進(jìn)了基層組織,實(shí)際精簡(jiǎn)幅度不大。到1942年9月,第二次精簡(jiǎn)結(jié)束。在兩次精簡(jiǎn)的基礎(chǔ)上,陜甘寧邊區(qū)根據(jù)中央指示準(zhǔn)備進(jìn)行第三次精簡(jiǎn)并做了比較充分的準(zhǔn)備。
1942年9月中旬,陜甘寧邊區(qū)組織人員對(duì)之前的精簡(jiǎn)工作進(jìn)行了認(rèn)真檢查。這次檢查工作實(shí)際上是總結(jié)第一、二次精簡(jiǎn)工作的經(jīng)驗(yàn),發(fā)現(xiàn)工作中存在的問(wèn)題,為第三次精兵簡(jiǎn)政工作做思想準(zhǔn)備和組織準(zhǔn)備。在此基礎(chǔ)上,1942年9月下旬,陜甘寧邊區(qū)專(zhuān)門(mén)召集分區(qū)專(zhuān)員,延安、安塞、甘泉等縣縣長(zhǎng),以及其他一部分縣、區(qū)、鄉(xiāng)干部,舉行簡(jiǎn)政座談會(huì)。這次座談會(huì)后,大家從思想上對(duì)精兵簡(jiǎn)政工作進(jìn)一步提高了認(rèn)識(shí)。
毛澤東對(duì)精兵簡(jiǎn)政工作一直非常關(guān)注。1942年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干會(huì)議上作了《經(jīng)濟(jì)問(wèn)題與財(cái)政問(wèn)題》的著名報(bào)告,其中再次提到精兵簡(jiǎn)政。他說(shuō),這次高干會(huì)以后,“我們就要實(shí)行‘精兵簡(jiǎn)政’。這一次精兵簡(jiǎn)政,必須是嚴(yán)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jiǎn)政中,必須達(dá)到精簡(jiǎn)、統(tǒng)一、效能、節(jié)約和反對(duì)官僚主義五項(xiàng)目的”。毛澤東的講話(huà)既指出了過(guò)去精簡(jiǎn)工作的不足,也對(duì)今后的精簡(jiǎn)工作提出了期望,極大地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對(duì)精兵簡(jiǎn)政工作的意義、目的和要求的認(rèn)識(shí)。
“對(duì)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延安時(shí)期,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通過(guò)精兵簡(jiǎn)政,克服了機(jī)關(guān)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提高了生產(chǎn)生活水平,度過(guò)了最困難的時(shí)期,這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奪取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乃至奪取解放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后來(lái)提到精兵簡(jiǎn)政這項(xiàng)政策時(shí)曾說(shuō):“‘精兵簡(jiǎn)政’這一條意見(jiàn),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lái)的;他提得好,對(duì)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
但是這一過(guò)程是不易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延安時(shí)期的精兵簡(jiǎn)政進(jìn)行了三次,將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當(dāng)時(shí)的主要任務(wù)上,才最終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這就告訴我們做事情要有中心,工作要有輕重緩急。如果分不清主次,必然手忙腳亂。同時(shí)也告訴我們,精兵簡(jiǎn)政既是一項(xiàng)臨時(shí)性工作,又是一項(xiàng)經(jīng)常性工作。所謂臨時(shí)性工作就是按照計(jì)劃在一定時(shí)間內(nèi)完成精兵簡(jiǎn)政的任務(wù)。所謂經(jīng)常性工作就是要把精兵簡(jiǎn)政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貫徹始終。不然就會(huì)出現(xiàn)一次精簡(jiǎn)過(guò)后,時(shí)過(guò)境遷,死灰復(fù)燃,導(dǎo)致精簡(jiǎn)的成果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