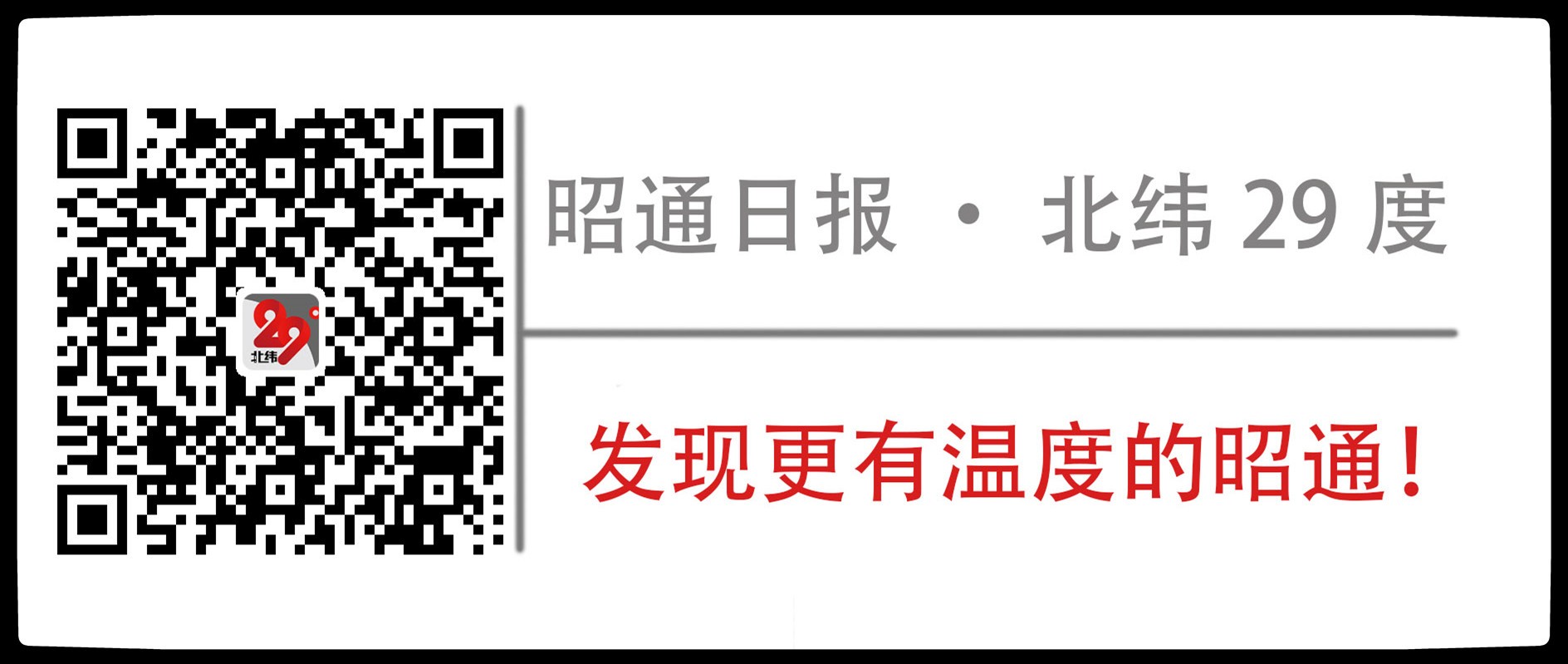2019-09-12 09:10 來源:昭通新聞網

?——關于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
阿卓務林
寫 詩
竊以為,上半生最美好的一件事,便是寫詩。詩歌之美,無與倫比,沒有再比“詩人”這個稱謂更悅耳、更美妙、更神圣的詞了。
1984年9月我上學,從此與高深莫測的漢語結下了不解之緣。漢語真是玄妙,它比舌尖還靈活,怎么說都合適,只要你會說。一個意思可以有無數種表達,太神奇了。
1992年春天,因患感冒就“收走”了父親苦難的一生。從此,一種莫名的孤獨感如影隨形,至今無法擺脫,這或許是我寫詩的源頭。
1993年9月,我考入云南省水利水電學校,語文老師趙景先生喜歡講解一些名著和佳作,深深被吸引,課余時間著實無聊,只好經常到學校圖書館打發(fā)時間,如饑似渴地讀各種各樣的書。一次偶然機緣,我在學校門口書攤上淘得《吉狄馬加詩選》,詩歌原來可以這樣寫,深深地被震撼。這部詩集的封面也特別精致,系彝族畢摩神圖,至今縈繞腦海。它是我讀過的書中最美的書之一。
1995年,我開始涂鴉,并走上了一條視詩歌為生命的道路。1997年9月,我參加工作,斷斷續(xù)續(xù)寫下所見所聞所憶所思所想所悟。1998年,《涼山文學》發(fā)表我的處女作《我的父親》,至今已有21年。
詩歌,是我摩挲傷口的避風港,也是我踽踽獨行的指路經。說風流,隨人流,觀花開,觀云散,悠然自得,不亦樂乎。常常,我也會作一次次洄游,向童年,向故鄉(xiāng),有人認為這些詩妙不可言,我等閑視之。
20多年了,至今筆耕不輟,是因為我真的喜歡漢語,喜歡詩歌。我一直有個愿望,就是把自己最喜歡的作品集結出版,有個小結。幸運的是,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前幾日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一樁心愿。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既有舊作,也有新篇,是我20余年詩歌創(chuàng)作的精華,半生的收獲,它基本涵蓋了我的三個創(chuàng)作領域。
我曾出版過兩部詩集,《耳朵里的天堂》和《涼山雪》,都很粗糙,時時窩火。《耳朵里的天堂》,出得匆促,甚至來不及校對,很遺憾;《涼山雪》,編排像是內部出版物,慘不忍睹。它們遮蔽了詞語閃熠的尾翼,遮蔽了意旨翻飛的翅膀。也好,不罷休,寫下去。從某種層面而言,《飛越群山的翅膀》,是我第一部可以謂之曰詩集的詩集。
故 鄉(xiāng)
我于1976年出生在川滇交界處一個叫大觀坪的彝家山寨,大概出生于蕎麥飄香的秋收時節(jié),生日已被父母遺忘。生在寧蒗,其實很幸運;身為彝人,心懷感恩。
我的寧蒗,地處滇西北高原橫斷山脈中段,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的寧蒗,風景迷人,密不透風的萬格梁子,藍得沒有雜質的瀘沽湖水,鬼斧神工的石佛山,天宮瑤池青龍海……我的寧蒗,民族風情獨特而濃郁,彝族十月太陽歷、畢摩文化、摩梭人母系大家庭、“阿夏”婚姻習俗、達巴文化、普米族韓規(guī)文化、傈僳族尼扒文化……
我的寧蒗太為蒼涼了,蒼涼得富有詩意,就連它的名字,也叫小涼山。我那些早不見晚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同胞,太為源遠流長了,就連他們的對話,也用諺語和格言,哪怕是一匹馬、一頭牛、一只綿羊、一條獵狗,都有無數關于它們的神話傳說,哪怕是村莊的一只公雞、山坡上被風吹歪了的一棵老樹、節(jié)日里照亮夜空的一枝火把,都有美好的弦外之音。歡樂的節(jié)日、憂傷的葬禮,身上穿的衣服、生活用的工具,都有深厚的文化內涵。男人盤在頭頂的天菩薩、女人刺在手臂上的梅花紋,為頸項鼓勁的領牌、為耳朵提神的珠璣,都在給人以詩性的召喚。
我的寧蒗啊,盡管它是那么蒼涼,但它的山,有山的雄偉;它的水,有水的靈秀;它的天空,也有天空的質感。說耳濡目染也好,說境域熏陶也罷,所有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和見聞的一部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我比別人收獲更多的寧靜,擁有更多的祥和,就算僅僅以一名翻譯者的身份去詮釋,也足以花費我一生的時間。
彝 人
我的民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無論婚喪嫁娶,迎來送往,或是祭祀慶典,無論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或是愛恨情仇,他們都會創(chuàng)作發(fā)自肺腑的歌舞,以表達自己的記憶和情感。我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知道他們的心思和想法,知道他們的快樂和痛苦,知道他們翻江倒海的內心,知道他們深藏苦汁的靈魂。
我的民族也是個害羞的民族,他們不善于傾訴,不善于與人對話或辯解,他們喜歡默默地與內心深處的“另一個自己”,展開誠摯的暢談和交流。這與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有關,或與他們的集體記憶有關,無從而知,也無法明了。他們從不怨天尤人,也從不憤世嫉俗,他們樂于助人并以此為榮,廣施善行并以此為耀。他們疼愛腳下的每一寸土地,憐憫身邊的每一個物種,善待山上的每一塊巖石,認為“萬物有靈,不得莫名傷害。”從這片土地上,我學會了一種叫做愛的東西。
父輩們一直認為,每個人內心深處都住著一個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精靈,他們常常告誡我:“不要驚嚇吉耳,不要鞭撻吉耳,不要辱蔑吉耳。” “吉耳”是彝語,意譯就是“靈魂”“另一個自己”的意思。他們說一旦“吉耳”失魄,便會慌不擇路,迅即消失,待你策馬追悔,已是無力回天。老人們還說,靈魂一旦逝去,肉體的呼吸也將隨之停止,生命之河就會隨之凝凍。我知道老人們的這些說法全屬迷信,不足為憑,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曾是我從小接受并深信不疑的一部分,已經在我記憶中留下了無法拭去的印痕。
思 想
在這個世上,我們應該承認,大多數人是有詩心感受力的,他們有自己的主見,有積極向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詩人與他們的區(qū)別,僅僅是能夠寫出來而已。
顯然,語言是思想表達最重要的途徑。對于寫詩人而言,語言就是獵人的馬刀、戰(zhàn)士的槍彈,是飛禽的翅膀、走獸的眼睛。如果對寫詩人需要提一個關于語言方面的要求,我想,是可以用“精確”這個詞來約束的。離開了精確,意象就會變質,指向就會紊亂,思想就會歪曲。
思想,當然也包括靈感,在大腦一閃而過乃至成型之后,重要的或許不再是思想是否恢弘,觀點是否新穎,重要的是意思表達是否精確。當然了,一語雙關、寓意深刻、余味無窮等等,與語言精確與否,則是兩碼子事。
難的是,語言有時確實無法承載我們內心所有的情感、思維和秘密,我們永遠也無法把內心波動毫無保留、沒有差錯地表達出來,包括神靈附體后的想象,包括閉目冥思后的頓悟,我們能否精確地予以表達、傾訴,的確是個大問題。
我們也應該承認,相同的原始材料,經過不同工匠的“雕刻”之后,生產出來的“作品”定然也會迥然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別。技巧的至關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容質疑。
技巧無疑是為了表達某種思想、借助語言這個工具橫沖直撞的一種手藝。但詩歌不僅僅是到技巧為止,技巧也絕對不可能是詩歌的目的,它僅僅是到達“彼岸”的手段。對于寫詩人而言,技巧就是獵人的揮舞、戰(zhàn)士的沖鋒,是飛禽的振動、走獸的凝視。我也愿意把技巧比作是串聯(lián)語言之珠的絲線,它能讓散落的珠璣組合成迷人的圖案,散發(fā)出奪目耀眼的光彩。
如果從形式上拷問,或許我們還可以這樣說,詩歌的形式大多是由內容決定的。當一件作品在大腦成型之后,它的大致輪廓無疑也是相應地一同成型了的。如果用拔高一點的說法,那就是:每一首詩,它都純屬天意。只要是能夠感動人的方式,它必然也是適宜的、恰當的方式。當然了,除了感動人,如果還能感染人、感化人,則是真的好詩。重要的不是方式,重要的是思想。
詩 歌
眼里所見、耳畔所聞、腦海所憶、心中所思,都是詩歌的源頭。對我而言,有幾個詞顯得特別重要,其中第一個詞是“看見”。我指的“看見”,它是廣義的,包括眼睛所見、心靈所見、夢幻所見、記憶所見。那些被我以不同形式、從不同途徑看見,并感動我的意象和情節(jié),我向來視若貴賓,馬上迎進家門,與之留影并留存下來。寫實手法僅僅是意思表達的一種手段,其實我更傾心于對心靈所見的捕捉。
第二個詞是“感悟”。通過耳聞、手摸、身受得來的體驗,會在不經意間給我以溫暖,對它們我也絲毫不敢怠慢,趕緊走上前去與之熱烈擁抱,唯恐轉瞬即逝。待我轉身,它們往往也會給我以新的啟迪,如果言之“善有善報”,我想也是精當的。
第三個詞是“天意”。我的心越寧靜,我就越能感受到它翅膀的抖動。有的時候,我似乎都觸摸到了它那柔軟的羽毛,聽到了它微微的鼻息。藝術的至高境界,向來就是自然而然、返璞歸真。
當然了,寫一首詩,我們肯定很少考慮詩歌以外的因素。詩作寫出來以后,我也很少按照某個體系進行相應的歸類,很簡單,什么東西迷住了我,我就贊美什么;什么事件感動了我,我就抒寫什么。至于創(chuàng)作理念和追求,則是另一回事。如果非要形容,那么我愿意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翻飛在小涼山的小鳥,虔誠地用憂傷的眼睛閱讀靜謐而滾燙、蒼茫而生機的大地。
使 命
詩歌在我的生活中占據怎樣的分量,我想可以這樣說:我寫詩,是因為悶在心里、不便說出的話,寫出來,既不傷人,也拯救了自己;我寫詩,是因為我的這個嗜好,猶如蜜蜂偏愛鮮花、太陽眷念東山,與生俱來,老也改不了。寫詩,是我拯救內心之苦的一條有效途徑,就如有的人喜歡運動,有的人喜歡旅游,平常而自然,或者純屬是愛好。我不會把詩歌當作一份職業(yè)來經營,寫詩從來也不曾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但詩歌早已演化為我命中注定的宗教,寫詩早已變成我習以為常的習慣,這是我能夠沉潛下心來的原因。
記得詩人孫文濤這樣說過:“詩歌來源于一種空氣、水分和土壤,它的命運也取決于這個特定的環(huán)境。”竊以為,無病呻吟,就是踐踏情感;故弄玄虛,就是浪費時間;矯揉造作,就是欺騙自己;閉門造車,就是摧殘生命。
那么,我要寫什么樣的詩歌呢?我想我應該聽從內心的召喚。因為我無法漠視自己內心的呼喚和吶喊,它們或低沉,或高亢,或激昂,或溫順,或漫不經心,或來勢兇猛地擊打著“另一個自己”。
我也無法漠視每一個生命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無法漠視每一個物種的轉瞬即逝與渺小無助。聆聽他們的心聲,觸摸他們的體溫,凝視他們的舉止,感受他們的呼吸,把生活中聽到的精彩語言記錄下來,把夢想中一閃而過的出格意境敘述出來,把經歷的“旅程”真實地攝制下來,把體會的情感真實地播放出來,把滄桑彝人的快樂與痛苦形象地“翻譯”出來,以無比沉靜的心態(tài)應對風云雷電和時世變遷,這或許也是善待生活、敬畏生命的方式之一,這是我的責任,其實也是很多邊地人的責任。
時 間
誰說這只是美景?此刻一陣風輕輕拂過此棵樹,下一刻,如果另一陣同樣輕微的風輕輕拂過此棵樹,樹的心情會不會同樣愉悅或哀傷?此刻一朵云徐徐滑過此片巖,下一刻,如果另一朵同樣徐緩的云徐徐滑過此片巖,巖的臉色會不會同樣輝煌或黯淡?萬物有靈,萬物皆有生命,只不過形態(tài)萬千、心態(tài)萬千罷了。
誰說這只是人世?此刻一個人讓你感激不盡或仇恨至極,如果我們將心比心,這個人在彼人的眼里,也許沒你想象的那么善或那么惡。換言之,這個人壓根就沒那么善或那么惡。每一個人,都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總有你觸摸不到的秘密。你所感觸的,只不過是你自己的內心。
誰說這只是生活?此刻一件事讓你欣喜萬分或悲痛欲絕,如果我們冷靜下來,這件事在彼時的心境,也許沒你想象的那么好或那么糟。換言之,這件事原本就沒那么好或那么糟。每一件事,都像一場霧,總有你看不見的謎。你所看見的,只不過是事件簡單的經過和結果。
誰說這只是歷史?如果一個物種瀕臨滅絕,生生不息只不過是一句夢的囈語;如果一種文字行將消亡,浩繁經書只不過是一堆紙的碎片。
幸好有的人有思想,有的人有良知,在這個世上;幸好有的人既有思想,又有良知,還有一顆憐憫之心,在這個世上。
時間碎片借此留存千古。
沖 動
上半生,我貌似只寫了一部詩集,就是《飛越群山的翅膀》。說到底,出版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的初衷,也是基于此。我關注吸引我關注的一切動物和植物,它們都是生命,它們都有靈魂,它們堪稱奇跡。從它們身上望過去,我看見它們身后慈母般無私的山和水。山水有情,山水有愛,山水有菩薩,山水有無盡。這些山水背后的人們,他們神色各異,他們各美其美,他們自成一家。他們的風土人情,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的滄桑歷史,值得品嚼,值得回味,值得珍惜;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心靈激蕩,讓人感動,讓人感慨,讓人感悟。我常常有為他們抒情立傳的沖動。
感謝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幸運地入選了2018年首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并于2019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于這部詩集的命運,交由讀者和時間去評說,不過至少有一點我是很欣慰的,詩集里的作品是我半生的精華,是我向小涼山這片土地獻上的誠摯的禮贊,也是我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獻上的誠摯的祝賀。我祈愿“它們可以讓小涼山從無數的山峰中獨立出來,并盡可能地接近蔚藍的天空”。

阿卓務林彝族,1976年生。他參加了詩刊社第23屆“青春詩會”,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獲過云南文藝基金獎、邊疆文學獎、云南日報文學獎等。詩集《飛越群山的翅膀》入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首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叢書。現(xiàn)居云南省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