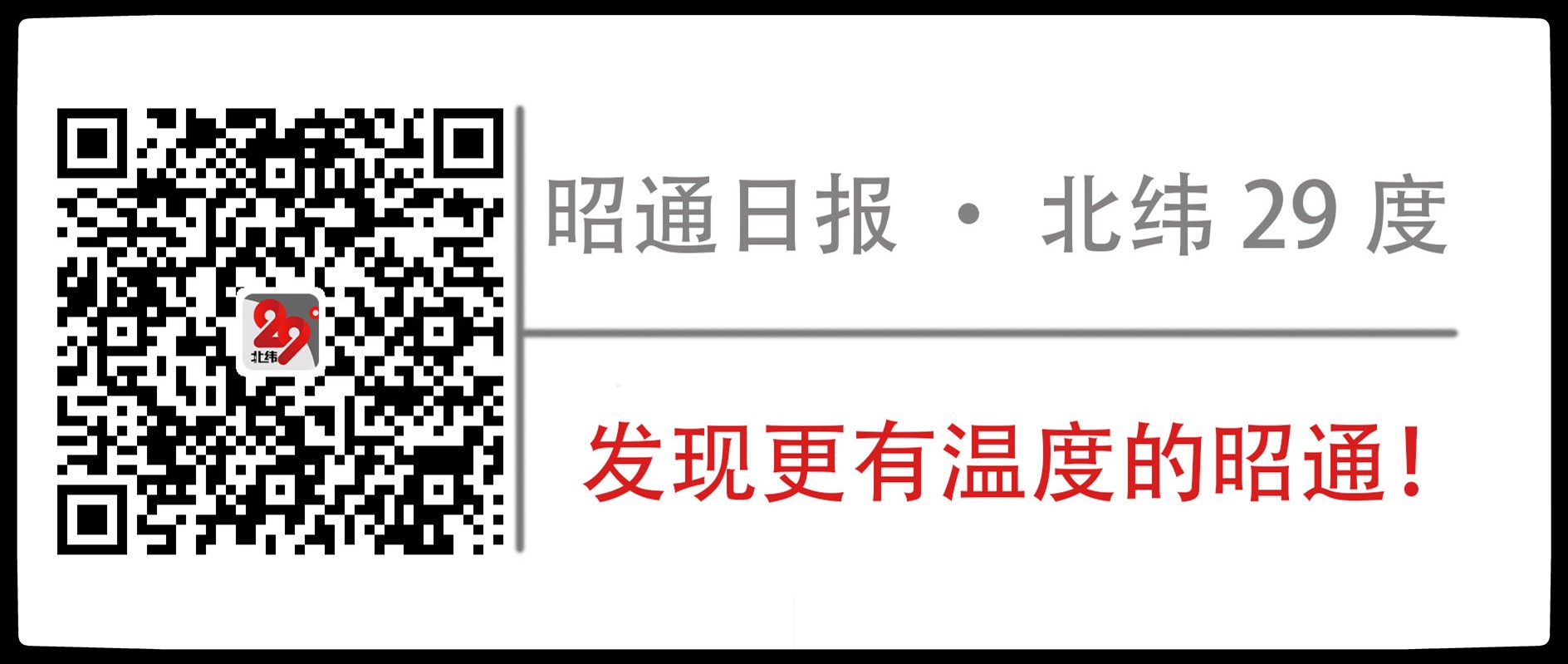2019-10-08 11:23 來源:昭陽融媒
望海樓下千頃池
千頃池是昭通的一個歷史義化符號,可惜未成地理標志。說虛未必實,落實未必虛。曾經(jīng)有好夸口的四川人吹噓家鄉(xiāng)風物,說了句“四川有個蛾眉山,離天只有三尺三”。云南人不甘示弱,就應了句“昭通有座望海樓,半截戳在云里頭。”
我登過峨眉山,所謂三尺三的距離當然是夸張,如同“飛流直下三千尺”的詩化。我也曾上過望海樓,所謂云里頭那半截,其實就是千頃池的記憶。
一樓存滄桑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泛黃的老照片上,可以認識昔日望海樓:一般般,橫看豎看都一般般。不論外觀還是工藝、高度,都缺乏特色。其實這座樓的價值,全在這個獨特的地理位置。
1990年代之前,望海樓的周圍多為良田溝渠、阡陌村莊,后來城市建設(shè)規(guī)劃定格,才進入市區(qū)藍圖,進而圍繞此樓建起了公園。
望海樓當年曾創(chuàng)造了驕傲的紀錄:城市規(guī)劃以它為地標建筑,以其為軸心,因其而改道,并將它原本土頭土腦、破舊不堪的樓體修緝一新,成為歷史上最恒久鮮明的形象標志。這一帶曾經(jīng)有月牙塘做城市之膀胱,后來填了;曾經(jīng)有一尊人們稱為老孔雀的怪異雕塑,后來換了;曾經(jīng)有轅門口的鐵塔想效法艾斐爾,后來拆了;曾經(jīng)有歷史悠久的楊家牌坊,后來倒了;曾經(jīng)有大小石橋的獅子,后來跑了……??唯有望海樓歷經(jīng)滄桑,巋然不動。這可不是樓閣的魅力,全是沾人家千頃池的光。
千頃池是昭通壩子遙遠歷史的水域,究竟是哪個朝代,多寬的水面,有哪些水產(chǎn),皆不詳。曾經(jīng)有好些鄉(xiāng)情濃濃的學者,專心對千頃池歷史地理做過研究探討。但大都不乏想象推測之力,而缺少翔實依據(jù)。有的說可以和滇池媲美,有的夸可以比肩洱海,有的贊可以超過澄江……??
據(jù)說千頃池遺址就在望海樓周圍。曾經(jīng)的浩淼千頃、沙鷗翔集、漁歌互答景象,早已隨池水退去,唯留下一座風雨斑駁的望海樓,做它無言的見證人。
望海樓不僅見證似夢似真的千頃池,還見證了那一帶蒙泉公社鳳凰山下的變遷:那里的良田稻谷飄香,其美味并不遜色于灑漁的木瓜林大米;那里的雙院子曾經(jīng)林木蔥郁,鳥語花香……??突如其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許多喬木都化做小高爐的炭火;起起落落的幾番政治運動,千頃池重孫輩的良田并未創(chuàng)造高產(chǎn)。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望海樓一帶的生產(chǎn)力漸漸活躍,生態(tài)漸漸恢復,農(nóng)民群眾的生產(chǎn)積極性漸漸高漲。1980年代維修望海樓,我曾參加了人代會的討論。
駐足海樓路
昭通城建規(guī)劃幾經(jīng)曲折,重心曾經(jīng)南下,后來又揮師北上。南下時建了條南大街,繼而修了條海樓路,圈了個望海公園。北上更是大手筆,一下子將小水庫省耕塘擴為省耕山水大湖泊……
望海樓已經(jīng)望不到北邊的湖光水色了,因為昭通城的地勢東北高西南低。但望海樓腳下的海樓路,卻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著樓上的眼球。
1980年代討論南大街等建設(shè)項目決策時,爭議的焦點多集中在征地多占良田和排水系統(tǒng)工程上。決策者力排眾議,水田占了就占了,房屋建了就建了,排水堵了便堵了,到而今時光久了就淡了。并且海樓路還得感謝那次的突破,不然海樓路豈能占更多的良田!
海樓路起初是按商業(yè)街市來設(shè)計的。昭通老城工商氣脈東疏西密,北淡南濃,想那規(guī)劃者的潛意識里,也許還想將海樓路建成昭通的南京路呢。
如今的海樓路,商業(yè)氣息并不甚濃厚,飲食文化色彩反而一度豐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是需求關(guān)系加習慣力量的結(jié)果。
十多年前,我還真登上過望海樓呢。
設(shè)計的樓下大道本來筆直如木匠彈的墨線,但因原計劃拆除的望海樓神圣不可撼動:市人代會決議必須保留此樓,于是此道轉(zhuǎn)了個彎,此樓獲得了新生。新生的樓閣一度開放,于是我欣然登上斯樓,試圖尋找一種類似范仲淹《岳陽樓記》那樣的感受。然而,斯樓決無岳陽樓之雄偉和文物積淀,決無洞庭湖那樣壯闊的背景,豈能震撼我心?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登樓之意不在樓。透過“恩波樓”石刻的歷史風霜,透過鳳凰山麓壩子乃至新民壩子滄海桑田的變化,我的眼中唯有你:千頃池。一切全在想象中,但并非一切都是過眼云煙,并非一切都是子虛烏有。
望海樓始建于康熙25年(1760),由恩波縣令沈生遴先生決策,有感皇恩浩蕩、澤社稷黎民之意。千頃池無疑曾經(jīng)波濤滾滾,如今雖然消失,畢竟不是西部樓蘭國那樣沙漠化的毀滅,我們終歸還有另外的青山綠水,終歸還有部分復活的湖底,終歸還有這樣一座波瀾不驚、寵辱不驚、見證過往的望海樓。
徜徉公園湖
蘇軾有詩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這樣的湖光水色,我真疑心就是東坡先生專為千頃池寫的。
歷史總有此起彼伏的節(jié)奏,歲月總是變換著花樣舞步,推陳出新。望海樓下新出現(xiàn)的一泓綠水,推出了一個嶄新的公園,也推出了千頃池重新整合后的方陣:興建水體公園,繼而開辟“烏蒙水鄉(xiāng)",接上早已完成的滇字一號工程漁洞水庫,連上北部風景宜人的省耕湖……??消失千年的千頃湖儼然又還宗返祖,以另一種身姿衣錦還鄉(xiāng)了!
人們公認,望海公園其實是青山綠水的精靈,背靠鳳凰山的綠意,胸懷人工湖的漣漪,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春色依依,夏陽靄靄,秋光歷歷,冬景點點……??這里已經(jīng)成了人民群眾消遣的樂園。
徜徉公園湖,但見水面有清官亭方塘般的清澈,卻有清官亭難以企及的寬廣:湖間小島,宿鳥天堂;繞湖小徑,花木芬芳;白沙灘涂,孩子們赤腳奔跑,灑滿陽光……??
夜幕下的海樓公園更具魅力,霓虹閃爍,流光溢彩,近水波光粼粼,遠山遙相呼應,街市車燈成串,完全是一座不夜城的景致。
一陣微風,吹開了湖畔鏗鏘的伴奏樂。一群中老年女士正在認真地跳著歡快的廣場舞,旁若無人,旁若無湖,旁若無樓。
望海樓似乎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黯然謝幕。我試著去理解它,去撫慰它燈火闌珊處的背影。
自古好水多與樓閣亭臺相依偎。滇池若無那“千秋抱負三杯酒,萬里云山一水樓”的大觀樓,“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奔了也白奔。
昭通城近年來以其多彩的秋色和濃濃的秋意,榮膺秋城雅稱。時值2019年初秋,秋月朗,秋葉黃,秋果熟,秋水長,山川風物之秀,透出大自然無限的魅力。
望海樓有對聯(lián)云:萬千氣象滿垌野,楊柳樓臺接鳳凰。由此可見當年風光不錯。其實,這樣的好風景曾延續(xù)了許多年。聽永豐鎮(zhèn)三甲村黃訓奎書記聊天,望海樓以南方圓十來里水域開闊,“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描寫的應該就是那里。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時常有大鳥、老鸛翩躚田間提魚抓蛙。老鄉(xiāng)們不時逮到大鳥,將其羽毛制成扇子,煽火做飯,煽風納涼,幾乎家家都有一把。他還表示,如果我感興趣,可以割愛送我一把。我連忙表態(tài)不敢要,濕地精靈,豈能凃炭。為什么千頃池消失,那時人們不珍惜、枉驚飛鳥,也是一個原因吧。黃書記悻悻然:不懂事呀。到我們這一代,懂了,雀兒也飛掉了!
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風物,代表了各個時期的生態(tài)。千頃池毋論虛實,也遑論大小,畢竟風光不再。偉人毛澤東有名句:“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人物如此,千古江山風物更是如此。既看重今朝,更要有利明天!
此時我想起似乎讀過的一首小詩《海螺》:
曾經(jīng)滄海的你,
如今只剩下空殼一具。
海灘上,
我小心拂去你滿面沙塵,
將你迎回家里。
放在枕邊,
我夢見大海潮落潮起。
貼近耳邊,
我聽到遠古恬靜的呼吸
……
作者簡介:?周翔,祖籍山東,供職于云南電網(wǎng)公司昭通供電局,為昭通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曾任云南省電力文聯(lián)副會長。曾出版《朱提拾穗》系列散文集、詩歌集;中短篇小說集《捉魚》;散文集《一籠不叫一籠叫》;紀實文學作品集《果緣》等。??
來源:昭陽融媒? (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