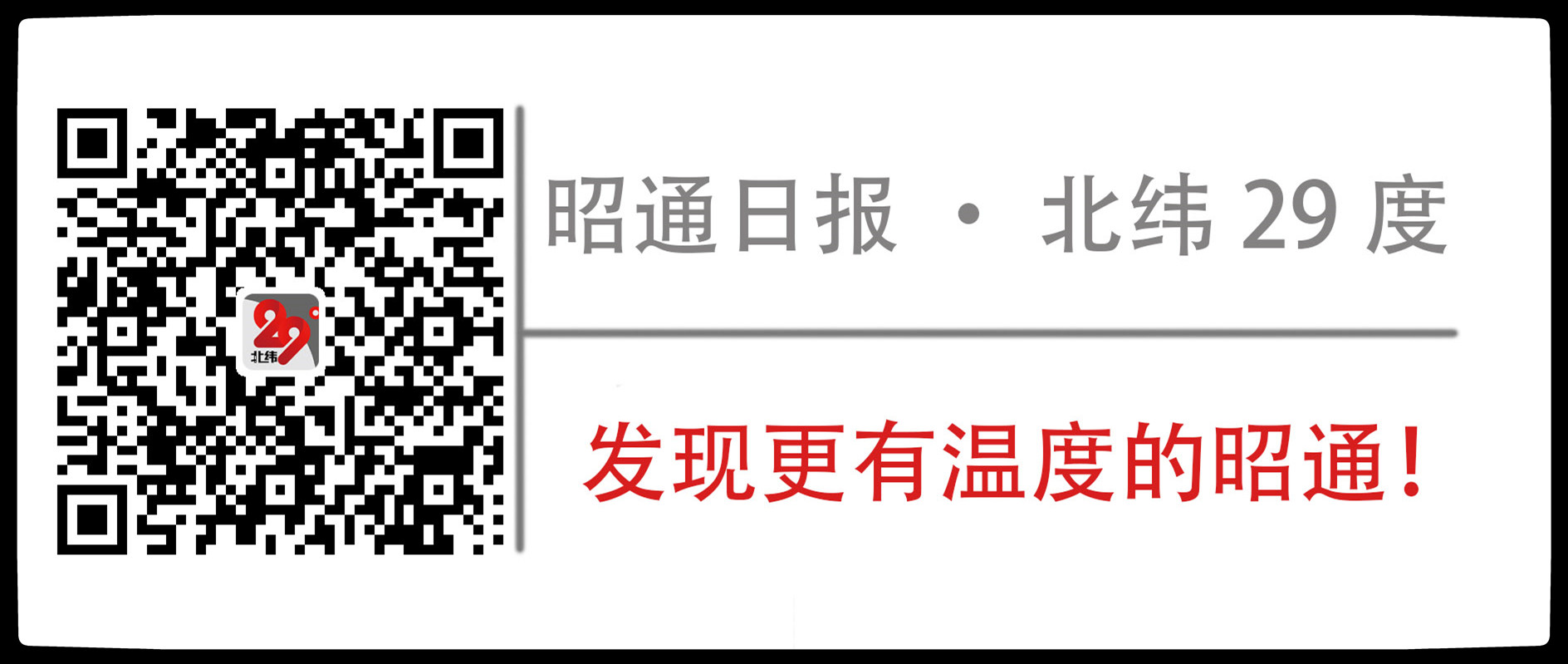2020-03-27 19:17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云南昭通巧家鸚哥村,是一個地處烏蒙山區(qū),背靠大山,緊鄰金沙江落差高達幾百米的村莊。這里的村民與外界聯(lián)系和出行,只能乘坐溜索,到對岸的四川涼山州,再換乘其它交通工具。如今,這道位于金沙江上的鸚哥溜索很快將成為歷史。——2017年2月2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jié)目在“走基層 看變化”報道了這個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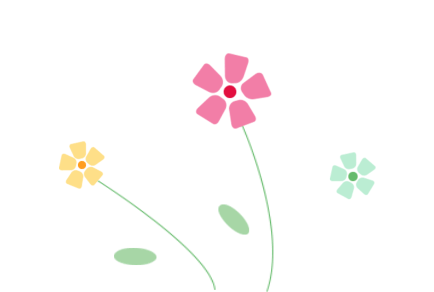
僅僅局部的環(huán)境。如果以圖片來看鸚哥村,一山一溝壑,一個取景框就收納了。但是,站在現(xiàn)場,一切都顛倒了過來。如果站在四川馮家坪的江岸上,抬起頭朝對面望過去,山偉岸,陡峭。低頭去看,幾百米垂直的下面,就是人們形容的洶涌澎湃或者波濤滾滾的金沙江。但是,站在江岸上看見的江水,不是在奔跑或者咆哮,而是如同按下相機,照片顯示出來靜止的一團白。
創(chuàng)造,是一種引領向前走的引力,也是一種最動人的景象。一個農(nóng)民,在高達260米,寬440米的金沙江上,創(chuàng)造出這“亞洲第一高溜”來,不得不令人驚嘆和服氣。這道溜索,非常捷徑地把云南葫蘆區(qū)和四川馮家坪連了起來,過去過來,再也不需要一天半載,只需要十分鐘左右。
但是,溜索之高,溜索之寬,溜索之險峻,一看就讓人不寒而栗。乘上溜索,就像赴死前線,你得堅定不移,是生是死,由不得自己把控。特別是第一次乘坐的人,沒有誰不心驚膽顫。所謂安全和勇氣,也是相互間一個給一個壯膽。三五個人,你敢坐,我敢坐,借了膽子,就都敢坐上去了。以我個人的感受,在第一次站上去時,也是緊緊抓住鐵籠的一根鋼筋,眼睛盯著離我最近的江岸。隨著溜索的移動,就看見了幾百米下的金沙江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寬闊,越來越壯觀,眼睛卻越來越花,頭腦越來越暈眩,整個身子越來越?jīng)]了穩(wěn)定性。鋼索在顫抖,鐵籠一寸一寸地在移動,我的心也一陣一陣的顫抖,緊縮,無著無落。
所謂震撼,除了你內(nèi)心對現(xiàn)場的恐懼感,還有高山,峽谷,空靈和遼闊的壯觀。當溜索移動至中間段時,看上去距離兩岸都很遠了。頭頂是高高的天空,腳下是深遠的江河,完全上不粘天下不著地。江風一吹,溜索的鋼繩隨之搖擺,移動,閃躍,說不害怕或者鎮(zhèn)定自若,那一定是假話。雖然每個人的感受斷定會不一樣。但是,在那一刻,一定,都會感到一個大世界里我們?nèi)说男∶烤箷犆谑裁矗苛锼靼l(fā)出的耳語,還是神的指示?一點也沒有夸張。那天從昆明城市下來的一個朋友李地龍。他站上溜索,溜索才開始啟動,他臉就嚇白了。溜索在一寸一寸地移動,離開江岸懸在空中時,他更加緊張了起來。雙手緊緊地抓住鐵籠的柱子,小腿在瑟瑟發(fā)抖。為減輕自己的恐懼,他把頭仰著,眼睛死死地閉緊,眉毛都結成了疙瘩。第二天,聽他說,自乘溜索回去晚上睡覺,一晚都被嚇了不斷做惡夢,一直在被那種懸空的恐懼所驚醒。
在1987年,上映了一部經(jīng)典電影叫《天菩薩》。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一個美國空軍中尉因參與中日戰(zhàn)爭而流落大涼山,遭賣給彝族做奴隸,改名拉鐵。拉鐵在彝族內(nèi)生活十年,愛上了少女牛牛,當他已適應那種生活時,卻被通知要返回美國,在國家的大前提下,拉鐵被逼放棄已擁有的生活和愛情,無奈地離去。在這里想表達的是,電影里拍攝溜索的一個鏡頭。開始是兩個美國兵,被當成了羊娃子賣出去的時候,被裝在了口袋里。從金沙江上乘溜索時,一人用一只手臂勒了夾著一個人,另一只手臂跨在溜索的一節(jié)竹筒上,順著溜索溜過去。其中有一個美國兵,溜到中間時,他不斷地反抗掙扎。結果,夾著他的那個人的手無法與他對抗,美國兵從溜索上像一個石頭一樣掉在了江中。從這種動感的鏡頭里,就可以感受到溜索的所謂震撼性。人不是飛鷹,在鋼索上,在懸空中,恐懼與生俱來。
危險。意外。心驚肉跳。視死如歸。無憂無慮。無畏無懼。祈禱和詛咒。種種可能性,在溜索移動的時間上都可能會存在。
身居巧家的鄒長銘老先生。在他的《昭通風物志》作品中,有過一篇寫《溜渡—笮橋》的文章。摘錄一段如下:
“最遲不晚于兩晉時期,溜渡就是金沙江、牛欄江、白水江、關河兩岸百姓實現(xiàn)彼此抵達的重要工具。爬上坐盤,坐穩(wěn),緊緊地攥住坐盤上的吊繩,左顧右盼,但見削壁如堵,鬼影憧憧,淵藪百丈,幽冥若霧,心里早已是虛空空地抓不到著落了。閉上眼,把未可預卜的前途隔絕在視野之外,僅存留一份不計生死的悲壯,勇往直前……無論你抵達彼岸的愿望如何強烈,守溜人緊拽著的拉繩只能一寸一寸地收攏,載人的坐盤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動。事實上,我們更有理由認為,自我們的祖先在關山絕塞,復水縱橫的滇東北地區(qū)定居那天起,溜渡便是他們走向明天的朝夕相伴的朋友。”
是的,在溜索上的人,絕大多數(shù)正如鄒長銘老先生作品里所述。其實,它的慢,慢得讓人懼怕,擔心。如同他們站在高速路邊看車過的速度,它的快,也快得讓人懼怕和擔心一樣。
鄒長銘老先生身體里藏著一座歷史博物館,無論你問到什么,他都如數(shù)家珍地告訴你。關于溜索,他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一個剛生了孩子的母親,在孩子滿月后,準備回娘家。在她回娘家的途中,必須要過溜索。年輕的媽媽高高興興把東西收拾好,放在背籮里背在身上,再把剛滿月的孩子放在前面用圍腰兜著。在乘坐溜索過江時,為了騰出手來抓著吊繩,她就用牙死死咬住兜著孩子的圍腰邊角。溜索行至江中,突然聽到江中咆哮的江水轟轟作響,低頭一看,只見白浪翻滾,一個接一個地涌過來。女人被驚嚇得“哇”地大叫了起來,結果,女人的這聲驚叫,圍腰松了,孩子便從圍腰里掉落江中。女人溜過江去,驚叫的嘴還在一直張著。
又能怎么樣呢?孩子掉下江了,讓人悲痛欲絕和無可奈何的是,回來還得坐溜索。還得繼續(xù)生活,再帶一個孩子,要去娘家,依然還得乘溜索出去。
深居峽谷的人,溜索再危險,總是可以有條與外界聯(lián)系的線。如果沒有溜索,更緩慢的時間和等待,同樣的無奈啊。在鄒長銘老先生的作品中,還有過兩則趣聞。說的是一農(nóng)戶的男人一早就到峽谷的另一邊趕場去了。午飯十分,家中的妻子做熟早飯才發(fā)現(xiàn)沒有鹽巴,就站在門前吩咐丈夫買鹽。兩人對話如在近鄰,表情達意準確無誤,可丈夫要從鄉(xiāng)場上把購買的鹽捎回,興許只能趕上妻子第二天的早飯。又一則說,某村地處絕壁半腰,下面就是滔滔的急流,可謂上不粘天下不著地,只一條小路和外界相通。這里的村民祖祖輩輩過著春耕夏鋤、農(nóng)桑只給、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可是種田需要耕牛,耕牛要到山外購買,能馱在背架子上背回村里的牛犢成為村民買牛的首選。何故?道路過于險絕,江流過于湍急。一馬平川的山外人之所以把這些發(fā)生的故事當做趣聞,是因為這樣的生存狀態(tài)離自己太遠,遠得有些天方夜譚。
開門見山,出門坡坡坎坎。是身居峽谷的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也是常態(tài)。在鸚哥村,無需追溯遙遠的時光,退回到十多年前。人們站在葫蘆區(qū)的村子里,看著江對面的人,一樣地喊得應。但是,如果兩人要碰面,抽根煙,或者交換某樣東西,就得背上食物走,快一點,在半天時間內(nèi)兩人可以把煙遞到對方手里,可以站在一起近距離說話。
交通,一直囚住了這個地方適應和消化的生活。但是,沒有囚住一個人的夢想和創(chuàng)造。一個叫蔣世學的農(nóng)民,創(chuàng)造了這道“亞洲第一高溜”,實現(xiàn)了他通向對岸的路的夢想。同時,也讓鸚哥村通向了國內(nèi)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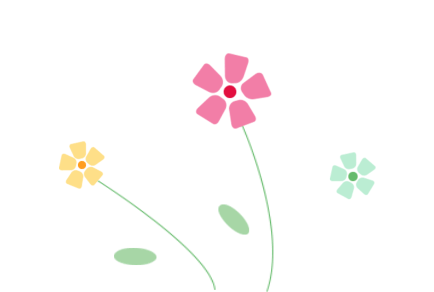
遠與近,構成視覺上的誤判。從心驚肉跳的溜索上過去后,就會發(fā)現(xiàn),眼前的村莊與站在對岸所見的村莊,截然不同。它呈現(xiàn)了一塊獨有的天地,大山仿佛往后仰了一下,騰出了一塊空間,讓出了一片平地。給人一種完全意外的感覺。錯落有致的房屋和樹木,維護著鄉(xiāng)村的寧靜尊嚴。
與所有掛在山梁上的山村不同的是,村莊和山壁之間,還有一塊一塊成梯狀的稻田。稻田雖然不多,卻珍貴,真是他們生活希望的田野。特別在八九十年代,是維系他們生命的金寶盆。盡管那時,收獲不豐,幾乎每一家人卻都靠著它,到更寒冷的高寒山區(qū),換取更多的洋芋作為一年的口糧。
以前不是田野。據(jù)村民說,在解放前,這一片是一個海子。海子中間,經(jīng)常有一股水在往上冒。當時,一茍姓地主家,喊幫他家的長短工,用很多石頭和泥巴,把海子填高起來。然后,地主家就在上面開始耕種田地。就在前幾年,有人看著這里水源好,把稻田承包了下來,放上水,又變成了一個大海子。承包人專門用來養(yǎng)魚。因為交通的緣故,魚養(yǎng)大了賣不出去,幾年下來,賺不了錢,還貼本,不得不把它放棄。放棄后又成為了良田。所以,有了今天在高山上還有田種的奇觀。
情是真誠的。生活是日常的。如果你進入這個村子里,走進他們中間,他們不會把你當成是一個異鄉(xiāng)人,也不會當成客人。如果來了遇上吃飯,飯菜端上桌子,就請你坐著吃飯。如果你要走了,他們照樣做自己的事情,不用太多的客氣。一切都那么平常和平靜。
經(jīng)歷過生活沉淀的人,都十分沉穩(wěn)。照說蔣世學一手策劃和運行的鸚哥溜,他說起它來,應該滔滔不絕。至少打開話匣子后,他會把建溜的苦楚和成就說得繪聲繪色。但是,沒有。一點也沒有。一問一答。問他什么,他只講什么,決不講一句其它多余的話。關于建溜的過程,他仿佛是一個局外人。
作為一個親身經(jīng)歷者的蔣世學,當然不是真正的局外人。他只是一言難盡。后來,我們坐在一起閑聊。慢慢地,蔣世學話多了起來。他說得最多的,還是路。他說起過去的部分經(jīng)歷,說他的老家,說他的婚姻,說他人生的路。他的老家實際上不在鸚哥村,是在更高一點叫油房的一個山梁上,氣溫比江邊冷涼得多。他和張世春結婚后,才住在了葫蘆區(qū)。他的人生,一輩子,都在這群山之中,打轉轉。山背后,其實也有路的,但是,要從山背后的路上走出去,就不要用時間來計算。比如去鄉(xiāng)街子上趕個場,早起晚歸兩頭黑還要加緊點。距離遙遠是一則。路途艱險,狹窄,麻繩一樣,很多地方要手腳并用才爬得上去是另一則。
山上的小道都大同小異。細小。陡峭。成書于漢代的《華陽國志》里,記錄了一首古歌:“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賈子,左擔七里……”這首古歌,非常準確和清晰地吟詠了烏蒙山中穿梭往來的生意人,行路是何等的艱難:楢溪、赤水這兩條河,就像盤蛇,東流西轉,彎彎曲曲。繞著羊腸小路的烏蒙山,又是極其的高峻,在山間趕路,都是大汗淋漓,拄杖小憩,哎喲嘆息。庲降過來的小販,左肩挑擔,苦熬七里才能換肩歇氣。因為道路太過狹窄,人擔著擔子走在上面,根本不可能換肩。就是秦漢之間鑿通的五尺道,也寬僅五尺,只能供馱馬行走。
但是,在鸚哥村的一些地方,千方百計踩踏出來的路,馬是無法行走的,只能單人通過。人通行時,腳下踩穩(wěn),還得用手扒著崖壁。而村莊前面的江,又無法行船。對岸有路,卻無法抵達。
就隔一條江啊!那路,就這樣如此清晰地擺在眼前,讓人隔岸眼觀,肉身卻難以跨步走到上面。現(xiàn)實苦楚,內(nèi)心也苦楚。每一次出去回來,直線距離分明很近,卻分明要繞行遙遠和艱難的路,才能抵達。怎樣才能以最近最快的方式過去?真是窮則思變嗎?變又能變到哪里?但是,這種像山路一樣繞來繞去的想法,一直在蔣世學的腦海里繞著。最終,繞成了他胸中燃燒起來的一個夢想:在金沙江兩對岸的絕壁上建溜,用幾根鋼纜繩來承載一個村莊的出路。
夢想的翅膀一旦展開,思想由此發(fā)生轉折。盡管困難一重接一重,就是最開始的基坑,挖多深,挖多大?鋼索的兩端怎樣才能固定鉚穩(wěn)?蔣世學心里都沒有譜。但是,他開始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金沙江下游有溜索的地方,觀察,琢磨,詢問。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和思索,他把每個細節(jié)記在心里,想透徹了,叫上妻子兒子就開始打坑。蔣世學這樣講述的時候,讓人由衷佩服。能把自己的夢想一點一點開始付諸于行動,他就已經(jīng)是自己的英雄。
當然,嘗試開創(chuàng)需要勇氣。因為它意味著成功與失敗的愉悅和沮喪,意味著困境中掙扎。當蔣世學把前期能出力的工作干好的時候,一打聽所需要的鋼索材料價格,七八萬塊。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對于一個山區(qū)無貨物流通的農(nóng)民來說,這已經(jīng)是一個巨大的數(shù)目了。它像一座山一樣堵在了他面前。因為家里如此寥寥,就是咬緊牙關,砸鍋賣鐵,也湊不起這個數(shù)。
錢不夠,蔣世學以最大的股東,約了十多家人來入股。在市場經(jīng)濟時代,如果以一種時尚的叫法,可以把它叫做溜索股份有限公司。實際當然不是,它不過是一個集體主義的行為,聯(lián)合了兩省的人。因為基坑的一端在云南,另一端要打在江對岸去,那里畢竟又不是云南的地盤,是四川。萬一有人破壞咋辦?為此,他約了一個四川人合伙。你看,他把各種可能性考慮得很周全。他既當起了溜索的設計師,指揮者,施工人,又是統(tǒng)籌家,他甚至把建好溜索后的運營,收入和分配,都早已計劃得井井有條。
咬碎時間和空間。沒有用機械,沒有用儀器。全都用人工。人力。鐵錘和鏨子。憑著在堅硬如鐵的巖石的質(zhì)感上打基坑。一個基坑的深度,達七米。然后,用鋼管,水泥,加固鎖定,把鋼纜繩鉚好。另一頭,用船把鋼纜繩拖過去。每一步都充滿艱辛和困難。用蔣世學的原話說:“吊命一樣啊,拖一股鋼纜繩過去,就要拖上三天三夜哩!”
或者說得更狠點,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充滿著兇險。在每一步兇險都化險為夷,徹底把四根鋼纜繩在兩端鉚好后。作為策劃人的蔣世學,每一個參與者,都無比激動。但是,激動是激動,很多人又擔心起一個問題。這么高這么寬的江上,誰敢最先坐上去試啊?還有人心虛,后悔和抱怨,費了無數(shù)的呆力笨力不說,如果不可以運行,那投進去的錢不是像丟在江里,泡泡都不冒一個了嗎?
后顧之憂是有道理的。因為每一分力都是汗水,每一分錢都是心血。然而,問題和困難,拋給了設計溜索的蔣世學。但是,在蔣世學心里,有一百個問題和困難,他似乎就有一百零一種解決的辦法。溜都拴好了,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個。作為鋼纜繩的承重,人在上面完全沒有問題。但是,誰又敢最先去冒這個險?
同樣大小的鐵,和同樣大小的石頭,孰重孰輕。蔣世學在生活中,不用計算,已成為了常識。他讓人把家里的廢鐵,或者鐵器的東西都搬來。大家也不知他要這些東西干啥,只是照著他的話,七手八腳地回家把鐵找了搬來,堆在一起。蔣世學不慌不忙地把一堆鐵稱了一下,總共有三千八百斤。然后,又讓大家把鐵放在溜索的鐵籠里,一寸一寸地拉著運行。結果,三千八百斤重的鐵,安然無恙地運過了對岸去。
人有多少重量?那可是三千八百斤啊!溜索雖然橫跨在云南葫蘆區(qū)和四川馮家坪之間。但是,這么重的鐵都過去了,人的重量算什么?恐懼和擔憂,問題和困難,隨著穩(wěn)穩(wěn)扎扎的溜索的運行,消除了,徹底消除了。最終滋生了膽量,都想爭相著站上去,體驗一回。
1999年。溜索成功了。終于成功了。出門就可以看見的路,再也不用繞上一天半載的時間了。現(xiàn)在,十多分鐘就可以順利抵達。大家激動,歡呼雀躍,也淚流滿面。
簡單的原理,也只有蔣世學懂得如何操作。開溜的時機把握,其他人都無法掌控。人站在這頭,對面是400多米之外。人乘坐在溜索上的鐵籠子里,什么時候不該停,什么時候該停下,必須準確無誤。因為停早了,離岸還懸著一截。停晚了,不立即停下,就會撞到對面的岸上。這靠的是眼睛,傳達到大腦的指令,當機立斷才能確保人的安全。蔣世學的眼力非常之好,讓人驚嘆,他可以看清400米之外。到對面的點了,最開始,他就一聲令下,停。后來,全在他無聲的掌控之中,眼,心,手的合一。
人工推拉,無比吃力。它不利于前行,似乎利于起舞。每一步行走都近乎于是一個雜耍的舞蹈動作。每運行一次,需要八個人,四個人站在下面使勁拉,四個人走在鋼索上用力推。在溜索開始運行后,乘坐的人,每人收取兩塊錢的費用。由于其他人都把握不好,大家只有在一塊商量,所有的管理歸蔣世學夫婦二人。入股的人家,以股份來進行收入。投資兩千塊的,在一月之中就拉一天。那一天中,收入多少就是多少。投資四千塊的就收兩天的費用,以此類推。無論輪到哪一家,都請他作總指揮,每天付給他十塊錢的報酬。
其實開始賺不了多少錢。蔣世學說:“最開始的時候,用人工,一天請七八個人來推拉,要供煙,又要供酒,還要供吃。一天運行下來,賺不到多少錢不說,主要是很費力。有時,站在下面的人,拉的繩子一斷,溜索就無法前進了。后來,想到用發(fā)動機來替代人工。”
這是否是與時俱進?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是逼出來的想法,是運行后的經(jīng)驗,是摸索出的成果。蔣世學雖然想到用柴油機,但是,手里沒得多余的錢。迫于節(jié)省,就買舊柴油機來設計。可以運行,又成功了。當時,讓人無法想象,“噠噠噠”的發(fā)動機一響,就省下了七八個人的勞動力和開支。從此,結束和告別了他們開創(chuàng)史上,那種原始和笨重的人工推拉方式。
機械無疑帶著速度或者加速度。人力省了,時間省了,速度也比以往快了。乘坐溜索的人,提心吊膽的恐懼感時間,縮短了。但是,麻煩事也在不可預知中出現(xiàn)了。舊的柴油機轉著轉著,有時突然就不轉了。這是加速度中戛然而止的恐懼。有一次,在送人出去時,“噠噠噠”的發(fā)動機響著響著,“噗嗤”一聲,像一個人的冷笑,之后就停下來了,再也發(fā)不起電來。柴油機壞掉的時候,乘溜的人正懸于中間。回不來。過不去。
那是一個冬天。在溜索上的人,瑟瑟發(fā)抖,不單是因為氣溫的緣故。江風吹來,無疑讓人寒冷。江岸上的人,把食物和鋪蓋溜到鐵籠里,在溜索上的人可以御寒。但是,更讓人心驚膽戰(zhàn)和不寒而栗的,是戛然而止停在半空中的鐵籠。無抓無拿,上不粘天下不著地。距離兩岸都是幾百米,距離腳下,也是幾百米的大江大河。一個巨大的空間里,周圍是空的,人心是空的。那一刻,在溜索上的人,平時相依相存的自然法則是否就完全顛倒了過來?誰也無可預知,懸空,會成為幸存者,還是一個生命毀滅的災難?
情不自禁地,岸上的人一邊修理發(fā)動機,一邊也在祈禱。“噠噠噠”的發(fā)動機再次響起來的時候,他們的心也如同發(fā)動機一樣,熱烈激越地搏動著,把懸在溜索上的人送過去。蔣世學說:“還不是一路波波折折的過來,因為有了那一次發(fā)動機壞掉的意外出現(xiàn),合伙的那個四川人,擔怕出現(xiàn)更大的事故,又賺不了多少錢,就全都并給了我。后來,柴油機買了三四臺,成本高得很,只有把過溜人的通行費每人漲到了3元。舊發(fā)動機機還是不好使,只有硬著心腸買新的,通行費也漲到了5元。直到2010年,電網(wǎng)改造,村莊終于通電了。當時電線桿,電線都是從溜索上運過來。有了電,我又想到了把柴油機換掉,直接用電。現(xiàn)在使用,都是用電,閘刀一推就啟動,閘刀一拉就停下,方便多了。”
通高壓電,告別和結束了另一段柴油機運行的歷史。自原初的人工到柴油機的交替,和用電的發(fā)動,溜索運行到目前為止,時間已過去了十多年。中間還發(fā)生一起意外的是,杉樹坪的一個人做生意運羊。因為進入鐵籠的門沒插緊,溜還沒到中間,門被羊撞開,一只羊下去,又一只羊下去。蔣世學趕緊往回溜回來,后面的羊才沒跟著下去。不然,這道被稱之為“亞洲第一高溜”的鸚哥溜,雖然完全由蔣世學一人設計和運行,至今并沒有發(fā)生過一起事故。無論用哪種方式運行,就是這現(xiàn)場感攝人心魄的溜索,十多年來,蔣世學夫婦除了運送來往的行人,還運輸各種物質(zhì)。那天,在溜索口看見的那輛“噠噠噠”正在拉運石沙建材的三輪摩托車,也是從溜索上運過去安裝,有了村子里唯一的一輛機動車。無論如何驚險,蔣世學確實敢為人先,幾根鋼索,完全承擔著一個村莊的重量。溜索是蔣世學的驕傲,也是鸚哥村的驕傲!
時間平靜而又忙亂的腳,爬上了蔣世學的臉龐。他的眼睛,也不能那么清晰地看到了400多米外的對岸。看不清對岸,難以掌握溜到點的節(jié)點。用對講機,多一人站在一端,相互報告,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蔣世學說:“對講機不起作用,等對方的聲音從對講機傳過時,溜箱都撞到對面的墻了。”他已經(jīng)看不清楚對岸,憑什么,在高壓電運行的溜箱下,還是那么準確地說停就停??
歲月流逝,每個人都在一絲不茍地老去。現(xiàn)在,蔣世學看上去明顯地老了。但你會發(fā)現(xiàn),蔣世學的臉上,雖然像粗糙的巖面,卻令人敬畏。這種敬畏,如同那又寬又高的溜索。溜索在運動和靜止之間,仿佛是他身體上的一個器官。因為你無法想象,那么遠的距離。他的把握,比對講機還準確,絲毫不差。憑的,完全是一種溜索和心靈一體的感覺。

作者簡介?朱鏞,昭陽區(qū)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第七次全國青創(chuàng)會代表,云南省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曾獲云南省作協(xié)創(chuàng)作獎,全球華文母愛主題獎,首屆滇東文學獎,第十二屆滇池文學獎,第二屆《百家》文學獎等獎項。出版散文集《奔跑的速度》《另一種方式的延續(xù)》,小說集《圍捕》《小巷里的茶館》,長篇小說《水靈》。現(xiàn)供職于昭陽區(qū)文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