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7 09:57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刺桐花開了多少個(gè)春天,東西塔對望究竟多少年,多少人走過了洛陽橋,多少船駛出了泉州灣”。
2017年冬,當(dāng)我這個(gè)來自云貴高原的游子,走上洛陽橋,我所受到的震撼,甚至超越了那首《鄉(xiāng)愁》,那枚小小的郵票,那枚珍藏在我心中的郵票。
曾記否,2011年,那個(gè)83歲的老人,跨過臺(tái)灣海峽,來到他的祖籍泉州,來解那份鄉(xiāng)愁。
可沒有想到,僅僅過去一個(gè)月,12月14日,這個(gè)叫余光中的老人,卻離我們而去。
“洛陽橋,又走過了多少人?刺桐花,又開了多少個(gè)春天?”
每念至此,我就想把對刺桐城的印象,送給那個(gè)90歲時(shí)離我們而去的老人。
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從泉州乘船回國,離開了他旅行17年的東方。他在游記中詳盡地描繪了泉州,把泉州與亞歷山大港相媲美,稱泉州為“東方第一大港”。游記的字里行間,滿城的刺桐花,紅得燦爛,泉州城也因此成為了“刺桐城”的美譽(yù),刺桐也從此成了泉州的符號(hào),刺桐花成了泉州的市花。
泉州城有個(gè)開元寺,開元寺里有兩座塔。東邊的塔叫鎮(zhèn)國塔,西邊的塔叫仁壽塔。其實(shí)兩座塔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座塔全由石砌而成,五層八面,東塔略高,有48.27米,西塔略低,有45.06米,是我國現(xiàn)存最高的兩座石塔。雙塔兩兩相對。在詩人眼里,不只是東西雙塔深情的對望,更是臺(tái)灣與大陸的深情凝望。咫尺天涯,海峽兩岸的同胞會(huì)在什么時(shí)候才能走到一起呢?
泉州城有條洛陽江,江上有座洛陽橋。橋長834米,寬7米,是宋朝泉州知州蔡襄的杰作,也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跨海石橋。這橋的特別之處,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洛陽江水急潮狂,造橋工匠用船載石塊沿橋梁中線拋下,使江底形成一道矮石堤,再在堤上建橋墩,橋墩中用條石交錯(cuò)壘砌,兩頭尖尖,以分水勢,減輕浪濤對橋墩的沖擊。而為了鞏固基石,工匠們還想出了種蠣固基法,即在基石上養(yǎng)殖牡蠣,使之膠結(jié),創(chuàng)下了把生物學(xué)應(yīng)用于橋梁工程的先例。
那天,我和余騰松從橋上走過,46處橋墩把47段長而寬的條石橫陳在江面上,像46條連環(huán)把浮在水中的船兒緊緊地扣在一起,分擔(dān)著南來北往的重量。看潮水淹沒了近千年的橋石,綴滿白色牡蠣斑的橋墩在退潮時(shí)若隱若現(xiàn),古人過人的膽識(shí)與智慧,讓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與泉州的邂逅似乎早有約定。我生活在祖國西南邊陲南“絲綢之路”上的昭通,那里不僅有唐風(fēng)漢韻,更有千年的馬幫,馱來中華的文明以及南亞的佛光。五尺道的血液與“絲綢之路”的動(dòng)脈一起律動(dòng),越過千山萬水。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diǎn)——泉州,怎能不令人神往呢?
“唐山晉水,宋舶元舟。“閩臺(tái)緣博物館牌坊上的這幾個(gè)大字,似乎濃縮了泉州的歷史。而泉州的歷史,實(shí)際上遠(yuǎn)比這幾個(gè)字概括的早得多。早在西晉時(shí),就有衣冠士卒南渡入閩,改南安為晉江。至唐初,因?yàn)槎惚軕?zhàn)亂,大量中原人特別是河南、河北和陜西的人南遷至此,帶來先進(jìn)發(fā)達(dá)的農(nóng)業(yè)技術(shù),開荒種地,也開啟了泉州的繁華。他們看到這里的山川地勢很像古都洛陽,于是把這個(gè)地方取名洛陽,這是洛陽橋得名的原因。
泉州枕著清源山,面對大海,氣候溫潤,得天獨(dú)厚。每當(dāng)季風(fēng)更迭,就有波斯灣、西亞、南亞的商船漂洋而來,在泉州港登陸。有最早記載的海外貿(mào)易是公元520年-527年,天竺(今印度)高僧拘那羅陀到泉州(當(dāng)時(shí)稱南安)九日山建造寺廟,翻譯梵文佛經(jīng),成為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例證。8世紀(jì)后期,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興起,注重從海上經(jīng)天竺和我國進(jìn)行貿(mào)易,泉州人也用銅鐵、陶瓷交換海外的金貝、珠寶、香料,泉州海外交通得到迅速發(fā)展。宋朝時(shí),泉州已經(jīng)與日本、高麗、占城、渤泥、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馬六甲(今馬來西亞)、蒲甘(今緬甸)、天竺、細(xì)蘭、波斯、大食(今阿拉伯)、弻巴羅、層拔等57個(gè)國家和地區(qū)有了海上貿(mào)易關(guān)系,他們舶來犀角、象牙、珠璣、玻璃、瑪瑙、胡椒,運(yùn)去絲綢、瓷器、茶葉,促進(jìn)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而今,走在泉州的老城,看到清源寺、基督教堂、開元寺以及數(shù)十個(gè)大大小小的寺廟,仿佛看到了當(dāng)時(shí)東西方文化在這里撞擊相融的景象。
在眾多西去的人流中,有一個(gè)人值得銘記。這個(gè)人就是鄭和。這不僅是因?yàn)猷嵑褪窃颇先耍c我是同鄉(xiāng),更因?yàn)猷嵑推叽蜗挛餮螅阎腥A文明傳播到了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非洲東海岸。在第五次下西洋的時(shí)候,鄭和就選擇了在泉州出海,并建立了媽祖廟。鄭和作為國家的航海大使,一生七次在海上航行,建立了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中西亞文明的使者,一直被后人記住。
可惜,因?yàn)槊鞒暮=輳氖澜绲囊曇袄锵Я恕V挥心切┊悋膹R宇、祈風(fēng)的石刻把泉州封存在了歷史的深處。
泉州一直保存著一種紅色的記憶。在寺廟、民居等建筑上,人們就地取材,選用燒制過的紅磚以及隨處可見的石塊來修房造屋,他們發(fā)明了一種出磚入石法,即把規(guī)則與不規(guī)則的石塊與紅磚交相修砌,有時(shí),還把海里的牡蠣殼也作為建材,粘得結(jié)實(shí),牢不可破。現(xiàn)在泉州城大大小小的街道,特別是老城區(qū)的西街一帶,還保持著這種紅紅的風(fēng)貌,成為泉州的又一種景致。
泉州人似乎特別地聰慧。我在老城區(qū)鐘樓附近,見到橫七豎八的好幾條街,設(shè)計(jì)與眾不同。不僅街道筆直,更特別的是,每面街鋪都是騎馬樓式設(shè)計(jì),隔三五米支砌一根大柱子,柱子與商鋪之間大約有兩米寬,依次排下去,形成了一條長廊甬道,甬道上面是打了板的。我想,這騎馬樓的設(shè)計(jì)是不是為了躲避常來偷襲的臺(tái)風(fēng)和海風(fēng),讓顧客免去日曬雨淋風(fēng)吹之苦呢?走上街道,逛著商鋪,太陽曬不著、雨淋不著,這種設(shè)計(jì)的確與眾不同。
泉州氣候溫和,雨水多,比較適合亞熱帶植物的生長,那些長了幾百年的榕樹,早已郁郁蔥蔥,獨(dú)樹成林,成為文廟等園區(qū)里最好的打扮。就連歷代古人祈風(fēng)出海、登高望遠(yuǎn)的九日山上,也有不少榕樹。
泉州最紅的色彩是那些開得燦爛的刺桐花。刺桐花根植在泉州的每一個(gè)角落,成為泉州生命的象征。每年三四月,平時(shí)極不起眼的刺桐花就次第開放了,鮮紅無比,把泉州城打扮成一個(gè)待嫁的新娘,紅紅火火,幸福吉祥。
在華僑大學(xué)學(xué)習(xí)期間,校園里的木棉花開了,在冬天里特別地可人,但我還是更喜歡那開得如火焰般的刺桐花。聽說,泉州城正在申報(bào)世界文化遺產(chǎn),他們申報(bào)的項(xiàng)目叫古泉州(刺桐城)史跡,刺桐已經(jīng)被泉州打上了歷史的印跡、文化的符號(hào),就像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diǎn),已經(jīng)成為泉州的財(cái)富。而歷代泉州人傳承下來的精神財(cái)富,成就了今天福建省的第一大經(jīng)濟(jì)體,再現(xiàn)了當(dāng)年泉州的風(fēng)采。
從南方“絲綢之路”一路走來,我很贊賞泉州在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方面的膽識(shí),眾多的文化遺跡仍然很好地保存下來或者被修復(fù),讓你應(yīng)接不暇。前些年,泉州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不遺余力,只是因?yàn)槠渌鞘袥]準(zhǔn)備好而擱淺。但是泉州毫不氣餒,積極爭取,向世界教科文組織遞交了古泉州(刺桐城)史跡申報(bào)項(xiàng)目的文本。
我真誠地祝福泉州申遺成功。此時(shí),我又想起了余光中老人的詩:“刺桐花開了……”
(該文寫于2017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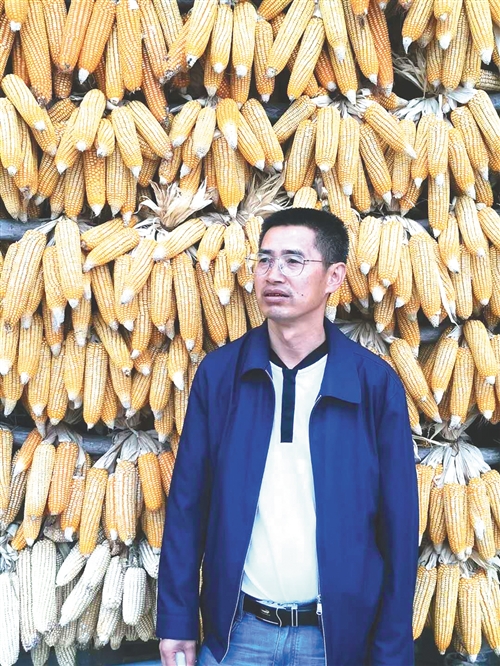 曹阜金?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縣人,現(xiàn)供職于昭通日報(bào)社,出版有散文集《夢回故鄉(xiāng)》《人在旅途》,有作品在國家、省、市報(bào)刊上發(fā)表。
曹阜金?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縣人,現(xiàn)供職于昭通日報(bào)社,出版有散文集《夢回故鄉(xiāng)》《人在旅途》,有作品在國家、省、市報(bào)刊上發(f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