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6 16:38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 |||||||
2016年,北京團(tuán)結(jié)出版社出版的《蹉跎·漩渦》一書(shū)扉頁(yè)上印著作者照片:一個(gè)紅光滿面,身穿藍(lán)格襯衣,系著紅色領(lǐng)帶,外加一件獨(dú)龍族褂子的小眼睛老頭,笑瞇瞇地佇立于咖啡色的書(shū)柜前。他寬且高的額頭之上,頭發(fā)已然花白,而身后的書(shū)柜里,眾多書(shū)籍排列有序,就像幾隊(duì)整裝待發(fā)的士兵。 照片上面是這樣一段作者簡(jiǎn)介:周元川,男,漢族,1943年生,云南賓川人,副主任中藥師。曾任怒江州醫(yī)學(xué)會(huì)、中醫(yī)藥學(xué)會(huì)、藥學(xué)會(huì)常務(wù)副會(huì)長(zhǎng)、秘書(shū)長(zhǎng),《怒江醫(yī)藥衛(wèi)生》常務(wù)副主編,怒江州藥檢所標(biāo)本室主任。出版專(zhuān)著《怒江流域民族醫(yī)藥》 《怒江中草藥》 ;省級(jí)以上學(xué)術(shù)刊物發(fā)表論文9篇,主持科研項(xiàng)目?jī)身?xiàng),獲獎(jiǎng)并生產(chǎn);應(yīng)邀應(yīng)聘中科院植物所工程師、云南省中藥材標(biāo)準(zhǔn)審編委員、香港中文大學(xué)訪問(wèn)學(xué)者。退休后創(chuàng)辦怒江州民族醫(yī)藥研究所,任所長(zhǎng)。業(yè)余從事寫(xiě)作,在報(bào)刊上發(fā)表過(guò)多篇文學(xué)作品。 這本書(shū)的作者周元川是我的大伯,這件事我也是2016年才知道的。時(shí)年,我44歲了,客居四川省已將近20年。之所以會(huì)是這樣,可能是因?yàn)榇蟛ぷ鞯牡胤皆颇鲜∨圩遄灾沃荩x我當(dāng)年生活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賓川縣山重水復(fù)隔得遠(yuǎn),親戚之間難以互通音信所致。 我和大伯能夠認(rèn)識(shí),還得感謝博客這個(gè)交流平臺(tái)。記得當(dāng)時(shí)身處異鄉(xiāng)的我,時(shí)常想念幾樣故土的家常飯菜,就寫(xiě)了一篇叫 《腌生》的美食文章放進(jìn)博客里,恰好就被大伯看到了。大伯身居異鄉(xiāng)久了,自然也對(duì)故土滋味心懷眷念,就在博客上和我交流。一來(lái)二去,塵封的親情圍繞我出生的那個(gè)叫巖澗橋的小村逐漸展開(kāi)。當(dāng)我看到電腦屏幕上突然跳出 “我是你親大伯”這樣一句口氣肯定的話時(shí),頗感意外。后來(lái),我先后收到了大伯郵寄過(guò)來(lái)的《蹉跎·漩渦》和《賓川仁和堂周氏家譜》兩本書(shū),通過(guò)閱讀大伯撰寫(xiě)的這兩本書(shū),我大致了解了整個(gè)家族以及大伯個(gè)人的過(guò)往經(jīng)歷、目前生活狀況。 《蹉跎·漩渦》一書(shū)由29個(gè)章節(jié)構(gòu)成,一共347頁(yè),講述的是作者自1943年出生之后,賓川縣解放前后發(fā)生的與作者相關(guān)的諸多事件。那是一段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歲月,在作者的敘述下猶如一幅幅斑駁的畫(huà)卷逐一展開(kāi),閱讀的過(guò)程中常常讓人內(nèi)心無(wú)法平靜。大伯的出生地溪河村,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狀況恐怕就是那個(gè)時(shí)代的一個(gè)縮影;生存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大伯,心懷向前看的信念,上下求索、咬緊牙關(guān)突出重圍的精神,也就是那一代人不甘沉淪的真實(shí)寫(xiě)照。書(shū)中,從小開(kāi)始就已經(jīng)形成“往前看,不能往后看、往側(cè)面看”這種定式思維的大伯,時(shí)至耄耋之年,為何還回首往事歷時(shí)數(shù)年寫(xiě)下這本書(shū)呢?在我看來(lái)并非是想自我立傳,因?yàn)闀?shū)中另一句話恰好展露了作者的心跡:“一直到晚年,才覺(jué)得有些事情還得往后看,失憶癥對(duì)于一個(gè)國(guó)家、民族、家庭、個(gè)人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或許正是這樣的初衷,使得這一本書(shū)與諸多記錄個(gè)人悲歡離合的回憶錄書(shū)籍有著本質(zhì)上的不同。 2020年1月25日,正值春節(jié),也正是武漢打響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戰(zhàn)“疫”的時(shí)候,收到大伯用微信發(fā)過(guò)來(lái)這樣一段話:“情系武漢,無(wú)心過(guò)年,因此敬告親朋好友和各位網(wǎng)友,本人謝絕一切拜年賀歲。在我同胞鄉(xiāng)親面臨生死存亡的日子里,哪有心情聽(tīng)什么新春快樂(lè)、恭喜發(fā)財(cái),恭請(qǐng)諸位海涵!”大伯的這一番話,深深觸動(dòng)了我。在家自我隔離的日子里,我再次翻開(kāi)了《蹉跎·漩渦》一書(shū),其時(shí),我已經(jīng)是第三次閱讀了。說(shuō)實(shí)在的,每次讀完之后,我都很想寫(xiě)點(diǎn)個(gè)人的想法,無(wú)奈書(shū)中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時(shí)間跨度較大,盡管全書(shū)結(jié)構(gòu)經(jīng)緯分明、環(huán)環(huán)相扣,但對(duì)于像我這種記性平平且天生對(duì)數(shù)字不敏感的人來(lái)說(shuō),想要把書(shū)中所涉及的人和事梳理一番,然后又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裝載到書(shū)中的時(shí)間那架馬車(chē)上是極為困難的。 這樣的感受屢屢使我坐立不安,那是因?yàn)椋乙恢庇X(jué)得對(duì)于《蹉跎·漩渦》這本書(shū)來(lái)說(shuō),我不是一個(gè)普通讀者,書(shū)中所講述的事情大都發(fā)生在賓川縣那片我所熟悉的故土之上,甚至?xí)性S多人物就是我的親人、熟人。除此之外,書(shū)中用到的許多生動(dòng)而又有趣的賓川縣方言也是讓我倍感親切。掩卷回味之余,我時(shí)常徘徊于書(shū)中的某個(gè)情節(jié)、某個(gè)場(chǎng)景里,明明心里思緒萬(wàn)千,可為啥就無(wú)從下筆呢?難道能夠駕馭這本書(shū)的只有作者本人?難道無(wú)形的韁繩只是牢牢把握在作者手中? 當(dāng)我再一次讀完這本書(shū)之后,有了新的想法,雖然全書(shū)涉及的人和事前后貫通,但許多章節(jié)又皆可獨(dú)立成章。既然這樣,我何不依葫蘆畫(huà)瓢,每讀完一章就寫(xiě)下自己所想到的一些事情呢?或許多年以后,我會(huì)將《蹉跎·漩渦》一書(shū)中所講述到的每一個(gè)我熟悉的村子、每一個(gè)我認(rèn)識(shí)的人、每一樣曾與我有關(guān)的事物,逐一敲打在我的電腦里。想到這些,我不禁回想起小時(shí)候尾隨父親從力角街步行回巖澗橋小村的家,一路翻山越嶺,正當(dāng)口干舌燥、饑腸轆轆的時(shí)候,聽(tīng)見(jiàn)身后傳來(lái)陣陣熟悉的聲響。原來(lái),村里那架由3匹馬拉的大馬車(chē)正朝我們駛來(lái),馬蹄揚(yáng)起的灰塵中、山風(fēng)奔跑的背影依然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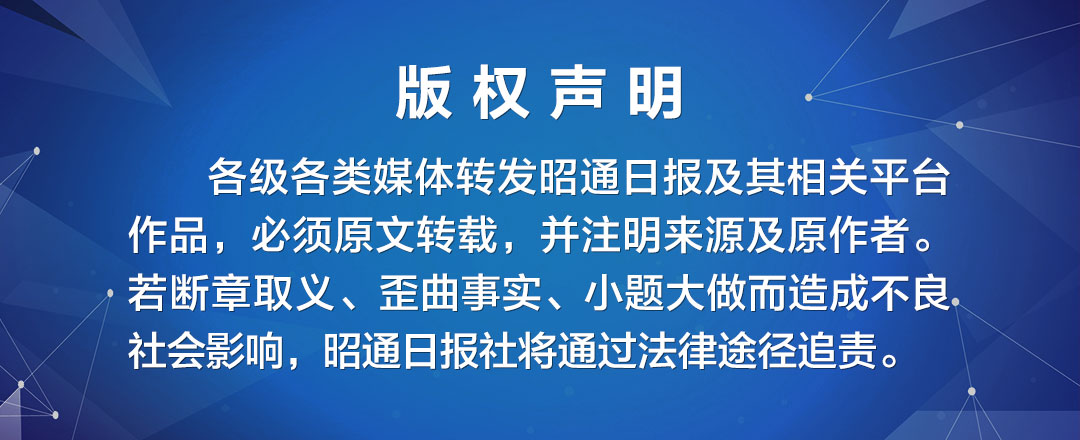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