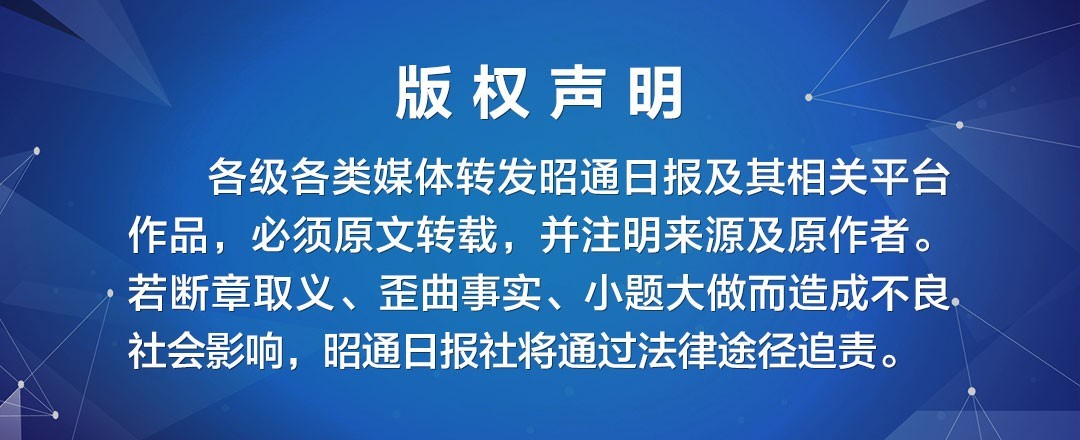2020-10-15 17:11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為窮人開疆拓土的蛋》 朗誦:一山

為窮人開疆拓土的蛋
冉正萬
這個蛋是山藥蛋,也叫地蛋。占領(lǐng)不同的地方它用不同的名字。在中國,它的名字有二十余個。在美國叫愛爾蘭豆薯,俄羅斯叫荷蘭薯,法國叫地蘋果,德國叫地梨,意大利叫地豆,在原產(chǎn)地秘魯叫巴巴。可見它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最初是帶著籍貫去的,落地生根后,融入新文化圈,它們有了新的臺甫。在西南地區(qū)可以這樣介紹它:姓馬名鈴薯,表字洋芋。
云貴高原上,在東部最大也就雞蛋那么大,以乒乓球大小者居多,幾十個才有一斤。從東至西至烏蒙山區(qū)昭通一帶,最大的六斤,最小的也有半斤,大多在一斤兩斤左右。我老家在黔北,黔北洋芋要是看見昭通的洋芋,一定會不好意思得靠邊站,甚至往地里鉆。如我遇到威風(fēng)凜凜的人時一個慫樣。據(jù)遵義市《桐梓縣志》記載,一九五八年,該地洋芋畝產(chǎn)125公斤。昭通市北閘鎮(zhèn),畝產(chǎn)以噸計,兩噸三噸四噸,這和幾十年來人為撿選反復(fù)實驗有關(guān),也和海拔與土質(zhì)有關(guān),和馬鈴薯本身強(qiáng)大的適應(yīng)能力更是有關(guān)。
十六世紀(jì),一個西班牙人從南美洲把馬鈴薯帶到歐洲,人們種植它不是為了吃,是為了欣賞馬鈴薯花。幾百年前,馬鈴薯花和現(xiàn)在也許大不相同,現(xiàn)在能見的白花和紅花,和眾多可供觀賞的花朵比起來,既普通又單調(diào)。或許人類馴化時,眼里只有地下塊莖,只顧吃,不再管它如何開花。在當(dāng)時的歐洲,馬鈴薯被定義為一種粗糙食物,只有下等人用來充饑。舊教徒甚至詛咒,說它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他們厭惡它、怕它,十有八九是因為它的毒芽有關(guān)。據(jù)1983年第一期《貴州醫(yī)藥》雜志記載,一位十二歲的農(nóng)村女孩,連續(xù)三天吃發(fā)了芽的馬鈴薯,出現(xiàn)頭痛,腹痛、頻繁嘔吐,伴抽搐,四次停止呼吸,面色青灰,嘴唇發(fā)紺,四肢厥冷,心律不齊。2010年第五期《福建農(nóng)業(yè)科技》有文指出,嫩綠的莖葉、外皮,特別是胚芽中均含有龍葵素,在馬鈴薯塊的胚芽里和受陽光照射變紫青的表皮里,龍葵素含量極高,不能用來喂豬,人更不能吃。查閱近三十年中毒事件,有好幾百起。
認(rèn)知局限有時是笑話,有時要命。馬鈴薯在休眠期是無毒的,它們休眠期只睡覺,不發(fā)芽。其休眠期長達(dá)三個月以上,如果管理得當(dāng),可以更長。
馬鈴薯在歐洲流浪了一百年才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這要感謝法國農(nóng)學(xué)家安·奧馬曼奇。安通過長期觀察和實驗,發(fā)現(xiàn)馬鈴薯不但能吃,還可以做面包、面條。對于種植的推廣,法國國王和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都作出過貢獻(xiàn)。俄國1842年發(fā)生饑荒,尼古拉一世強(qiáng)令農(nóng)民種馬鈴薯,早就不耐煩的俄國農(nóng)民發(fā)動了著名的“馬鈴薯暴動”。當(dāng)時,尼古拉一世根據(jù)財政部的建議,下令在數(shù)省設(shè)立馬鈴薯育種地段,按公有方式種植馬鈴薯。這引起官屬農(nóng)民的懷疑,以為要他們重新當(dāng)農(nóng)奴。這成了葉卡捷林堡、皮爾姆、喀山、諾夫戈羅德省等地農(nóng)民暴動的導(dǎo)火索。尼古拉一世盛怒之下出動軍隊,馬鈴薯在槍聲和血淚中慢慢被農(nóng)民接受,在土豆加牛肉的美味中,土豆猶如家庭成員,再也沒曾分開過。
最重要的是,幾百年來,科研人員對馬鈴薯的研究從未停止。2019年,由德國、秘魯、英國、西班牙組成的國際研究小組,對八十多種馬鈴薯進(jìn)行測序,以此確認(rèn)馬鈴薯起源。他們測序的馬鈴薯不僅有現(xiàn)代的,還有保存于1660年至1896年之間的樣本。
馬鈴薯起源于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脈。秘魯人有句諺語:寧看土豆,不看美女。
馬鈴薯何時經(jīng)何種方式傳入中國,至今沒有定論。一說從絲綢之路傳入,先在華北、山東、津京一帶種植,既而進(jìn)入內(nèi)蒙。另一說經(jīng)菲律賓、臺灣到達(dá)福建海岸,并率先在福建、廣東種植。美國學(xué)者德·希·珀金斯則認(rèn)為,馬鈴薯傳入中國的時間由歐洲人發(fā)現(xiàn)美洲和太平洋群島時間而定。也就是說,它們漂洋過海,在印度、爪哇和蘇門答臘、緬甸立足,然后大搖大擺來到昭通。雍正年間的《會澤縣志》和嘉慶年間的《大關(guān)縣志稿》都有記載。《大關(guān)縣志稿》上有烏洋芋、白洋芋、紅洋芋、草鞋洋芋數(shù)個品種,可見種植時間已經(jīng)不短。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十六世紀(jì),中國已有零星種植。明萬歷年間由蔣一葵編撰的《長安客話》記述,北京地區(qū)種植的馬鈴薯即土豆。其后不遠(yuǎn),徐光啟在《農(nóng)政全書》中寫道: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內(nèi)白皮黃。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膩衣,潔白如玉。
馬鈴薯傳入中國后,得到的待遇和它們在歐洲大不相同。史料記載,萬歷以后,馬鈴薯已經(jīng)躋身宮廷,成為皇家美食,達(dá)官貴人方可享用。稀奇玩意不一定是好東西,金屬鋁被提煉出來時身份超過白銀。拿破侖三世在宴會上使用過鋁制叉子,泰國國王使用過鋁制表鏈。2017年10月27日,世界衛(wèi)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jī)構(gòu)公布的致癌物列表,鋁制品在一類致癌物清單中。
馬鈴薯沒有貴賤之分,不屑與少數(shù)人為伍,它頑強(qiáng)地開疆拓土,哪怕切成兩瓣、三瓣甚至四瓣也能從地里發(fā)芽,一心要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食物,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平地不讓種,它們往高山上走,遠(yuǎn)遠(yuǎn)地把水稻和玉米甩在身后。它們不提虛勁,說什么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往高處走的同時,不能種水稻的角落必須占領(lǐng),不當(dāng)主食的地方就當(dāng)菜,不當(dāng)菜的地方就當(dāng)主食。既可簡單地水煮火燒,也可與一百多種食材搭配,做出幾百種不同口味的食物。與此同時,它還為愛挑剔的人留了一手:洋芋的營養(yǎng)成分是胡蘿卜的兩倍,是白菜的三倍。維生素C(抗壞血酸)含量遠(yuǎn)遠(yuǎn)超過糧食作物;蛋白質(zhì)分子結(jié)構(gòu)與人體的基本一致,極易被人體吸收利用,其吸收利用率近100%。有營養(yǎng)學(xué)家研究指出:“每餐只吃馬鈴薯和全脂牛奶就可獲得人體所需要的全部營養(yǎng)元素。”這還不算,它還可加工成果葡糖漿、檸檬酸、可降解塑料、粘合劑、增強(qiáng)劑及醫(yī)藥上必須的添加劑。
亞里士多德在《動物志》一書中說:從無生物進(jìn)入生物界的第一級便是植物,而在植物界中,各個種屬所具有的生命活力(靈魂),顯然有多少或高低的等差。從整個植物界看來,與動物相比照,固然缺少些活力,但與各種無生物相比照,它們又顯然賦有了“生命”。在植物界中,具有一個延續(xù)不絕的級序,以逐步進(jìn)向于動物界。
兩千多年過去后,最能與亞里士多德生命活力(靈魂)對應(yīng)的詞是基因。馬鈴薯為了適應(yīng)不同的環(huán)境,基因一直在悄悄變化。國際研究小組發(fā)現(xiàn),因為一種叫CDF1基因的變體出現(xiàn),使這種馬鈴薯更適應(yīng)歐洲夏季。進(jìn)一步測序表面,變體的差異是獨立發(fā)展的。也就是說,馬鈴薯能夠主動適應(yīng)不同的生長環(huán)境。
所有的植物都有智慧。樹木為了得到更多的陽光,向著天空不停地伸展;無娘藤把莖盤繞在比自己高的植物身上,捕蠅草靠吃昆蟲為生,含羞草為了保護(hù)自己會迅速地合攏葉子。這都是生存的智慧。但馬鈴薯的智慧遠(yuǎn)遠(yuǎn)超過其他植物,它主動迎合人類,特別喜歡配合人類對它們進(jìn)行的改良。特別是進(jìn)入中國后,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已經(jīng)培育出以紫色、紅色為主的彩色優(yōu)質(zhì)馬鈴薯,將紫、紅色馬鈴薯老品種與優(yōu)良高產(chǎn)馬鈴薯品種雜交,改良篩選出100多份不同品系的彩色馬鈴薯。與老品種相比,改良后的彩色馬鈴薯高產(chǎn),外形美觀,抗病性強(qiáng)。其中黃皮的P03新品種,就像為了黃皮膚的中國人特意長成這種顏色。
有些植物為了保護(hù)自己,讓自己有毒或者渾身帶刺,人在平時很難見到它們,大多只知其名,真身不知在何處。它們那點防身武器就像可憐巴巴的魔鬼,只能躲在深山修煉,遇到人往往不堪一擊。馬鈴薯正好相反,與人越來越親近,經(jīng)過三四百年努力,硬生生把其它食物擠開,一躍成為人類第四大主糧。它知道地球上誰是老大,于是無論走到哪里,都與人以合作而非對抗相處。在舊教徒眼里的一把爛牌,被它以謙遜和寬容作為王炸,成為植物界最大的贏家。馬鈴薯,是植物界的智者和王者。
中國是種植馬鈴薯面積最大的國家,面積還在增加,十年前六千萬畝,如今已經(jīng)超過九千萬畝。與拉脫維亞、哥斯達(dá)黎加、波斯尼亞、克羅地亞等國土面積相當(dāng)。中國每個省都有種植,其中又以云南增加最快,據(jù)說,全國十個馬鈴薯,就有一個產(chǎn)自云南。而云南又以昭通為最。這和窮人有關(guān),現(xiàn)在則和扶貧有關(guān)。2020年,昭通市昭陽區(qū)著力塑造三萬畝洋芋帝國形象,建設(shè)高標(biāo)準(zhǔn)馬鈴薯示范基地。本地相關(guān)文件規(guī)定:“對洋芋帝國基地單個經(jīng)營主體實施的馬鈴薯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種植馬鈴薯面積須達(dá)到1000畝以上,補(bǔ)助資金兌付須達(dá)到相關(guān)技術(shù)規(guī)程要求的種植規(guī)格、種植行向、種植密度、出苗率、整齊度、病蟲害防控效果等質(zhì)量要求,以驗收認(rèn)可面積據(jù)實兌付。”并且全是脫毒良種。
這里還是馬鈴薯種子基地。供德宏、紅河、文山、廣東、廣西冬季種植,貴州、四川小春種植,云南大春種植。同時還為緬甸、孟加拉、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國提供種源。那么,你吃到的馬鈴薯,有可能是昭通馬鈴薯的后代。與之相應(yīng)的項目叫國際馬鈴薯科技園。內(nèi)容包括五萬畝西南高原馬鈴薯高標(biāo)準(zhǔn)及關(guān)鍵技術(shù)集成示范基地;年儲六萬噸智能冷鏈系統(tǒng);集成技術(shù)服務(wù)及線上線下營銷等互聯(lián)網(wǎng)新業(yè)態(tài)平臺;馬鈴薯產(chǎn)業(yè)大數(shù)據(jù)平臺;建成智慧農(nóng)業(yè),包括氣象監(jiān)測、土壤大數(shù)據(jù)、病蟲害監(jiān)測及防控中心;年產(chǎn)兩億粒馬鈴薯原種智能霧化栽培大棚;智能機(jī)械分揀包裝工廠;年產(chǎn)十萬噸智能機(jī)器人生態(tài)肥料工廠;馬鈴薯新品種研發(fā)中心;全球農(nóng)業(yè)科技研究創(chuàng)新平臺;馬鈴薯VR博覽館。中國雖是種植面積最大的國度,單產(chǎn)卻不及很多國家。
在可以預(yù)計的將來,會有更多的馬鈴薯從昭通走出去,在他鄉(xiāng)生長,在他鄉(xiāng)開花。有人說,你腳下的土地就是你的祖國。這話是不是從馬鈴薯的前世今生獲得的靈感?
站在昭陽區(qū)西魁梁子上,目力所及,最遠(yuǎn)的山梁上是發(fā)電的大風(fēng)車,海拔多在三千米以上。海拔兩千八百米以下,成片的是馬鈴薯,零星的是莜麥。西魁是一個小地方,但名聲越來越響。賣烤洋芋的,菜場賣菜的,洋芋販子,都把自己的洋芋叫“西魁洋芋”。就像北京之外的“北京烤鴨”并非來自北京。
西魁梁子海拔兩千三百米以上,沒有一塊稻田,卻比當(dāng)?shù)仄渌胤阶钕瘸陨洗竺住N骺R鈴薯不但耐寒抗病,還高產(chǎn),鄰近的四川布拖、金陽、昭覺等縣農(nóng)民背著大米上來換薯種,一斤換三斤。據(jù)中國馬鈴薯網(wǎng)最新報價,昭通種薯P03每公斤二塊八,合作88每公斤三塊六。布拖、金陽大米一斤能否再換三斤,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一畝稻田出產(chǎn)的大米換不來同面積西魁梁子出產(chǎn)的馬鈴薯。
人類主食的改變主要是烹飪方式的改變。新石器時代,以火炙、石燔、汽蒸為主。夏商周,因為青銅器的使用,烹飪奠基開新篇。春秋至隋、唐,鐵鍋的使用,燉、燒、燜、燴越來越豐富。隋唐時期胡餅制作方法傳入,又增加了烤。白居易《寄胡餅與楊萬州》詩云:胡麻餅樣學(xué)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寄與饑饞楊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
馬鈴薯適合任何一種烹飪方式,哪怕回到新石器時代,火炙、石燔都沒問題。至于燉、燒、燜、燴,百無禁忌。倒要看你使用的配料。西南地區(qū)的所有的城市,無論大小,無論白天晚上,都能吃到烤洋芋。我現(xiàn)在居住的小區(qū),每天晚上九點左右,烤洋芋和小豆腐小攤好幾百個,早的半夜收攤,晚的烤到天亮。也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人,白天有無其他工作,只知道時間一到,用一根小扁擔(dān),一頭挑著炭火,一頭挑著小豆腐和洗切好的洋芋,各自來到街邊,擺好炭火和小凳即可開張。這是給身體倍棒和尿酸不高的年輕人準(zhǔn)備的,吃烤洋芋和小豆腐不喝啤酒,如同看電影不吃爆米花。像我這樣有痛風(fēng)史的中年人,一般只能看看、笑笑,然后縮回老窩,看看非布司他片還剩多少。
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名著《鐵皮鼓》第一章中動情地寫道:“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時候,穿著她的幾條裙子,坐在一塊土豆地的地邊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練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齊齊地歸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豬油面包,接著,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著她的幾條裙子,坐在兩只差不多裝滿土豆的籃子中間。她的靴底同地面構(gòu)成一個直角,靴尖差一點碰到一起,靴底前悶燒著一堆土豆秧,它間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陣陣火苗,送出的濃煙,與幾乎沒有傾斜度的地殼平行,局促不安地飄去。”
剛拔出的土豆秧子能點燃。對此一直疑惑。或許那是但澤,又是深冬。在烏蒙山,剛拔出的土豆秧子還很濕,要經(jīng)過兩三個太陽的暴曬后才能燃燒。不過他說得對,在土豆地里火燒土豆最好吃。
在烏蒙山赫赫有名的大山包自然保護(hù)區(qū),我看見燒在牛糞堆里的土豆,皮焦黃,幾次忍不住想下手。大山包的牛只吃草,沒有人工飼料,牛糞燃燒起來很香,這香味一定會鉆到洋芋里面去。糞火不是烈火,慢慢煨,洋芋熟透后不急于掏出來,扒到熱灰里,保持一定溫度。我沒吃,它們個頭太大,又是剛吃完飯出來。隨著年齡增長,肚皮越來越大,食量越來越小。讀的書越來越多,記性越來越差。這么悲哀的事情連慈悲的洋芋也無可奈何。
曾有人以吃火燒洋芋寓待人,要會捧會吹會拍。因為又燙又有灰,吹拍捧是必須的。不過,以此寓人卻不敢恭維。這明顯是以下對上,一副奴才相。吃燒洋芋,我喜歡另外一個故事:由于天災(zāi)絕收,農(nóng)人連種子都沒有,去地主家討要。地主從火堆里扒出洋芋請客人吃。如果客人剝了皮吃,地主什么也不會給。如果客人吹干凈灰就吃,地主會給他種子。如果客人連灰也不吹就吃,地主不但給種子,還要另外贈送糧食。地主是因為珍惜糧食才成為地主。
馬鈴薯不需要吹拍捧,它寧愿人們把它當(dāng)成一個普普通通的蛋。它曾與窮人相依為命,現(xiàn)在,它擔(dān)負(fù)起為窮人擺脫貧困的重任。

昭通日報—北緯29度夢工廠出品
音頻錄制/圖片拍攝:楊洋
海報制作: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