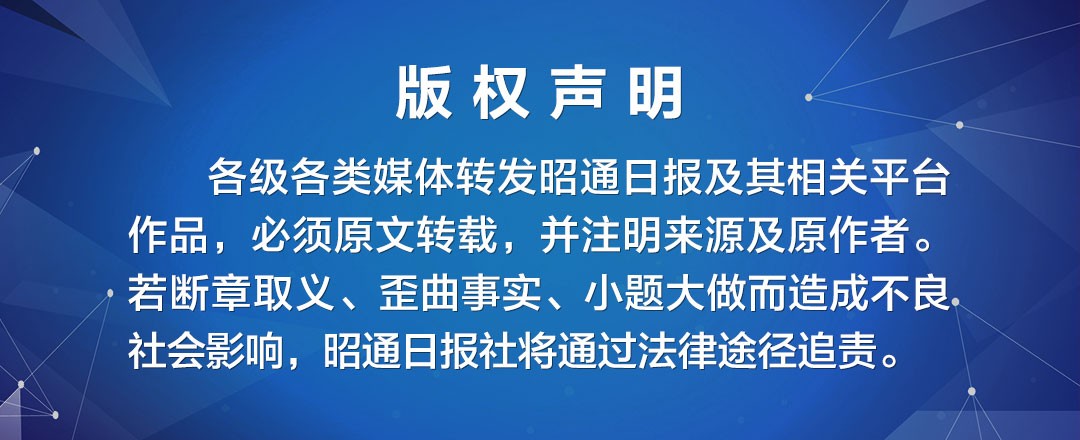2020-11-09 16:52 來源:昭通日報
作者簡介
楊曉燕,筆名慕雪,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作品散見于《邊疆文學(xué)》《散文百家》《云南日報》《金沙江文藝》等刊物。著有散文集《聽風(fēng)的日子》。
苦刺花,苦刺花,有女莫嫁舅舅家,舅舅家里有個山貂鼠,舅母家里有個癩蛤蟆……”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們唱這首童謠的時候,正是苦刺花開得旺盛的季節(jié)。
那一年,我七歲。漫山遍野的苦刺花在山風(fēng)中搖曳著,如落入山野的一簇簇雪花,給山鄉(xiāng)增添了些別樣的景致。
苦刺花開,正是家鄉(xiāng)人吃花的時節(jié),我?guī)е婺咐拥目嗍w粑粑,和二妞他們一起摘苦刺花。來到山上放眼一看,四處都是一片花的世界,摘花的人三三兩兩。山的對面是老陰山,幾只老鴰嘶鳴著在上空盤旋,祖母說老陰山的松樹上掛著很多死娃娃腦殼,我們再不敢朝前一步。祖母說那里有煞神,去到老陰山,會沾染山上的邪氣。
我不喜歡吃苦刺花,那個苦涼苦涼的味道讓我無從下咽,祖母說這是窮苦人家災(zāi)荒年頭最好的吃食。祖母總說:“死丫頭,沒有苦,哪呢有甜?”
也就在這個春天,全家人共同期待著另一喜事。母親就要生產(chǎn)了,父親外出還沒有回來,村里的接生婆枝奶奶也還沒有回來,說是去遠(yuǎn)處的一個村子里接生去了。隔壁的三奶奶端了一盆灶火灰去母親床邊,她看了一下狀況說母親難產(chǎn),要趕緊請接生婆,祖母說:“婆娘家生娃娃,哪個不是自己生?我那幾年生老二老四,在山上抓松毛葉子的時候就生下來了,自己拿石頭切斷臍帶,把圍腰布解下來抱在籃子里就背回來了。有什么好驚乍乍的!”
母親在床上痛的死去活來,我從門縫里看到母親的頭發(fā)像是用水洗過一樣,呲著牙齒,呻吟聲由大變小。那情形,讓我想起家里殺豬年豬的時候,我天天和祖母喂養(yǎng)的大豬在殺豬匠的刀子下痛苦呻吟,血越流越少的時候,呻吟聲也越來越小,最后漸漸停止了呼吸。想到這些,我開始害怕起來,祖母這才慌了,于是趕緊叫我:“死丫頭,看什么看,趕緊去看看枝奶奶給有回來了。”奶奶剛說完,我撒腿就奔枝奶奶家,可是枝奶奶還是沒有回來,祖母只好又叫鄰村的李半仙來給母親驅(qū)邪。
我祖父回來了,看到李半仙在屋里用桃樹葉刷來刷去,嘴里罵道:“這種神神叨叨的,裝神弄鬼的咋個有用。”祖父說著就火急火燎的出去了。家里,李半仙叫我祖母抓來一只雞,一刀把雞的喉管割開,血從刀口處噴到地上,濺到一疊黃色的冥幣上,李半仙把冥幣拿到母親床頭,然后再把染了雞血的桃樹葉在房間里來回舞動著,口中念念有詞:“我請?zhí)蚁蓙恚蠊硇」頋L出去,雞公來代替!”……
不多時,祖父請了一個赤腳醫(yī)生來家里接生,赤腳醫(yī)生給母親注射了針?biāo)缓蠼心赣H用力,祖母看到我在外面守著,于是把我攆出去玩了。
因為害怕母親死了,我不敢出去玩,就這么在大門口坐著,等候母親生產(chǎn)。那時候,時常聽村里人說,鄰村的哪家小媳婦生娃娃時大的小的都死了,哪家的婆娘生產(chǎn),娃娃是生出來,產(chǎn)婦因流血過多死了。村里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凡是夭折的娃,就被送到老陰山掛在松樹上給老鴰吃。我那個年紀(jì),對死亡有著深深的恐懼,想起老陰山上的死娃娃腦殼,就不寒而栗。
三奶奶端著一盆灶火灰出來,上面有些暗紅色的黏糊糊的血,就像我平時磕破了頭,奶奶端來灶灰撒在血上,再用掃把掃干凈倒到對門坡的樹林的那種樣子。三奶奶換了一盆又一盆的灶火灰,潑了一盆又一盆帶血的水。我幼小的心靈也跟著一陣陣掙扎,害怕、孤獨、失落……
“呱哇——呱哇——哇哇哇……”正在恐懼著,只聽到屋內(nèi)一聲響亮的嬰兒哭聲,把我的思緒拉了回來。我跑進(jìn)屋,只見三奶奶手里抱著一個小人兒,她笑呵呵的說:“趕緊來看看你的小妹妹給好看。”赤腳醫(yī)生說:“胎盤還不下來,我看這個情況,應(yīng)該還有一個娃吧,大人都快要不成了,沒得力氣生了,趕緊送醫(yī)院。”正說著,父親已經(jīng)從他上班的地方趕回來了。父親見此癥狀,斬釘截鐵的說:“送鎮(zhèn)衛(wèi)生院。”赤腳醫(yī)生說:“肚子里還有一個,怕等不到鎮(zhèn)衛(wèi)生院了,這得抬著走七八公里,會悶死的。”父親說:“大人要緊。”赤腳醫(yī)生說:“我再來試試。”三奶奶給母親喂著紅糖雞蛋,然后叫母親再用力。可是母親用不上力了,赤腳醫(yī)生于是硬著頭皮,用手去給母親接生……幾分鐘以后,又一個小弟弟出生了,只是這個弟弟生下來不會哭,臉是青紫色。
父親顧不了那么多,他讓赤腳醫(yī)生先救著孩子,然后邀了村里的幾個青壯年小伙,把媽媽放進(jìn)用被褥墊好的超大竹籃里,抬著她去鎮(zhèn)衛(wèi)生院,經(jīng)過醫(yī)生極力搶救,母親的命算是保住了。
數(shù)天以后,父親用自行車載著我去醫(yī)院看望母親,母親見了我,微笑著拿糖果給我吃,說是親戚送來的。我坐在母親身邊吃糖,弟弟妹妹安靜的在旁邊睡著。我就這樣靜靜陪著母親,暗自想著我還是一個有媽的娃,于是心里就開始有些欣喜起來。
這一天,弟弟妹妹吃飽了,不吵鬧了,我在旁邊翻看著一本小人書,可我認(rèn)不得多少字,想讓母親給我念字,我叫阿嫫她不應(yīng)聲,眼睛看著我,說不出話來,我嚇得大哭起來,母親望著我,她的眼角瞬間流淌出清亮亮的液體……此時醫(yī)生來了,他們迅速對母親施行搶救。看著醫(yī)生忙碌的身影和父親焦急的神情,我嚇得再次哭起來了:“我要我阿嫫,我要我阿嫫……”所幸的是,經(jīng)過醫(yī)生極力搶救,母親又一次從死神的手中逃離出來,醫(yī)生說這一次是針?biāo)^敏。
母親生了龍鳳胎,祖母走路做活都不時哼著小調(diào):“油菜花開一片黃,對門坡上等小郎……”遇到人就喜滋滋的打招呼,有時候也會在門前摘一個桃樹葉吹起調(diào)子,那聲音婉轉(zhuǎn)悠揚(yáng),看得出祖母的心情像是家門前五月的石榴花,熱烈舒展。
母親出院后,父親再也沒有出去建筑隊上班。等母親的身體恢復(fù)得差不多了,她和父親一塊起早貪黑一鋤頭一鋤頭的在陡坡上墾荒,在田地間勞作,她說家里有了這么多張嘴,得比以前更要勤快些,要不然就吃西北風(fēng)了。
冬去春來,老陰山依舊魏然而立,門前的河水永不回頭,日夜奔騰著向東流淌去。村里的娃娃們依然不知愁為何物,下河摸魚,上山打鳥,下地割草,在稻場上玩捉迷藏,在灰窩窩里玩打仗。炊煙升起的時候,大人們叫喚各人家的孩子回來吃飯,有的娃娃衣服撕破了,頭被擦破了,大人就開始嘮叨斥責(zé)。于是,狗吠雞鳴聲、訓(xùn)斥聲,孩子的哭喊聲混合在濕漉漉的炊煙里,迎接著又一個山村夜晚的到來。
日子,依然過得像是秋天里村頭樹上的紅柿子,在枝頭熱熱鬧鬧。閑暇的時候,母親會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們?nèi)ゴT。聽嬸子大嫂們閑談,這些女人們在一起議論著村里的事。她們說隔壁的五大媽就要生了,五大媽已經(jīng)連續(xù)生了三個兒子,這是她的第四個孩子,盡管已經(jīng)超生,但是五大爹說多子多孫多福壽,他就是苦死累死也情愿交超生罰款,生下這個娃。
二胖媳婦已經(jīng)娶進(jìn)村里好多年了,長的單薄秀氣。她生了一兒一女都沒有養(yǎng)大,先后夭折了。后來她公公婆婆去親戚家領(lǐng)養(yǎng)了一個女娃娃回來給她壓長,也許因為生不出孩子,她總是很自卑,也不愛和人搭話,此時她正低著頭縫針線,稍微還有些底氣的是,她已經(jīng)挺著一個孕肚了。一個嬸子說:“二胖媳婦,你這個肚子尖溜溜的,一定是個兒子。”二胖媳婦細(xì)聲細(xì)語的說:“姑娘兒子都好,生兒子不見得你老了會背你烤熱頭(太陽)。”嬸子笑笑說:“沒有兒子,在村里人前人后受人欺。”二胖媳婦不作聲了。
冬天的小山村,鉛灰色的天空低低的壓了下來,風(fēng)像一只野獸般怒吼著。二胖家的屋門前,一位神婆拿著桃樹葉在驅(qū)趕著邪魔小鬼。二胖媳婦在房間里生的快要死了,聲音微弱了下來。二胖說請人送衛(wèi)生院,他老母說:“女人生娃娃不都像擠豆米,哪個像這種嬌滴滴呢,急什么,要給她吃點苦得呢。”不一會,就有了孩子呱呱墜地的響亮哭聲。見又是一個女娃娃,二胖老母滿臉不高興,嘴里嘀咕:“這老天怕是要絕后吧!”
我因為是女孩子,祖母并不是很疼我,當(dāng)我摔倒大哭的時候,她總是說:“丫頭家家的,有什么好金貴的。”母親說:“姑娘兒子都一個樣,都是我的心肝肝。”不知不覺中,我又到了上初中的年紀(jì),因為要住校,我每個周末才能回家,便用省下的錢給祖父母兄弟姊妹買個糖或者一塊糕點什么的,弟弟妹妹開心,祖母也眉開眼笑。接下來我又給祖父祖母洗滌臟了的衣物,給做飯的祖母挑滿一缸水。
一天又一天,祖母見我這么乖巧懂事,重男輕女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大幅度轉(zhuǎn)變。再后來,我考取了師范,成了我們村里第一個女中專生,注重顏面的祖母覺得臉上有光,對我的態(tài)度有了很大的轉(zhuǎn)變,凡是好吃的都給我留著,見到鄉(xiāng)鄰就說:“女娃子也可以挨我們老楊家光宗耀祖了。”
讀師范二年級的時候,老師們帶我們?nèi)ギ嫃V告畫,掙得幾百元辛苦費,我把自己掙的錢給祖父母各買了一套衣服,給母親買了一塊頭巾,給父親買了一條褲子,給弟弟妹妹買了糖果。祖母對我愈加疼愛起來,總親熱的叫著我小名。
放假回到村子里,母親說,二胖媳婦吃敵敵畏,已經(jīng)送去城里搶救了。我很震驚,但是又覺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那個說話輕聲細(xì)語的女人,自從領(lǐng)了一個女娃娃來壓長后,又接連生了兩胎都是丫頭。母親說,五大媽因為與二胖媳婦爭菜園里澆菜水的事情,仗著自己生了四個兒子,羞辱了二胖媳婦:“你看看你就是一只下不出公蛋的母雞,等你老死了連個送上山的人都不有得,你有什么資格挨我爭?”二胖媳婦受了氣,回家又遭重男輕女的公婆一頓數(shù)落,想想活著實在沒有盼頭,索性含淚穿上自己喜歡的一套新衣服,喝下敵敵畏躺在了床上等著閻王爺來叫她。幸好二胖回來發(fā)現(xiàn)的及時,趕緊叫了我父親去洗胃,洗完又叫人抬著去了縣城的醫(yī)院,才算保住性命。
我和弟弟妹妹長大了,而祖父母一年年的蒼老下去,我工作的時候,祖父和祖母卻要靠著拐杖才能出門了,再后來的后來,他們已經(jīng)老得不怎么出門,也不怎么愛說話了,只有村里的三爺爺每天都會叼著煙斗來找祖父聊幾句,回顧一下他們以前的陳年往事,此時的祖父,才一改常態(tài),精神倍增,笑容和歡樂又回到了他那滿臉褶子的臉上。
門前的小河依舊永不停歇向前奔流而去,春天來了又去,去了又回,父親和母親的白發(fā)也在歲月的洗滌中與日俱增。父親是一個喜歡外面闖世界的人,他當(dāng)過兵,當(dāng)過煤窯工人,干過建筑,他還喜歡穿干凈整潔的衣服,喜歡唱流行歌曲,喜歡拉二胡。可是因為家里孩子多,祖父母年紀(jì)大了,而大伯叔叔姑姑們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工作,沒辦法回來伺候老人,父親即使再怎么向往城市的生活,也不能把重?fù)?dān)丟給母親一個人。于是,父親開始跟著祖父學(xué)習(xí)醫(yī)術(shù),就這樣,半路出家的父親,順承了祖輩們“中醫(yī)世家”的祖業(yè),在家鄉(xiāng)當(dāng)起了赤腳醫(yī)生,閑著的時候就與母親去地里勞作,恨不得白天比夜晚更長一些,那樣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苦刺花開了一茬又一茬,日子過了一春又一春。村里打工的姑娘媳婦們?nèi)チ擞只兀亓擞秩ィ赣H一直羨慕著,念叨著:“等你們姊妹幾個讀書畢業(yè)了,我也去外面打工,來世上做場人,也好去見見世面。”可是當(dāng)我們姊妹幾個長大的時候,我的祖父母老了,母親沒辦法丟下年邁的公婆,只有繼續(xù)努力做好一個兒媳的分內(nèi)之事。陽光灑在院子里,祖父母老得哪兒也去不了,只能坐在院子里烤太陽。汗流浹背的母親從地里回來,忙著燒火做飯。忙碌了一陣子之后,把熱乎乎的飯菜盛在碗里端過來遞給了祖父母,然后又喂豬喂雞,等待著家里的其他人回來吃飯。
當(dāng)夜晚來臨的時候,父親拿出他心愛的二胡,就著山村里清冷的月光,開始訴說心里的往事。而母親獨自坐在電視機(jī)前,剝著包谷棒子殼。父親拉了一會二胡,然后拿了一把小椅子,坐在母親旁邊剝著包谷棒子殼。父親看著母親羨慕電視里那些色彩斑斕的世界,打趣的說:“現(xiàn)在娃娃們讀書的讀書,工作的工作,等把老人送上山之后,我們兩個也出去打工吧。我去醫(yī)院打雜,你去給人家當(dāng)清潔工。”母親笑了笑:“那這個家不要了?”父親笑笑不吭氣了,繼續(xù)剝包谷殼,他們心里的美好憧憬在生活瑣碎中暗淡了下去。
我的祖母在82歲的時候,漸漸出現(xiàn)了老年癡呆的癥狀,她開始叫不出孫子孫女的名字,最后連家里人都不認(rèn)識了,她只是認(rèn)識唯一的一個人,那就是我的祖父。此時將近九十歲的祖父,除了精神狀態(tài)不如從前外,意識依然清晰,祖母時常端一張小凳子,坐在祖父前面,讓祖父給她撓癢。祖父一邊給祖母撓癢,一邊有一句沒一句的講著一些兩個人經(jīng)歷的陳年往事。祖母閉著眼睛,靜靜的聽著。再后來,祖母已經(jīng)沒辦法走出堂屋門了,每天的一日三餐,母親都要親手端到祖父母手里。除此,祖母也沒辦法到院子邊上的外面去上廁所了,家里人給祖母準(zhǔn)備了一只便桶,父親就伺候著祖母在房間里解決大小便的事。我工作之余,也會回去給祖母曬曬被褥,給他們洗洗衣服,打整一下他們房間的衛(wèi)生。而祖父母,每天坐在堂屋的一組雙人沙發(fā)上,祖母閉目養(yǎng)神,祖父給她撓癢捶背。
兩年后,祖母已經(jīng)起不了床,每天都只能在床上呻吟,父親給祖母熬中藥,打營養(yǎng)液,打吊瓶。叔叔姑姑們回來了,祖母已經(jīng)意識不清了,嘴里嗯嗯啊啊說著誰也聽不清的語言。在那個清冷的黃昏,祖母在三叔的懷里去世了。
祖母去世以后,受到打擊的祖父臥床不起,父母給祖父熬了中藥和參湯,并喂他吃下。慢慢的,祖父的病好起來了,只是他的身體已經(jīng)大不如前,但農(nóng)忙的時候,祖父仍然會幫母親剝包谷棒子殼,在院子的曬場上,趕著來偷嘴的雞。那個時常來陪祖父聊天的三爺爺,突然生病去世了,我家的院子里再也沒有兩個老人爽朗的笑聲。祖父失去了祖母,又失去了可以一起聊天的三爺爺,精神狀態(tài)日況俞下,祖父偶爾會和兒孫們聊幾句,但是都不如以前的那種暢然了。孤獨的祖父,每天晚上都會顫巍巍地從床底下摸出一瓶兒子們給他準(zhǔn)備的酒,咕咚咕咚喝上幾口,然后上床睡覺,他說,吃了酒晚上睡覺半夜不會醒。祖父一定覺得,半夜醒來看到房間里另一張空空的床,黑夜中那種深深的孤獨會螞蟥般叮咬著他的心。
兩年后,祖父去世了,他走的時候很突然,誰也不在他的身邊,他就在夜晚靜悄悄的走了。辦完祖父的后事,本想父親和母親會輕松了些,但是父母都很傷心,母親常常自責(zé),為什么自己沒有在祖父面前守著他,而讓老人一個人靜悄悄的走了。母親常常會做了飯后要先盛一碗準(zhǔn)備端給祖父,才想起來祖父已經(jīng)去世了,每當(dāng)此時,母親就會暗自垂淚。母親說,祖父是個脾氣很好的人,從來沒有在家里發(fā)過脾氣,他走了非常不舍。
后來,弟弟成了家,弟媳婦生了一個孩子,因為年輕人要工作,只能把一歲半的孩子給父親和母親帶著。見到村里在外面打工的四嬸回來,說是在廣東的一個廠子里做工。母親和四嬸說:“你們福氣好,可以到處望望外面的世界,我這一輩子就是只能在這個家里生根了。”父親幽默的說:“老婆子,你去闖世界吧,家里的事情交給我了。”母親說:“我走了,你怕是會把我的豬雞餓死。再說了,這個小孫女咋個整?”父親無奈的笑笑說要去鄰村出診,于是出門了。
讓我們一家猝不及防的是,一向身體健康的父親突然得了心臟上的毛病,我們帶著父親輾轉(zhuǎn)于縣、州、省各級醫(yī)院。醫(yī)生說父親心衰很嚴(yán)重,他們目前沒辦法給父親手術(shù),和弟弟妹妹商量后,我和先生決定帶著父親去省城的醫(yī)院給父親做手術(shù),當(dāng)我家先生開著車載著父親前往省城醫(yī)院的時候,父親遞給我兩張一寸的照片,一張是母親的,一張是父親的,父親說:“燕子,這是我和你媽前年拍的照片,我們最瞧得順眼的就是這兩張照片。”我默默的接了過來,照片中的父親和母親都很顯年輕,烏黑的頭發(fā),兩年前拍的照片,看上去就是五十不到的樣子。可是這一年,父親因為病痛,把他折磨得都不成人樣了。母親為了父親的病,已經(jīng)愁得白發(fā)倍增,滿臉皺紋。父親給我他的照片,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心里更像鈍刀割一般難受。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把父親的病醫(yī)治好。
生命是一刻也不停歇的,或許,我們真應(yīng)該在生命最燦爛的時候,燃燒自己,留一點光和熱給這個大地。就像我的父親,他總是停不下來他忙碌的腳步。
父親心臟支架手術(shù)很成,。出院回家后,天生樂觀好動的父親,或許他覺得不應(yīng)該這個病就把自己打倒,軍人出身的他也許不愿意被命運折服,他總自己自己已經(jīng)好了,沒有把醫(yī)生的叮囑放在心上,趁著母親不在家的時候,擅自爬到屋頂上去弄電視接收器。等母親干完活回到家時,父親直挺挺的躺在屋頂?shù)耐呱希烨拔医o他買的智能手機(jī)滑落在他腳下……
聽到噩耗,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到父親身邊,我摸著他的手,還尚有余溫,可任憑我撕破喉嚨,我這個一向高大堅韌的父親,再也不會回答女兒的問話了。我的母親已經(jīng)哭得昏死過去兩次,家里隨即被一種巨大的悲傷籠罩著,看著父親親手置辦的所有家私,他還來不及安度晚年,就匆匆忙忙走了。頓時,我的世界一下子坍塌,只想用盡所有的眼淚,讓思念鋪成通往天堂的路,會不會讓我再和父親相聚……
又是一個春的季節(jié),我們?nèi)宜坪踹€未從失去父親的悲痛中回過神來。可春天就這樣意氣風(fēng)發(fā)而至,她似乎是一塊沾染生命活力的畫布,嫩黃、淡綠、翠綠、粉紅、淡紫……富有張力的顏色讓人心口豁然一亮。在春風(fēng)里感受著新生的氣息,我們心里的悲傷似乎減了不少。
這樣的春天,我們家終于傳來了好消息。弟弟打電話給我說弟媳婦要生二胎了,我立即請了假趕至醫(yī)院產(chǎn)房外。此時,只見弟弟已經(jīng)抱著一個小嬰兒了,我問他弟妹呢,弟弟說還在產(chǎn)房,過了一會,弟媳婦被醫(yī)生推出來了,她說肚子很痛,醫(yī)生說這是產(chǎn)后子宮收縮。又過了一會,弟媳的肚子更痛了,只見她滿頭滿臉都是汗,嘴唇發(fā)白,我趕緊讓弟弟去找婦產(chǎn)科主任,主任來了說立即去做B超,可能子宮里還有問題。B超出來后,果然是子宮大出血,醫(yī)生說必須馬上手術(shù)。于是,弟媳又被推到手術(shù)室準(zhǔn)備手術(shù),我們在產(chǎn)房外焦急的等待了數(shù)小時,這三個小時,可以說就像把我們家人丟在鍋里的面湯水里般煎熬,焦急疼痛又茫然。好不容易熬到弟媳手術(shù)完出來了,可是她已經(jīng)陷入了昏迷狀態(tài)。醫(yī)生說要立即輸血,否則病人生命危急。
這一晚上,弟媳婦由弟弟陪著在急救室輸血,我在護(hù)理床上帶著剛剛出生的小侄子睡覺,小家伙倒是很乖,醒來哼幾聲后,把奶瓶給他嘴里一塞,他吃幾口就繼續(xù)睡覺了。一夜都睡得很安穩(wěn),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媽媽在經(jīng)受著怎樣的劫難,時刻都有生命危險,我便一直睜眼到午夜時分,才朦朦朧朧睡著了一小會。到了天快亮的時候,看著小侄子睡得香,我便請旁邊病人的家屬給我看管著他,立即跑到急救室看了看弟媳,所幸的是,她已經(jīng)醒來了,只是還不會說話,我終于松了一口氣。
看到我,她一個勁流眼淚。事后我問她為什么哭,她說她情緒復(fù)雜,也許因為拼盡全力,終于有兒有女了,也許為她醒來時醫(yī)生和她說了一句話:“你的命終于撿回來了,好好養(yǎng)著!”她看到我,也可能是那種從鬼門關(guān)回來后見到親人的那種喜悅,抑或是生孩子過后的痛楚還沒有完全消失……女人為了繁衍下一代,總是耗盡心血,甚至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把希望之花盛開在未來……
有了小侄子后,母親便沒辦法抽身了,因為弟弟和弟媳都在老家的衛(wèi)生所工作,這樣一來,在城里接送大侄女上學(xué)的任務(wù)就只能由母親完成,周末她又忙著回去老家種莊稼、喂豬、喂雞,幫弟媳帶小侄子……我說讓母親把農(nóng)活的事情放一邊,我們兄妹三人也能夠讓她衣食無憂了,但是似乎雞、豬、莊稼已經(jīng)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了,讓她一下子放棄,對她來說就像讓她放棄身心的一部分。
回到村子的時候,母親依然會和我拉家常,她說五大媽死了,五大媽生了四個兒子,兒子們一個都不愿意養(yǎng)她,兒子們像踢爛洋芋一樣,把她到處攆,最后她一個人住在了兒子們臨時搭建的一個低矮的房子里。據(jù)說,五大媽是因為生病,在她的小廂房里躺了兩個月,哼叫了幾個星期后才死去的。而村里被五大媽罵的那個養(yǎng)了三個女兒的二胖媳婦和她老頭子,已經(jīng)被女兒們接到省城享福去了。
看著老屋屋脊背后快要落下去的太陽,我心中忽然升起無限悲涼,我想我們每個人終有一天,就像電影落下的沉沉帷幕,會被人蓋上一層白布,宣告生命從此終結(jié),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像冰融于水,一切歸一。
生老病死,依然像每天的太陽升起又落下一樣再普通不過,村子里依然不斷有孩子出生,有人死去,有人出嫁。春天里撒小秧、種苦蕎、種包谷,夏天里薅草、施肥,秋天里收稻子、苞米……所有的事情一如既往。
清明節(jié),給親人掃墓的同時,也是一個踏春的日子。踩著春天的綠草和野花,我在父親的墳前久久佇立著,想到他生前生活的種種不易,和母親一起為養(yǎng)育兒女,贍養(yǎng)老人,一鋤頭一鋤頭墾荒,一點一滴的奮斗,留下了正直勤勞的人生足跡。而后輩們踩著父親的腳步,一代接一代,走好未來的路。
一些新生的藤蔓在父親的墳頭攀爬著,一陣風(fēng)吹過,嫩綠的顏色在陽光下充滿了無限的生命力。生與死,生與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命輪回,如鏡子中的影像,生命在歡笑中來,在哀嚎中送走……
忽然想起《鏡雙城》里那句話:一切始于結(jié)束之后,生與死重疊,終點與起點重疊,一切歸于湮滅,如鏡像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