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0 14:40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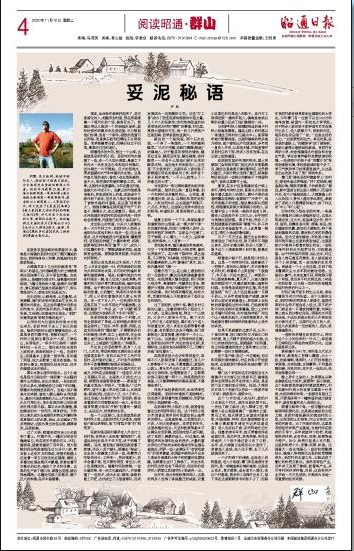
在脫貧攻堅戰(zhàn)略的浩蕩春風中,鎮(zhèn)雄縣大灣鎮(zhèn)的妥泥村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悄然轉(zhuǎn)身的人和事,構(gòu)筑起村莊的脫貧經(jīng)脈。
大灣鎮(zhèn)早在十九世紀初就享有“旱碼頭”的盛名,當時鎮(zhèn)雄最大的士紳隴維邦莊園坐落于此,至今保留完整。走在老街上,板壁房沉郁古樸,裝載著時間的秘語,飛檐斗角的封火墻,盛滿歲月的露水,青石板路已經(jīng)被水泥路替代了,街頭巷尾的行人,都在匆忙趕赴遠方。
走出老街,山路彎彎,山巒疊翠,水流蜿蜒,境內(nèi)的多條河流在此匯合后,向著赤水河奔去。在這些向著赤水河奔去的河流中,妥泥河是另類的,不喧囂,不張揚,兀自繞山優(yōu)雅地向東流去。“妥泥”的意思就是“舒服安穩(wěn)的地方”。
從雨河河與仕里河的河流中分流出來后,妥泥河終于走上了自己的旅途。豁然開朗的頭道河緩緩抬起頭,這里是妥泥村最平坦、寬敞的地方,一個村民小組居住著百余戶人家,三面臨山,東面臨水,一條鄉(xiāng)村公路和一座橋?qū)⒋迩f一分為二。居住在村莊東面的人家較多,西面的相對少一些。走進村莊,房屋基本上就是一層磚房,有的蓋了兩層,但大多數(shù)第二層沒有裝修。站在橋頭看去,房屋排隊站在河邊,似乎在凝望遠去的流水。
犀牛水是頭道河的起點。這個小地名是因為公路邊的一座極像一頭兇猛的犀牛山而得名,在出水洞前,一泓汩汩而出的山泉水,驕傲地穿過公路下的石縫,順著水溝流淌進妥泥河。當?shù)厝苏f不清泉水的來源,曾有人翻山越嶺去尋找源頭,最后只發(fā)現(xiàn)周圍的大山上竹林密布,水從竹根沁出,泉水在流向深山后迅速消失得無影無蹤。犀牛水水質(zhì)清澈,捧起清涼的水一飲而盡,渾身舒坦。天然的山泉水成為當?shù)鼐用窈透浇逭悴杌蛑缶频纳虾盟矗虼耍呎Q生了很多烤酒坊,這股水煮出的包谷酒,醇厚香濃,品質(zhì)較高。
過了大橋,順著妥泥河走200米就到了寨上。村落中央,一幢古舊的老宅巍峨聳立,站在有年代感的石頭、木柱、窗欞前,就像穿越到了百年前。浩大寬敞的四合院里曾經(jīng)住過10多戶人家,青石板上還有歲月的痕跡,房屋的板壁上還掛著一串忘記收走的紅辣椒,樓枕上系著的紅繩在微風中飄著,那象征著平安喜樂的紅色,暗淡了歲月和往事。這里的住戶添丁增口后,都搬出老屋,就近擇地建房。這幢老宅被人冷落后,像個巨大的鐘擺,在風中搖擺著。
現(xiàn)在,生活條件逐漸好起來了,老宅里居住的人,相邀來到村里,想在那里修建一個現(xiàn)代化的廣場,被我否決了。我建議將這兒修成一個休閑娛樂場所,就和扶貧的同事多次走進老屋,盡力幫助他們協(xié)調(diào),但有一個條件,破敗的老屋可以拆除,但是青石板和四棵柱子必須保留。簡單修繕青石板,四棵石柱立于四角,算是對過往的追憶。
順著流水的方向,拐過一個山灣,這里就是妥泥村民小組。妥泥河的河水清澈了一些,在一個大回頭灣里,懸崖之下的河水一次次攻擊出奇形怪狀的礁石,還沖刷出一片開闊地。巨大的回流水,帶來溫暖的水氣和豐富的水生物。這是河魚扎堆的地方,曾有人在此悠閑垂釣,魚不大,是肥美的花鰱和鯽魚之類。雨季,這里河水經(jīng)常暴漲,今年還漫過河堤,魚被大水沖走不少。烏蒙山的河流都是湍急的,那些逆流而上的魚,在旅途中又被沖到下游去,但總有幾條還是洄游到了食物豐盛的河道里,在這里“延續(xù)香火”。倔強的鯽魚在桃花盛開時產(chǎn)下的魚子,慢慢長大,在這里繁衍。現(xiàn)在,赤水河流域的妥泥河和其他的河流一樣開始全面禁漁,河道里已經(jīng)有小魚在游弋。
走出臨山的河道,10多戶人家掩映在一大片竹林之中,妥泥村民小組的土地相對比其他村民小組多一些,但山地居多,這片河灘地因為河道寬闊、灌溉便利,老百姓因種植了大量的枇杷、核桃、板栗等經(jīng)濟林果而“富甲一方”,成為人們炫耀的資本:“要嫁就嫁妥泥娃,地里都是金疙瘩。要娶就娶妥泥婆,河邊洗衣好耍喲。”
妥泥以前也是趕過鄉(xiāng)場的,7月賣豆、8月賣瓜盛極一時,花花綠綠的衣服與式樣簡單的農(nóng)具,手巧的村民編織背簍和提籃銷售。現(xiàn)在,沿著河流的方向在村里走一趟,有幾位老人坐在角落,用鋒利的刀剖開青竹剔絲取線,編織旮底背簍。由于青壯年的大量出走和周邊道路的改善,之前繁忙、熱鬧的鄉(xiāng)場冷清了,街上只有生意清淡的幾家土雜貨店。有一次下鄉(xiāng)入戶,一位扶貧隊員在店里買到了10多年前生產(chǎn)的解放鞋,這雙膠鞋穿了一年多,還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便成為扶貧隊員下鄉(xiāng)的“標配”。
在妥泥或者大灣的每一個村落,水田全部改成了旱地,以前種植水稻的田里全部種上了包谷、洋芋、板栗、花椒,這些農(nóng)民俗稱的“懶莊稼”,不需要更多的時間管理、侍弄,加之土地有限,完全依靠土地已難以維持生計,很多青壯年外出務(wù)工,土地留給“空巢老人”種蔬菜。
外出務(wù)工的妥泥青年,孤身一人出門,幾年后,帶回來南腔北調(diào)的老公或者老婆甚至孩子,有的從遠方打工后開車回村,在村里的公路上,不時有外省牌照的車子放著震撼的搖滾樂招搖駛過。
在妥泥河即將迎來與仕里河交匯的地方,村民在這里修建了一座廟宇,祈求上蒼賜以平安。這里的人們走出大山前,都要到廟里敬香表意——家里留下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空巢老人”過河耕作,留守兒童上學必經(jīng)之路上,水流湍急,路途兇險,這些為人父、為人子的人,走過當?shù)厝怂追Q的“溝外”妥泥橋,都會迎著家的方向默默地站一會兒,有的還隨身帶著父母用“汗帕”包著的一撮泥土,去往遠方,找尋新的生活。
在一個三岔路口,往左拐就是張家溝村民小組,這里的村民大多姓張,每家每戶都沾親帶故,是“打得罵不得”的“網(wǎng)兜親”。
張家溝是妥泥村最早有人外出打工的村組,有很多人去沿海“摸爬滾打”,在遙遠的他鄉(xiāng)嘗盡千辛萬苦,終于站穩(wěn)了腳跟。后來,看到他們掙錢回家改善了家境,許多人丟下鋤頭,跟著去“淘金”。出去的人做建筑工的多一些,依靠勞力吃飯的活計,工種單一,勞動強度大,技術(shù)含量不高,但只要吃得苦、肯出力,收入也是穩(wěn)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頭腦活絡(luò)、有一定文化基礎(chǔ)的人,開始掌握了一些技術(shù),成為水電、鋼混、裝修的能工巧匠,合伙成立了小型裝修隊,后來發(fā)展成為一定規(guī)模的公司。這些“打工者”成為了改變張家溝面貌的中堅力量,幾十戶人的張家溝,農(nóng)村危房改造的扶貧項目成為村民“嘲笑”的事情,村莊里,高房大屋隨處可見,唯一的幾戶貧困戶還是因病、因?qū)W致貧的監(jiān)測戶。
路邊的一個庭院里,兩個石水缸里,一個養(yǎng)了一株蓮花,一個用來腌制酸菜。“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躥躥(趔趄)”的鎮(zhèn)雄人,對于酸菜有特別的情結(jié),酸菜紅豆湯、酸菜豆花湯、酸湯豬腳、涼拌酸菜……沒有什么是他們做不出來的酸菜式樣。遠走他鄉(xiāng)的張家溝人,注定是“不太貧窮的”,這里許多人家的孩子都跟隨父母在沿海城市上學,前年有個孩子回來高考,“一不小心就考上了一所著名的大學”。
與張家溝一街之隔的黃家溝經(jīng)濟條件卻很差。起伏的山路一直延伸著,到一片杉樹林后卻戛然而止。山林里,夏天潮濕悶熱,蚊蟲、烏梢蛇和菜花蛇較多。入秋后雨水多,山谷里盛產(chǎn)刺梨子、八月瓜、米泡兒,這些深山老林中原生態(tài)的野果,味道極好,更是泡酒的上佳之物。
盛夏之初的一個下午,我曾經(jīng)漫步到黃家溝的山坳里,在一棵大樹下讀一本泛黃的經(jīng)卷,四言八句看得入迷時,山坡傳來粗獷的喊聲:“各家各戶注意了,天干物燥,小心著火,一人失火,全家牽連,保護森林,人人有責……”
我站起身來,鋪天蓋地的熱浪襲來,天空一下變得黑黢黢的,悶熱異常,暴雨說來就來了。在大樹下躲雨時,草叢搖晃,幾只野兔飛快奔跑,對面的山坡上黑色的墓碑森然,山河“邀請的”草木,加入狂風暴雨的飛翔……
迎著夕陽下山,在山路上遇到相識的一位貧困戶,攀談后他熱情地邀請我吃飯。在他煙熏火燎的堂屋,我們用柴火燒洋芋,煮豬腳桿,吃酸菜紅豆湯,圍著爐火喝酒,聽他“沖鎮(zhèn)雄殼子”,擺妥泥村的故事。我們吃得花嘴花臉,哈哈大笑,泛黃的經(jīng)卷上不經(jīng)意間多了些許塵世的煙灰。
過了妥泥橋,左轉(zhuǎn)個彎,靠近鄉(xiāng)村公路的山崖上,住著巖灣村民小組的幾十戶人家。這里山路彎彎,爬過一個山坡后,10多戶人家抬頭可見。敲了半天門,很少有人在家回應(yīng),偶爾有幾個老人和孩童出來,老人身邊永遠都帶著孫輩的兒童,有的嬰幼兒還走不穩(wěn)路,在門前都被老人緊緊拽著,害怕孩子一不小心,跌下山谷。這里地少且很難種好莊稼。正是收包谷的時節(jié),河邊的包谷壯碩,漿滿籽綻,這里的包谷卻猥瑣不已,無精打采地“耷拉著頭”。
在脫貧攻堅大走訪和再排查中,巖灣不少人家都選擇了易地搬遷,有幾戶人家割舍不下土地,不愿意搬遷,就留在山坡上,青壯年外出務(wù)工去了,家里的土地與父母相伴,也慢慢衰老了。空蕩蕩的房子里住著一兩個人,狗尾草起伏的地里,幾只瘦骨嶙峋的狗躲在里面,不屑理會我們。
河流不會輕易改向的,生活艱難但還得繼續(xù)。妥泥村的海拔不是陡峭的,但也絕不是順著河流而蜿蜒的,雨薩坡村民小組就略高一些。
在巖灣村民小組的上面,就是曾經(jīng)富足過的雨薩村民小組。這個村民小組20年前甚至更早的時間就嘗到土地帶來的甜頭。這里地勢高,之前居住的人不多,人均占有耕地多。在艱苦的年代,這里種植的包谷、大豆和板栗等基本可以滿足生活所需,老百姓吃飯不成問題,成了妥泥人羨慕的地兒。時過境遷,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開始向東南沿海城市和全國各地流動,雨薩一些人還滿足于“有飯吃就行”的簡單愿望,在觀望中被很多外出務(wù)工者返鄉(xiāng)修建的大房子和購置的電器驚醒,也跟著出去打工掙錢了。失去先機的村民當然也有干得好的,但總體的經(jīng)濟收入明顯比其他村民小組遜色一點。
近年來,因為扶貧政策的深入,這里的很多人選擇了易地搬遷到城里,安置小區(qū)居住的仍是老人和孩子。在外打工難得回家一趟的年輕人,鎮(zhèn)雄縣城或以勒的安置小區(qū)成了他們落腳的一站。
與雨薩村民小組隔坡相連的海子村民小組海拔最高。建在山坡上的村落以一條通往云嶺村的公路為中心,星羅棋布地分散著房屋。這里和鎮(zhèn)雄的很多地方相似,地下曾經(jīng)出產(chǎn)優(yōu)質(zhì)煤炭,多年前一直有人開采,從其他鄉(xiāng)鎮(zhèn)、村組直接開采到村莊的下面,很多人沒有選擇,在這山坡上起房蓋屋。
在脫貧攻堅的號角吹響后,國土資源部門會同相關(guān)部門經(jīng)過多次反復(fù)勘察后,確定這是地質(zhì)災(zāi)害的影響區(qū),動員群眾搬遷,大部分群眾選擇了搬遷,距離影響區(qū)較遠的一些群眾則割舍不下房屋和地產(chǎn),留在這里廝守土地。
夏夜,在農(nóng)戶自發(fā)修建的連戶路上夜行,蟬鳴與狗吠交織,星星點點的農(nóng)舍暗示著這里的人間煙火,裹葉子煙的老者倚靠在核桃樹、板栗樹下“沖殼子”,納毛布底鞋子的老嫗,擺談著東家長西家短,嘮嗑著張家碗大李家碗小的閑人,談?wù)撝l(xiāng)場上十塊錢一碗的米線有幾根,偶有人說起在外務(wù)工的兒女,長吁短嘆與顯擺此起彼落。明月升起,很多人才想起豬廄里的豬餓得“嗷嗷”叫,孫子的作業(yè)還沒有檢查簽字,火上還煮著一鍋紅豆,慌忙火急地四散回家。
日子一天天過去,搬遷出去的群眾逐漸適應(yīng)了城市生活,孩子讀書不用跋山涉水,回鄉(xiāng)衣著光鮮,很多人沉默了。海子這個人煙逐漸稀少的村落,落寞還在繼續(xù)。
順著連戶路下行,就是埡口村民小組。這是一個奇特的村莊,地勢像極了一把椅子,背后的山是海子,冬天刺骨的北風吹來,順著海子山梁回旋一下就跑了,冬天在一閃念中就過了。南面的一片山坡地勢略高,夏天來了,火急火燎的南風順坡而下,吹醒莊稼和漫山遍野的杜鵑。東面是連綿起伏的莊稼,再往前就是銀廠溝了,這個遠遠看去像一只獅子的山,30多年前曾經(jīng)盛產(chǎn)硫黃,廢棄后的山坡還有硫黃渣土,那些踩上去松軟的硫黃渣經(jīng)過雨水沖刷,已經(jīng)被野草和不知名的樹木逐漸覆蓋,埡口上的村莊手握時間的劍,冷冷地指向銀廠溝這個讓人喘息的地方,大自然修復(fù)草木,艱難地面對著時間悄然的戕害和水土流失的殺伐。
如果不是硫黃的過度開采,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埡口面對的日月鎖水口和太極圖,是上天賜予妥泥的盛大禮物,這個山河挾持的村莊,是振翅欲飛的鳳凰,但山溝里遭遇的流水之患和青山之結(jié),還需要一些時日慢慢松綁。
走下連戶路,經(jīng)過一片莊稼地,包谷和花椒的香味摻雜,村莊的房子開始密起來,這里就是村委會所在地的槽門村民小組。
槽門這個奇怪的名字對曾經(jīng)當過大灣鎮(zhèn)(時為大灣公社)黨委書記、鎮(zhèn)雄縣原林業(yè)局局長的鄧生林老人來說,是妥泥乃至大灣的變遷寫照。他說,大灣的歷史用幾個字就可以總結(jié)——陳家開場(鄉(xiāng)場)、隴家助興、國家中興。
這個73歲的老人在任時,就把戶口遷到這個村莊,退休后就定居于此。一次性了斷工齡后,老人聘請工匠,帶著家人在山坳里修建了一座端木之屋、青石之宅,每天耕讀之余就在村里轉(zhuǎn)悠,村里修路、種樹、找水源或哪家有點大事小事都喜歡請老書記來說道說道!老人也樂此不疲,樂呵呵地忙出忙進。他喜歡讀書寫字,每天帶著老伴在地里忙活,栽瓜種豆,養(yǎng)雞養(yǎng)豬,身體出奇地好,5個孩子通過奮斗有了公職,去年,在大灣鎮(zhèn)衛(wèi)生院的長女退休了,來接老人進城,老人住不慣,去了幾天就跑回來了。
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坐在老人的院落里,老人介紹道:槽門所在地面對妥泥河,是一條鯉魚奔沙灘的地勢,這里有山有水,草木蔥郁,適合讀書人居住,在這個村落里,更多的人選擇外出務(wù)工,留下來在這里默默讀書的孩子少了,但每年妥泥村都有被錄取到全國高校的大學生,今年槽門有一位孩子以近600分的高考成績,被國內(nèi)一所知名大學錄取。對于很多人家的孩子放棄讀書早早選擇外出務(wù)工,老人感慨萬千,貧困的村莊,現(xiàn)實的生存壓倒了一切,一邊是生活的壓力,一邊是夢想的遠方。幸運的是,在扶貧的道路上,“控輟保學”成了硬指標,適齡兒童得以繼續(xù)返校就讀。妥泥村有兩所小學,校舍修建得比村委會和農(nóng)舍還氣派,學生有營養(yǎng)餐和免費就讀的保障,一些貧困戶的孩子有“雨露計劃”等資助措施支撐,學校里就讀的孩子多了,學習氣氛和學習效果明顯提升,從這里走出去的孩子有了更廣闊的未來。
槽門是“騎在妥泥村鯉魚背上”的村莊,曾有民謠這樣唱道:“好個泥納灣,鯉魚奔沙灘,哪家來葬著,子孫做高官!”據(jù)說,新中國成立前這里人煙稀少,民謠傳開后,有不少鎮(zhèn)雄城里人、大灣集鎮(zhèn)上的人以及四川、貴州人搬遷來此居住,逐漸成了妥泥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成了村莊的“中心”和“心臟”。
田坎村民小組在妥泥河旁,一條通往大灣鎮(zhèn)的公路從旁喧鬧穿過,這是從昭通出發(fā),過大關(guān),經(jīng)鹽津豆沙關(guān)、柿子壩、廟壩,到彝良縣牛街、柳溪、洛旺,抵達鎮(zhèn)雄的鳳翥、威信的大落腳后,轉(zhuǎn)個彎就到鎮(zhèn)雄的瓜雄,最后抵達妥泥的最佳路線。因為交通的緣故,田坎是大雄古邦河流向高山過度的典型地區(qū),這里家家戶戶修房子都喜歡挑出陽臺,一些經(jīng)濟條件好的還支起羅馬柱,安起落地窗。由于村民臨河而居,遠山近水,村莊里有人推石磨豆花售賣,有人就在路邊開個小雜貨鋪,賣一些低端的生活用品。我就在一個小土雜店里,買到了瓶身覆滿灰塵10多年前的威信老酒。這里的人豪氣,本來生意不好,兩瓶酒只要幾十塊錢,我后來不時光顧這店,5塊錢一把的蚊香、30元錢一雙的毛布底鞋是我駐村扶貧的行頭之一。
村民們離開家鄉(xiāng)轉(zhuǎn)出山谷前,都會向著故鄉(xiāng)的方向張望。走下公路的左邊,妥泥河畔的兩岸有人家居住,搖尾吃草的牛全然不理會有人經(jīng)過,夜不閉戶的門前總有一只看家狗蹲伏著,河岸沙灘上瘋長的沙棘紅彤彤,頑強的水芹菜綠油油,不遠處那座必經(jīng)的小木橋在洪水中被沖走了。這里外出務(wù)工的人多,而且大多是擁有一定技能的人,因此,家境普遍殷實。
一座橋突然橫亙在妥泥河上,將田坎這個小小的自然村一分為二,卻連通了云南和四川兩省的商貿(mào)和文化。這座橋就是鄭公橋。
拱橋建于1941年,用料是三尺見方的青石,都是經(jīng)工匠精心雕鑿,大小一致,紋路清晰,堆砌時,人們巧妙根據(jù)力學原理,互相拉撐,互相攀附,千鈞重卻穩(wěn)如磐,歷經(jīng)風雨,卻不見一絲松動,依舊發(fā)揮著功用……
踏上異鄉(xiāng)之途的人,如果要去以勒坐高鐵趕往大城市,就要爬一段小陡坡,這個沿路都是房屋的村落就是青杠,村子在新時代浩大的發(fā)展主題里十分尋常,水泥磚砌的磚房,一般都沒有超過三層,只要是擠得下一幢房屋的地方就有房子,就有孩童和老人進進出出。
順著公路轉(zhuǎn)個彎,一段平整的水泥路面剛剛硬化完,這是通往窩凼的必經(jīng)之路,妥泥村海拔最低的窩凼村民小組,以低到泥土的姿勢,向山谷告別,向妥泥河俯身。沾了河流的熱烈,這里是妥泥經(jīng)濟林果產(chǎn)業(yè)基地,當?shù)卮迕裨谡囊龑?dǎo)下,多年前就種下枇杷、花椒等經(jīng)濟林果,還有花生、核桃、板栗等地方特產(chǎn)。如今,枇杷已經(jīng)進入豐產(chǎn)期,這里的枇杷個大、皮薄、肉厚、味美。比鴿蛋大一些比雞蛋小一些的枇杷綴滿枝頭,鎮(zhèn)雄人爭相購買這里的枇杷饋贈親友,妥泥村的北望之處、公路邊成了繁忙的枇杷交易處。雖然有特色產(chǎn)業(yè),近年來又發(fā)展了辣椒、藍莓等產(chǎn)業(yè),并引導(dǎo)村民科學種植,目前,這些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開始一天天見成效,日漸成為當?shù)匾豁椫匾慕?jīng)濟來源。

 尹默? 原名楊明,昭通市昭陽區(qū)人,現(xiàn)供職于昭通日報社,為云南有突出貢獻的新聞工作者。他的作品獲第23屆、第27屆云南新聞獎一等獎和第6屆云南報業(yè)新聞獎一等獎等獎項,獲省級以上新聞獎二、三等獎百余次,詩文發(fā)表于《星星》《海拔》《散文家》《散文詩世界》《西部散文選刊》等,并已收錄于其出版的文學、新聞作品集中。他還編劇過長篇紀錄片《穿越金沙江》《金沙江大移民》劇本,編劇、導(dǎo)演過《摩托車記者》《農(nóng)民工楊洪祥》等微電影作品。
尹默? 原名楊明,昭通市昭陽區(qū)人,現(xiàn)供職于昭通日報社,為云南有突出貢獻的新聞工作者。他的作品獲第23屆、第27屆云南新聞獎一等獎和第6屆云南報業(yè)新聞獎一等獎等獎項,獲省級以上新聞獎二、三等獎百余次,詩文發(fā)表于《星星》《海拔》《散文家》《散文詩世界》《西部散文選刊》等,并已收錄于其出版的文學、新聞作品集中。他還編劇過長篇紀錄片《穿越金沙江》《金沙江大移民》劇本,編劇、導(dǎo)演過《摩托車記者》《農(nóng)民工楊洪祥》等微電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