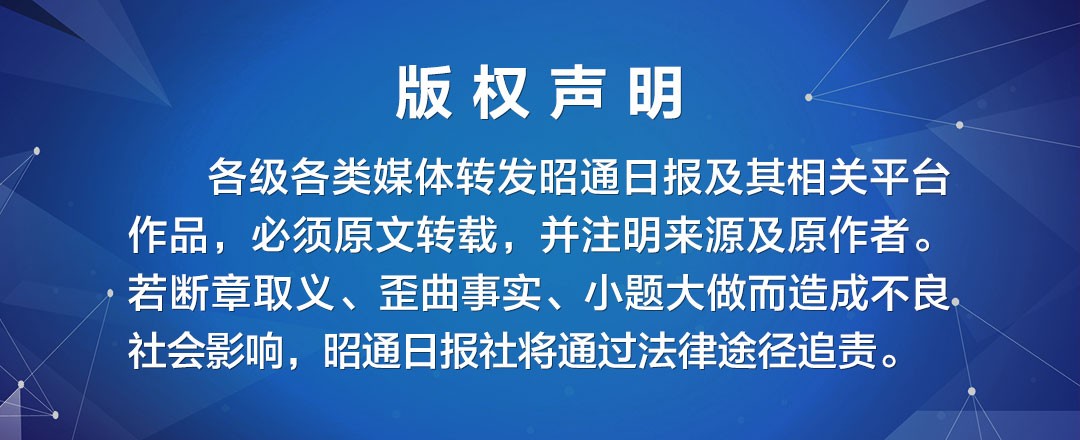2021-02-02 12:20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一、神
?滴答的雨聲敲醒了白晝的大門,微光從窗戶透進(jìn)來(lái)。這是九月的光和九月的雨,雨水吻遍草葉和花蕊。在八月,滑過(guò)草叢的那條蛇,已經(jīng)沒(méi)了蹤跡。我站在晨光初現(xiàn)的老核桃樹(shù)下,想起母親說(shuō)過(guò)的話“:如果在八月的傍晚有蛇入門,那一定是故去的人歸來(lái)。”我不明白一個(gè)故去的人,是如何變成蛇,又是怎么找到搬遷過(guò)數(shù)次的家門的。
母親又說(shuō)“:人無(wú)論生前還是死后,都有神陪伴,生時(shí)神跟在你身后護(hù)佑你,死后神就走在你前面指引你。”在過(guò)去數(shù)十年的光陰里,母親的話一直在耳邊回響,而我從出生就與父母相伴,他們的種種行為方式,早就在我心中“輸入”了“有神、有鬼和有佛”的觀念。人心是永遠(yuǎn)懷著恩怨的,如同我有過(guò)傾城的悲戚,也有過(guò)莫名的歡喜。古老的山石與草木在風(fēng)吹雨打中和睦相依,自然界中的萬(wàn)物都有“靈性”。山的神、水的神、樹(shù)的神、日月的神與人類共存了幾千年“,萬(wàn)物的神皆是德昂族的神”。德昂族的村寨多在山谷,遠(yuǎn)離城鎮(zhèn),靜悄悄地通往山寨的小路上有“路神”,道路兩旁金色的稻穗屬于“谷神”,人置身在萬(wàn)物之中,被“萬(wàn)物之神”眷顧和陪伴。晨光明亮之時(shí),兩只鳥(niǎo)兒從核桃樹(shù)上飛走了,它們的神是鳳凰,鳳凰是隱身的神,用畫(huà)像指引百鳥(niǎo)。上古時(shí)代,鳳凰來(lái)過(guò)人間。德昂族人有“百鳥(niǎo)圖”記錄鳳凰來(lái)過(guò)的蹤跡。第一個(gè)畫(huà)“百鳥(niǎo)圖”的可能是我們的族長(zhǎng)、祭司、蠱婆,也可能是博學(xué)多才的王子。在顛沛流離的遷徙過(guò)程中,為了保存下“百鳥(niǎo)圖”,人們把“百鳥(niǎo)圖”文繡在族中最有威望的祭司背上,一代代相傳下來(lái)。世界不斷變化,會(huì)讓口耳相傳的劇情充滿變數(shù),更可怕的是這種變化有消融一切的本質(zhì)。“百鳥(niǎo)圖”和“水龍紋”已經(jīng)被時(shí)間消滅了,如同已經(jīng)不存在的祭司和巫師,他們被時(shí)代和時(shí)間拋棄了。門前的核桃樹(shù)引不來(lái)鳳凰,我端著一杯滾燙的咖啡,雨后的陽(yáng)光有著新鮮的香味,這樣愜意的心境,不知道母親是否有過(guò)?母親一生“敬神”卻從不尋問(wèn)神在何方,“敬鬼”卻從不問(wèn)鬼從何來(lái),“鬼神在心”的她仍舊坦然“拜佛”。母親從不稱亡魂為“鬼”,她說(shuō)那叫“故人”“八月入門的蛇是故人,只有蛇可以帶故人回人世間”,所以,很早很早以前,德昂族人就有“立蛇門”和“祭蛇樹(shù)”的習(xí)俗。
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從南亞半島還是從印度遷徙來(lái)的,也不知馬來(lái)西亞矮黑人種和高棉族哪一個(gè)是我名正言順的祖先,但這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本來(lái)就不知道自己來(lái)自何處、又要到哪里去,人如山野之間的一株草,生生滅滅,追問(wèn)的事就交給學(xué)者吧!我只要具有“神秘感”的想象力就行了,這種神秘感也許是母親賦予我的。我一直相信,這樣的神秘感通向某位酒醉的祖先,他常常跳入我的腦海,還醉醺醺地對(duì)我說(shuō):“孩子,沒(méi)關(guān)系,你們不知道我的過(guò)去。”是的,我不知道祖先的過(guò)去,除被寫(xiě)在紙上的、被口耳相傳的之外,還有許多被遺忘的故事。遺忘的就是不可尋回的。我與這些故事隔著百年或者千年,不知道千年前的祖先有酒喝嗎?
無(wú)論站在哪一座龍陽(yáng)塔下,我都固執(zhí)地認(rèn)為:塔上的那條青龍明明就是蛇首龍身,為什么一條蛇會(huì)長(zhǎng)出龍的鱗片呢?每每這個(gè)念頭一產(chǎn)生,我四周的燈就一盞接一盞地熄滅了,黑暗和無(wú)盡的孤獨(dú)就落進(jìn)我安放心靈的世界,我必須誠(chéng)實(shí)地告訴自己,我看見(jiàn)的的確就是一條蛇呀,對(duì),一條蛇。就算我一直找不到祖先與蛇的神秘關(guān)系,塔上的,仍然是一條蛇。我這樣堅(jiān)持,不知道我的族人會(huì)不會(huì)朝我扔“臭雞蛋”呢?九頭蛇是高棉族的標(biāo)志,印度濕婆神的三只眼睛中有一只眼睛是蛇,如果我一定要把“龍陽(yáng)塔”(德昂族的吉祥圖案,上面刻有“青龍媽媽”和“太陽(yáng)爸爸”)上的龍當(dāng)蛇的話,這兩點(diǎn)可能是我唯一能找到的一點(diǎn)關(guān)聯(lián)吧?其實(shí),印度繪畫(huà)中的蛇與龍是很相似的,印度人認(rèn)為“蛇是神圣的動(dòng)物”,國(guó)內(nèi)也有一些民族稱蛇為“地龍”,那么蛇會(huì)不會(huì)就是龍的原身呢?
我的母親就視蛇為神。有一次,我們建在江邊蘆葦叢中的油毛氈房的家里就來(lái)了一條黑蛇。它從竹籬笆門的縫隙爬進(jìn)來(lái),緩慢地在屋里轉(zhuǎn)悠,像是迷路了的樣子,我被嚇得驚叫的聲音,加速了它迷亂地轉(zhuǎn)圈。母親提來(lái)米袋,向門口撒出了一條“米路”,蛇慢悠悠地順著“米路”出門去了。母親說(shuō):“那是死去多年的外婆來(lái)家了。”這件事在我心里擱置了許久許久,我一直想知道母親和蛇是如何達(dá)成相認(rèn)的默契的。
今年八月,我剛搬進(jìn)的山中新居,也來(lái)了一條黑蛇。這時(shí)正值黃昏,我驚慌失措,急忙跑進(jìn)屋去找米缸,可是缸里沒(méi)有一粒米。心底里突然冒出:“這條蛇可能是條毒蛇。”這念頭一起,隨之我吐出了一句“:把它打死吧?”。來(lái)串門的朱先生說(shuō):“不,不!”我們來(lái)來(lái)回回地跑動(dòng)著尋找指引它出門的工具,最后用一把鐵鏟把它送出了門。當(dāng)夜,我夢(mèng)見(jiàn)父親穿著一件黑衣裳,用寬大的衣袖蒙著臉跟我說(shuō)話。四周靜靜的,父親低低的聲音把門窗震得搖晃,窗簾也胡亂地飄起來(lái)。我無(wú)法接受父親變成了一條蛇,并以蛇的形態(tài)來(lái)看我,我寧愿相信這條蛇是母親。
母親從小為我構(gòu)筑了一個(gè)虛實(shí)參半的“神鬼世界”,“虛”是“實(shí)”的看不見(jiàn),“實(shí)”是“虛”的“假面具”。在我心里鬼是鬼,也是神;神是神,也是鬼。某年的一個(gè)文學(xué)活動(dòng)現(xiàn)場(chǎng),主持人問(wèn)了我一些關(guān)于我的詩(shī)歌中出現(xiàn)的問(wèn)題,我回答說(shuō)“人心里一直住著一個(gè)鬼”,被在場(chǎng)的某位名家當(dāng)場(chǎng)抨擊,我當(dāng)時(shí)回答不了,卻也沒(méi)有為在這樣的場(chǎng)合啞口無(wú)言而尷尬,我以沉默的微笑回應(yīng)著那位名家,主持人也恰到好處地幫我解了圍。就算到了今天,我也相信我心里住著“一個(gè)善惡相交的‘鬼’”,這個(gè)“鬼”有時(shí)也是我的“神”,有這種感應(yīng)是我之幸。在我這里,人、鬼、神不是對(duì)立的,而是形影相隨、和諧共存的。
母親口中沒(méi)有“惡鬼”,只有變得“不善良了的鬼”。母親思維里的鬼也不是人死后變成的鬼,而是萬(wàn)物本身具有的“靈魂”。凡遇“不善良了的鬼”,母親就會(huì)用茶豆煮雞蛋來(lái)相送,母親也從來(lái)不說(shuō)要“攆鬼”,而是說(shuō)要“送鬼”。母親“送鬼”的儀式有好多種,有深夜撒米,有用金竹葉來(lái)灑水,有用桃樹(shù)枝掃地后將桃樹(shù)枝立在門邊。只有“不善良了的鬼”出沒(méi)后,才會(huì)用“茶豆煮雞蛋送到蛇樹(shù)下”這個(gè)祭祀,而蛇樹(shù)是母親在僻靜地帶找來(lái)的一棵紅木樹(shù),就是樹(shù)皮上有些會(huì)扎人的小絨毛刺的那種,紅木樹(shù)會(huì)開(kāi)一種細(xì)碎的小白花,也許是扎人的小絨毛賦予了樹(shù)的“神性”,母親才會(huì)選它作為我們的“蛇樹(shù)”,將“不善良了的鬼”送給它收納。
據(jù)說(shuō)幾千年前,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認(rèn)為蛇是“創(chuàng)世之神”,也有遺址發(fā)現(xiàn)古老的泥板上“繪有一條嘴里銜著自己尾巴、身體圍成圓環(huán)的大蛇”,蘇美爾人認(rèn)為這條巨蛇是創(chuàng)世者的仆從,蛇頭銜蛇尾的造型,象征著世界萬(wàn)物的周而復(fù)始。古埃及人也認(rèn)為蛇類是冥界的守衛(wèi)者,埃及神話中,蛇神賽托也是將世界纏繞起來(lái)的形象,蛇是埃及神話里出現(xiàn)最多的動(dòng)物之一。古滇文化中的蛇更豐富多彩,蛇形青銅器的發(fā)現(xiàn),說(shuō)明了古滇人的思想觀念中“蛇神崇拜”是不可或缺的。我相信,蛇與我們也有著神圣的關(guān)系。
就像選擇蛇樹(shù)一樣,母親仿佛與生俱來(lái)就有自己挑選“自己的神”的本能。我也是如此,我選“光”做我的“神”,我所有沉默的禱告都向著光。光起源于萬(wàn)物,萬(wàn)物也就成了我的神。在原子世界的中心,太陽(yáng)千萬(wàn)年的光與熱,照拂著宇宙萬(wàn)物和人間,給予人類光、風(fēng)、水、空氣、雨水、沙漠、食物、廣袤土地、富于創(chuàng)造的心靈和至高的信仰,這些足夠我在冷漠中獲得溫暖、悲苦中獲得安然、理想中獲得純潔。這些滿當(dāng)當(dāng)?shù)墨@得,為我每次遇到的無(wú)路而退提供了退路。
二、樹(shù)
有一次,我坐在飛機(jī)上,透過(guò)舷窗,看見(jiàn)一朵朵白云像千軍萬(wàn)馬迎過(guò)來(lái),不為飛機(jī)側(cè)身,也不躲避飛機(jī)的翅膀。低頭望去,只見(jiàn)大地像藏在遠(yuǎn)古時(shí)期的水底,山峰、江河、道路和綠色的森林,搖晃著、透明著,像是虛構(gòu)的、正在舉行著的一場(chǎng)祭祀,而我始終是個(gè)局外人。
德昂族人最初擁有的樹(shù)應(yīng)該是南方叢林中的楠木、柚木、花梨木、栗木、鹽膚木等雜樹(shù),當(dāng)然也包含了那些已消失了的樹(shù)。菩提樹(shù)是與奘房同時(shí)期進(jìn)入村寨的,佛祖釋迦牟尼在菩提樹(shù)下修成正果之后,菩提樹(shù)就成了“神圣的信仰之樹(shù)”。母親說(shuō),她們家族稱菩提樹(shù)為“龍樹(shù)”,“龍樹(shù)”翻譯成漢語(yǔ)就是“圣樹(shù)”之意。有奘房的地方必有菩提樹(shù)。春天,四周的田壟上,青禾抽著枝葉,白鷺在菩提樹(shù)間飛飛落落,有種穿越“輪回之門”、通向未知旅程的恍惚。菩提樹(shù)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植下了不朽與完美的意識(shí),幫助我完成此生的圓滿與渴望。
榕樹(shù),我們當(dāng)?shù)厝私写笄鄻?shù)。村寨中,路旁和奘房四周都有大青樹(shù)。德昂族人敬仰大青樹(shù)。傳說(shuō)大青樹(shù)上住著神,也住著鬼,既通神又通靈。大青樹(shù)還是德昂人靈的棲息地。說(shuō)到底,我們是“尋根”思想的遺民,寧死守著古老茶農(nóng)的名分,以填補(bǔ)沒(méi)有機(jī)會(huì)親歷繁榮歷史的遺憾,還偏執(zhí)地固守著民族感越來(lái)越薄弱的宿命。想到外婆、母親、姨媽和舅舅們,我忽然間就變成了他們“陌生的親人”。這種遭遇和心情,如同午夜的雷雨,有著非虛構(gòu)的飽滿記憶。有的村寨會(huì)把長(zhǎng)在寨子中的某一棵大青樹(shù)立為“寨心樹(shù)”,這棵大青樹(shù)也不一定是長(zhǎng)在寨子的中心地帶,但“寨心樹(shù)”一定是高大挺拔、枝繁葉茂、四季常青的。一旦選定這個(gè)寨子的“寨心樹(shù)”,它就是這寨子的中心世,人們以此為中心建房蓋屋,祭祀朝拜,同時(shí)賦予這棵“寨心樹(shù)”超自然的“神的力量”,讓它保護(hù)村莊里的一切。而那些遠(yuǎn)離村寨、獨(dú)木成林的古老大青樹(shù)就會(huì)被村民選成各家的“蛇樹(shù)”,也就是“鬼樹(shù)”。在盤根錯(cuò)節(jié)的“鬼樹(shù)”身上纏白線、供奉芭蕉和米飯團(tuán),給那些被人們從患疾的人身上攆出來(lái)的“鬼”。這些“蛇樹(shù)”像叢林一樣駭人又陰森,帶著未知的神秘和某種“沒(méi)來(lái)由的慰藉”。
不過(guò),這樣的景象只存在記憶之中了,如今“獨(dú)木成林”已經(jīng)是故鄉(xiāng)著名的風(fēng)景旅游點(diǎn)。人類自古就習(xí)慣寄情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那些我曾經(jīng)以為棲身在大青樹(shù)上的“神”“鬼”不知遷移到了哪里。再回山寨,蔚藍(lán)的天際聚集著祥云,天幕下,年年風(fēng)調(diào)雨順,人事安寧。
每一棵樹(shù)都是人類的奇跡,茶樹(shù)是我心里最憂郁的一棵。茶樹(shù)承載了我對(duì)生命起源的認(rèn)知,茶樹(shù)是祖母,也許是外祖母。從農(nóng)耕時(shí)代至今,德昂族人種茶、制茶、茶、禮茶。古老的茶農(nóng),一直守候著古老的茶園,守候著我們生命的起源。
三、歌
我一直盼望著有一天,我能用德昂文寫(xiě)出一首詩(shī)。這個(gè)夢(mèng)從很久以前就開(kāi)始了,只是那些難寫(xiě)更難讀的字母,我至今未能讀準(zhǔn)確,自己拿著一個(gè)識(shí)字本,一去緬甸就找人問(wèn),對(duì)德昂文精通的又都不能講漢語(yǔ),會(huì)講漢語(yǔ)的人又不識(shí)德昂文。每每下決心之后,我就用“灰心”來(lái)原諒自己被“繞舌音節(jié)”的拒絕。
我內(nèi)心有著深重的愧疚,愧疚于祖先記錄下的歷史、古歌、曲調(diào),我只能用漢語(yǔ)的語(yǔ)境來(lái)理解它們,我除了血統(tǒng)和遺傳之外,與母文化有著巨大的文化斷層和隔閡。在這個(gè)困境里,我無(wú)法用這些圓形的字體寫(xiě)一封家書(shū),更別說(shuō)寫(xiě)一首詩(shī)了。就像“結(jié)繩記事”時(shí)期一樣,我要用自己的符號(hào),制造自己的語(yǔ)言,然后才能讀懂自己的內(nèi)心。我是一個(gè)失語(yǔ)的德昂人,彷徨、焦慮又滿含希望的生命,被驅(qū)離古老的傳統(tǒng),是一種注定要走散的未來(lái)。
德昂族人的山歌是用手壓住嘴角、輕輕地“哼”出來(lái)的,這些歌謠就像月亮下小溪水的潺潺流淌。幾百年來(lái),一代代德昂人就用這種簡(jiǎn)單且低調(diào)的傳唱方式,傳唱著自己的歷史和情感,每一個(gè)傳唱者富于創(chuàng)新的創(chuàng)造就成了我們的“心靈史”。是的,用歌來(lái)唱天地宇宙,唱鬼神和萬(wàn)物,唱悲喜,唱愛(ài)恨,唱生死。2013年10月2日,我獲得了一次傾心的聆聽(tīng)。那天,天還未亮就起床,帶著敬畏的心去三臺(tái)山,聽(tīng)李臘翁老爹唱古歌,并錄制下來(lái)。這是我多年的愿望,雖然錄制可能會(huì)因我的不專業(yè)而不理,但我聞到了“人親骨頭香”的味道。那天,我在李臘翁老爹家待了一天,我喜歡老爹臉上那一道道歲月留下的痕跡,那是風(fēng)霜雪雨“豐富過(guò)”的人生。在他的歌聲中,我聽(tīng)得見(jiàn)“血脈相撞的聲音”。
奘房上空的晨光,云朵像自由的心,稻子黃了,我仿佛是為了見(jiàn)證米的潔白才來(lái)。下面是個(gè)“竹節(jié)上”的村莊,籬下有瓜,架上有豆,老爹唱的每一個(gè)音節(jié),流淌著母語(yǔ)的漣漪,“創(chuàng)世歌”“田野曲”“賽可調(diào)”“德昂簫”和那些古遺址中沒(méi)落的痕跡,離我很近很近。我是被歌聲引來(lái),也是被歌聲送走的人,“風(fēng)里來(lái)的人,必定要向雨里去”。
四、門
德昂族的古遺址,在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有記載的只有10余處,大多被時(shí)間湮沒(méi)成記憶了,還可以看見(jiàn)清晰痕跡的僅有弄璋鎮(zhèn)南算村的一座古佛寺了。這是德昂族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建筑,經(jīng)歷了百年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靜悄悄地“偏居”在這個(gè)寧?kù)o的村莊里。雖然10年前就被列為省級(jí)文物保護(hù)文物,但其破敗證明了它的無(wú)人問(wèn)津。幾經(jīng)劫難,破敗仍存,幸得南算村傣族人民的守護(hù)。村里的老人說(shuō),因?yàn)槭堑掳喝肆粝碌模?/span>叫“奘崩龍”,漢譯就是“崩龍佛寺”之意。更為寶貴的是,佛寺里保存著一座德昂木雕,雖然不完整了,但對(duì)研究德昂族古代建筑有著非常重要的價(jià)值。最讓人驚喜的是寺里還珍存著一面“德昂大木鼓”。
這座德昂古建筑呈長(zhǎng)方形三疊式,有特別鮮明的德昂族木建筑風(fēng)格,與我在緬甸南坎見(jiàn)到的德昂古民居風(fēng)格相似。據(jù)說(shuō)佛寺屋檐上原來(lái)有八只龍頭的飛檐,在時(shí)間的更迭之中,室外的雕飾和墻、瓦片都已被更換過(guò),室內(nèi)德昂族木雕和石雕卻被完好地保存下來(lái),算得上是國(guó)內(nèi)唯一一間可以見(jiàn)證德昂族古建筑的建筑物。佛寺是全木建造的,所用之木,木質(zhì)堅(jiān)硬,被時(shí)間磨礪成深褐色,我竟分辨不出是何樹(shù)之木。梁的柱子粗大,柱底為圓形,有雕琢的石墩,瓦頂、四壁木梁上都有浮雕。最完好的一處浮雕是在木房架的掛枋拱木,木雕刻,未上彩繪,圖案有鳳朝陽(yáng)、龍戲珠及各種花卉。木格窗,不是雕花窗。我想,從房子的格局來(lái)看,原來(lái)的窗子肯定是雕花窗,可能是后來(lái)更換過(guò)了。
幾經(jīng)修葺,佛寺面積縮小,還拆換過(guò)幾根橫梁,木柱腳因風(fēng)雨侵蝕而腐朽,被鋸去一截,原來(lái)一樓高三米多,人可直立行走,牛群也常在下面乘涼休息,現(xiàn)在只有一米了;原來(lái)的三疊進(jìn),也撤了一疊,變成如今的二疊式。無(wú)論怎么變,還能保存著這些,就是我們德昂族的福祉了。我相信這些木雕是滇西德昂族建筑史上的“先行者”,手工木刻的龍、鳳、蜻蜓和喜鵲都有著德昂人粗糙的繪制風(fēng)格,簡(jiǎn)潔的花朵穿斗在房梁上,停泊了百年的時(shí)光。后來(lái),經(jīng)入寺的和尚添了金粉才生動(dòng)起來(lái),風(fēng)蝕了的木屋頂,傳說(shuō)從前是銅瓦,曾經(jīng)金碧輝煌過(guò),這與族群的由盛而衰有著隱隱的含義。興衰是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人逃不脫。已湮沒(méi)的,必將是被人類共同復(fù)制的記憶。
石階、石柱、石雕,與房子的年歲一樣“。德昂大木鼓”,外形與佤族的木鼓相似。用牛皮蒙兩端和鼓面,鼓身是一根巨大的圓木雕琢而成,長(zhǎng)兩米多,鼓腰四米左右,木心刳空,鼓頭不太圓,尾端較圓,漆黑,與現(xiàn)今的德昂木鼓外形相差甚遠(yuǎn),我稱它是“德昂鼓王”。寂寞的“德昂鼓王”,是南算村傣族人民保護(hù)下來(lái)的,如今則成為了南算村的“保護(hù)神”,每當(dāng)喜慶之時(shí),南算村就會(huì)敲響這面古老的木鼓。寂寞的“德昂鼓王”已經(jīng)更換過(guò)多次的鼓皮,鼓尾還系了一條哈達(dá),木制的四個(gè)輪子與它相伴,陳舊的鼓輪,常常載著“鼓王”走出寺門,敲出雄厚的鼓聲,護(hù)佑人們的靈魂。
佛寺的門,據(jù)村中老人說(shuō),從前門兩邊曾有木雕刻的人像及兩只大象、兩只飛馬,后來(lái)被破壞了。現(xiàn)在我看見(jiàn)的每一扇門、每一面墻、每一根梁、每一扇窗,都透出“別離”的訊息,就好像臨行前的告別,提醒我:它們就要永遠(yuǎn)地消失而去。攏攏思緒,我想要它們都好好地生活在我的記憶里、我的孩子的記憶里、孩子的孩子們的記憶里。
族源追溯,會(huì)告訴我每一個(gè)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精神、情結(jié)和來(lái)源。我有一扇“時(shí)間的門”,走進(jìn)去是歲月內(nèi)在的種種奧妙,展現(xiàn)著時(shí)光的美;走出來(lái)是生命的躍動(dòng),是真理透過(guò)時(shí)間顯現(xiàn)出來(lái)的存在,是永恒穿過(guò)種種阻礙、從過(guò)去發(fā)生的事實(shí)中清澈的自我現(xiàn)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