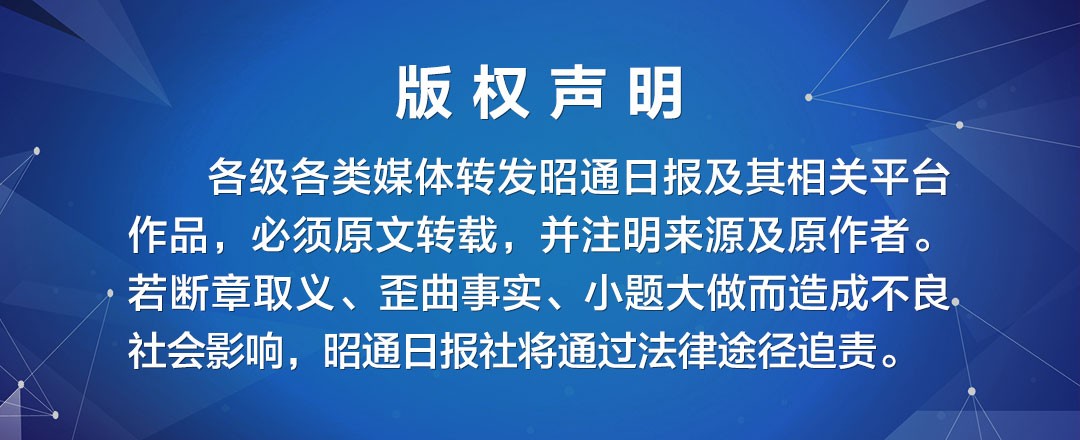2021-03-02 17:39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我不是特別想寫有關(guān)故鄉(xiāng)的文字,總覺(jué)得這個(gè)主題已經(jīng)被別人寫得很“爛”和“俗”了,但隨著年歲的增長(zhǎng),越來(lái)越覺(jué)得對(duì)于自己的故鄉(xiāng),尚有許多未盡之言,這塊從出生起我就“缺席”的土地,隨著時(shí)光的流轉(zhuǎn),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回來(lái),我身體里流淌的血液因子也開始一滴一滴地注入了某種悲傷。這種悲傷越來(lái)越濃稠,我想,如果我一直保持緘默,它會(huì)不會(huì)在我體內(nèi)凝結(jié)成固體,讓我永遠(yuǎn)化成一塊在他鄉(xiāng)的“望鄉(xiāng)石”呢?
我必須得為它寫點(diǎn)什么,留下點(diǎn)什么。
一
不得不坦承,時(shí)光就像水銀柱一般緩慢侵吞著我的記憶,故鄉(xiāng)的面貌也在這種啃噬里逐漸變得殘缺不全。如果硬要回憶,那勉強(qiáng)可說(shuō)的,就是四五歲時(shí)第一次在父母的帶領(lǐng)下,和哥哥一起回老家時(shí),看到的那條在田間里涓涓流淌的小河以及高中畢業(yè)第二次同父親回老家時(shí),出現(xiàn)在衣服里面把我嚇得半死的“虱子”。
我并不想感傷那些如今已不復(fù)存在的溪流和泥鰍、小蟹,田地和村莊。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大地與人的連接正在以各種方式異化——?dú)v史發(fā)展下的城鄉(xiāng)面目在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所不同,我并無(wú)可能評(píng)判這塊大地在現(xiàn)在和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而千萬(wàn)年前,哪種面貌更好一些?
所以,我并不想感傷。唯有失落,因?yàn)槲疫@一生的時(shí)光曾有那么一丁點(diǎn)兒是留在這里的,而我的生命,還是得回來(lái)。父親、爺爺,對(duì)一個(gè)家族的兩代人來(lái)說(shuō),這塊土地早已烙下了“足夠的印記”。
當(dāng)我的身體和這塊土地漸行漸遠(yuǎn)的時(shí)候,內(nèi)心有一股緩慢滋生的力量,隱秘地、不可阻攔地和皮囊逆向而行。
二
很多年以前,在我還是個(gè)小女生的時(shí)候,乘坐著一架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簡(jiǎn)直就是龐然大物的“波音737”飛機(jī),從邊陲之地起飛,越過(guò)云貴高原,穿越重重迷霧,到了比天空更加蒼茫的北京。17歲參軍的叔叔在那里已經(jīng)安家落戶了,嬸嬸是某學(xué)校的英語(yǔ)老師,爺爺也在我去的前一個(gè)月被接到了北京。
飛機(jī)在下降,而我,貼在飛機(jī)的舷窗邊,貪婪地往下看:巨大的城市像一幅遼闊的畫,中間的空氣卻像一層深灰色的濃稠的紗,使來(lái)自地面的燈光閃閃爍爍,仿佛天地倒置,星辰在下。
到了北京,除了好奇,就是難受。每一個(gè)人,離鄉(xiāng)的人,我想,最先作祟的就是“胃”。我們的胃比我們更有“鄉(xiāng)愁”,更眷戀某一種食物。比如洋芋,比如酸菜,比如大米飯,比如所有不加小粉煮出來(lái)的任何一種湯。某日,我在廚房準(zhǔn)備泡面吃,見(jiàn)爺爺緊皺著眉頭踱著步走進(jìn)來(lái),手里捏著一個(gè)饅頭,嘴里喃喃地說(shuō):“跟吃豬食一樣!”我忍不住笑了。原來(lái)爺爺也不習(xí)慣哦。
我已經(jīng)記不清當(dāng)時(shí)叔叔所在院子的具體位置了,但應(yīng)該是很偏僻的,因?yàn)樵诒本┠菢臃比A的京城里,居然還有一大片的地上,種著一些蔬菜。我因?yàn)榭偸桥磺宄卟说钠贩N而被叔叔笑話。
長(zhǎng)安街、天安門、長(zhǎng)城、故宮,我像一個(gè)陌生的誤入此地的游蕩者,唯一的存在感是看見(jiàn)了鏡子里的自己,那個(gè)以為自己已經(jīng)長(zhǎng)大了的小女孩兒。
我離開北京后不久,爺爺也回到了老家。那個(gè)曾經(jīng)可以肩挑一百公斤的矍鑠老人回到昭通后便一病不起,北京那一次竟成了最后的見(jiàn)面。直到如今,我腦海里的爺爺仍然是那個(gè)穿一襲深藍(lán)色土布長(zhǎng)袍、裹著一個(gè)大大的黑色包頭、臉膛瘦削、布滿老人斑,似笑非笑看著叔叔院子里的那方菜地,仿佛在“嘲笑它太袖珍”的爺爺。
離開故土的人,為何會(huì)變得如此虛弱呢?
那是我第二次遠(yuǎn)離故土。
三
就跟東北人喜歡稱呼女孩子為“丫頭”一樣,“姑娘”這稱呼是我昭通老家人喜歡用的。自小被父親和幾個(gè)叔叔叫著“姑娘”長(zhǎng)大,一直到現(xiàn)在仍然這樣叫,每次說(shuō)話前都會(huì)清清楚楚地喚一聲“姑娘”。我呢,一聽(tīng)到這聲稱呼,心里頭就先“柔軟了三分,聽(tīng)話了三分”。
某日,一位昭通籍的老師發(fā)“微信”給我的時(shí)候,居然以“喬姑娘”相稱,我這心,立刻就“化”了,立刻就“貼”了過(guò)去,仿佛對(duì)方成了我的親人。
掰著指頭算,約有20年未回過(guò)老家了——當(dāng)然,如果上一次到昭通開筆會(huì)不算的話(因?yàn)槟谴纬碎_會(huì)和住宿,哪兒也沒(méi)去)。
老李一直說(shuō)我是“冒牌的”昭通人,我特別不服氣:“憑啥我就不是昭通人呢?就因?yàn)槲覜](méi)出生在昭通嗎?那也是因?yàn)槲业髮W(xué)畢業(yè)后就到瑞麗去,娶了我媽嘛。我在昭通的親戚還有很多呢!”
不過(guò),老李這樣說(shuō)我也是有緣由的。娘是傣族,爹是漢族,因?yàn)槌錾氐娜瘥愂沁吔贁?shù)民族地區(qū),于是戶口本上就隨娘填了傣族。后來(lái)也是因?yàn)槊褡迳矸荩疫\(yùn)地成了魯迅文學(xué)院少數(shù)民族高級(jí)研修班中的一員,所以大多人都只知道我是傣族,不知我的父親是昭通人,是漢族。當(dāng)時(shí)老李斜著眼睛說(shuō)我:“你又想混進(jìn)昭通噶?”這一個(gè)“又”字把我打擊得氣虛不敢辯駁,實(shí)在是有理說(shuō)不清,先是“混”進(jìn)了少數(shù)民族作家群,現(xiàn)在“又”想混進(jìn)昭通作家群——誰(shuí)都知道昭通的文學(xué)群在中國(guó)赫赫有名,作家們將國(guó)內(nèi)所有大獎(jiǎng)小獎(jiǎng)都已收入囊中。所以我這心還是很虛的:我為何竟沒(méi)有遺傳到這等天分?
2019年5月,我參加云南省報(bào)告文學(xué)協(xié)會(huì)的年會(huì),地點(diǎn)就在老家昭通。
19日飛到昆明,次日清晨,麗海和老李到酒店接了我,我們都坐一輛車從昆明出發(fā)。車上,老李開玩笑說(shuō)我這是“榮歸故里”。我一下子臉熱心跳,羞愧起來(lái)。明知這不過(guò)是一句玩笑話,卻在心里跟自己“較真”了起來(lái)。
古人要富貴了才歸故鄉(xiāng),而我半生一事無(wú)成,財(cái)不足置辦豪車大宅,權(quán)僅夠支使家里一只小狗,何謂“榮歸”?
父親是家中的老大,畢業(yè)后原本是應(yīng)該分在昆明軍區(qū)做一名軍人的,卻陰差陽(yáng)錯(cuò),“命運(yùn)拐了個(gè)彎”,被分配到了瑞麗。也就在這里,他和母親相遇了,完成了命定的一場(chǎng)姻緣。和所有相愛(ài)而結(jié)合的男女一樣,對(duì)愛(ài)情和婚姻抱有天然的樂(lè)觀主義進(jìn)入,后來(lái)卻不得不狼狽不堪地掙扎著游出這方“泥塘”。
若是以世俗標(biāo)準(zhǔn)來(lái)看,當(dāng)時(shí)的父親在事業(yè)和婚姻上算是略有成就的:年紀(jì)輕輕便已進(jìn)入管理層,一兒一女。隨著父親根基日漸穩(wěn)定,老家的幾位叔伯兄弟也來(lái)到了瑞麗,各自也都有了自己的落腳點(diǎn)。這樣看,父親這一代的家族似乎進(jìn)入到了一個(gè)“鼎盛的時(shí)期”。
20世紀(jì)90年代的瑞麗,正是改革開放后最為繁茂的時(shí)期。如同泄洪的閘,人群和財(cái)富從各個(gè)通道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翡翠黃金、紅藍(lán)寶石、水晶瑪瑙……讓人目瞪口呆、應(yīng)接不暇,伴隨而來(lái)的自然還有不可測(cè)的風(fēng)險(xiǎn)和跌落。昨天還是挑著擔(dān)子賣鹵雞蛋的小販一夜之間就成了大飯店的老板,今天還是“錢包充實(shí)”的商賈,明天就成了不名一文的窮人。
如果沒(méi)有那一年的意外,我很有可能成為一位衣來(lái)伸手、飯來(lái)張口的大小姐,可是命運(yùn)之手從來(lái)不容人抵抗,它將我家撕成了碎片。人類的貪欲已是原罪,自出生便隨附而來(lái),終生與之作戰(zhàn)。父親沒(méi)有足夠的力量與意外對(duì)抗,有了很多而又想要更多,一次足夠高度的“跌落”讓他終身無(wú)法“從容地翻身”。從那次意外發(fā)生以后,父親性格大變,怨氣滿腹。我也開始畏懼每一次跟他的接觸,因?yàn)槊恳淮我?jiàn)面唯一的內(nèi)容就是聽(tīng)他罵所有的人,罵“該死的婚姻”,罵這個(gè)社會(huì),從30年前就開始?xì)v數(shù)“罪狀”。我悲哀地看著腰背尚且挺直,發(fā)須尚還黑密的父親,終于有一天,我打斷了父親的話:“爸爸,如果你一直活在過(guò)去,那你永遠(yuǎn)就沒(méi)有現(xiàn)在和未來(lái)。”“未來(lái)?我都這把年紀(jì)了,早死早好!現(xiàn)在過(guò)成什么樣子了,不要你們管!”父親依舊中氣十足。“可是,爸爸,我從小看書,看到的都是年長(zhǎng)的人可為年幼的人作表率,長(zhǎng)者都能看淡所有的爭(zhēng)斗,可是在我們家,為什么不是這樣呢?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你們之間的爭(zhēng)斗和不原諒,這是你們要教給我們的嗎?”
聽(tīng)到這句話后,父親不再發(fā)怒,突然就沉默了,低頭只呼嚕呼嚕地吸著他的水煙筒。
從那以后,再?zèng)]有聽(tīng)他抱怨過(guò)什么。整個(gè)人,突然就平和多了。
受父親那次事業(yè)下跌的影響,幾位叔叔的境遇也開始走“下坡路”。在城市生活過(guò)的他們,又如何回得去?欲歸家無(wú)人,欲渡河無(wú)船。如今,一個(gè)個(gè)如離枝的葉子散落各地,正為一家老小拼盡全力地 “和生活死磕”。
四
按照我現(xiàn)在的回憶,爺爺?shù)募覒?yīng)該是在農(nóng)村,而且有閣樓,屋子中間有個(gè)火塘,地面是由深褐色的又帶點(diǎn)紅色的膠泥土壓成,被奶奶清掃得一塵不染。屋外是一壟一壟平平整整的田地,當(dāng)時(shí)種的是紅蘿卜。記得這么清楚,是因?yàn)槲胰ネ党赃^(guò)。紅蘿卜翠綠的葉片既小又柔弱,細(xì)長(zhǎng),有一些軟軟的絨毛,我將它的葉子攏在一起,向上輕輕一拔,一根和我手腕差不多粗細(xì)的紅蘿卜便被我拔出來(lái)了。紅蘿卜纖長(zhǎng)的身體帶著濕漉漉的泥土,有一種透明的晶瑩質(zhì)感。我至今清楚地記得它入口的滋味,還帶著初冬時(shí)霜的冰冷,被霜凍過(guò)的紅蘿卜,仿佛有著一種舉世無(wú)雙的清甜,所以,這滋味,我至今不能忘記。
比之紅蘿卜,昭通的洋芋,我吃了那么多,印象卻有點(diǎn)模糊了。
洋芋是第二次回老家吃的。父親開車帶我去的。
洋芋和昭通醬,它倆是絕配,這是我那次的發(fā)現(xiàn)。
奶奶把洋芋放在屋子中間的火爐上烤,還沒(méi)烤熟,一股焦香味就像鉤子般地鉆到鼻腔里,把我的“饞蟲”給勾出來(lái)了。沒(méi)烤熟之前奶奶是不給我們碰的,直到外皮烤成了黑黑的一片,用瓦片刮成脆脆的焦黃色,她用一根筷子去試探:如果筷子能很輕松地插進(jìn)洋芋的身體里去,說(shuō)明熟了,反之則還不可以入口。熟了以后的洋芋,奶奶用兩個(gè)手指頭飛快地將它提拎起來(lái),另一只手則迅速用靛藍(lán)色的粗布衣襟接住,撣撣灰,拍打拍打,便放在一張小小的草紙上,蘸料是她早已放在土碗里的昭通醬。如果洋芋烤熟了的時(shí)候奶奶剛好不在,我們就會(huì)爭(zhēng)搶,一個(gè)個(gè)都快成年的大孩子,還像小頑童一樣地?fù)寔?lái)?yè)屓ィ笥缶鸵粋€(gè)個(gè)地滿地打滾。
一次和哥哥吵了架,我賭氣不搭理他好幾個(gè)小時(shí),他就一直在我面前繞來(lái)繞去討好我。我跑到火塘邊坐著,扔了個(gè)洋芋進(jìn)去,快熟的時(shí)候他又跑來(lái)了,站在我面前嘻嘻地笑。我沒(méi)好氣地說(shuō)了一句:“快讓開,別對(duì)我的洋芋虎視眈眈!”話一出口,自己就忍不住“撲哧”笑了起來(lái),媽呀,“虎視眈眈”我的洋芋!哥哥聽(tīng)后,笑得要打滾,屋里所有的人都樂(lè)不可支。正笑著,突然聞到一陣很“臭”的味道,趕忙四處尋找,卻發(fā)現(xiàn)是自己的腳踩在火塘邊的鐵條上,橡膠鞋底被烙出了一條印痕。
再一次,爺爺坐在火塘前一個(gè)人呼嚕呼嚕地吸水煙。他披著件灰藍(lán)色的布衣外套,纏著深藍(lán)色的布包頭,一雙手納的黑色粗布鞋,灰白色的胡子大概有我半只手掌那么長(zhǎng)。我拿了幾個(gè)洋芋放到火塘邊,用灰埋起來(lái),坐在旁邊的爺爺笑起來(lái):“小麗,你那么愛(ài)吃洋芋呢。”我“嗯”一聲就準(zhǔn)備走,爺爺把我叫住,說(shuō)要跟我擺擺“龍門陣”,于是我只有乖乖地坐下來(lái)了。
爺爺一邊“呼嚕呼嚕”地吸著水煙筒,一邊跟我講:“你們?cè)谛?huì)澤和東川還有三個(gè)奶奶哩!”我剛把嘴巴張大還沒(méi)來(lái)得及其他反應(yīng),就聽(tīng)見(jiàn)奶奶的聲音從門口傳進(jìn)來(lái):“那你是不是還要帶著他們?nèi)フJ(rèn)識(shí)認(rèn)識(shí)呢?”爺爺嚇一跳,趕緊換了個(gè)話題,仿佛剛才說(shuō)那些話的人不是他。藍(lán)布長(zhǎng)衫黑褲子的奶奶白了他一眼,踮著小腳又出去了,我則樂(lè)個(gè)半死。這件事后來(lái)被我當(dāng)成家里的趣事說(shuō)了好多年,但一直到現(xiàn)在,爺爺奶奶都故去了多年,我也不知道那三個(gè)地方是不是真的還有我們的血脈親戚。
后來(lái)愛(ài)吃洋芋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吃,頓頓吃;在家吃,出門還要花錢買了吃。街上的吃法并不多,大概就是三種,烤熟的居多,可能是因?yàn)榉奖悖苽€(gè)三輪車就可以四處叫賣;另外還有兩種,一種是類似于我們現(xiàn)在吃的麻辣燙,洋芋切成一片一片的,用竹簽穿起來(lái),燙熟了后抹上各種醬料吃;一種是油炸洋芋,蘸料又分兩種,干辣椒面或者是昭通醬。出了門,見(jiàn)到哪種就吃哪種,完全不挑,因?yàn)橐粯拥睾贸浴V劣谠诶霞依镒隽顺裕浅苑ň投嗔耍藷目镜挠驼ǖ模€有炒的、煮的,整個(gè)地蒸的或切絲煎餅的……至于吃相,那就草莽得很了,怕?tīng)C手,就將洋芋整個(gè)地插在筷子上吃、一面換手一面用嘴呼哧呼哧地吹著吃,比較經(jīng)典的是蹲在地上雙手“顛”著吃。各式各樣,各形各狀,回想起來(lái)真是好笑得很。在老家的那半月里,我胖了近10市斤。同時(shí)帶來(lái)的后果就是在往后的20年里,我再也不敢“碰”洋芋了。
后來(lái)聽(tīng)說(shuō),在1948年,邊縱部隊(duì)1200人赴越南河陽(yáng)整訓(xùn)時(shí),400人死于惡性瘧疾,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滇東北人,他們臨終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個(gè)家鄉(xiāng)的燒洋芋。
蘋果和往事有關(guān)。
那年的我愛(ài)上了一位男生,準(zhǔn)確的表述應(yīng)該是:我和一位男生相愛(ài)了。他“寵我是寵到?jīng)]邊際,寵到?jīng)]有底線”的那種。現(xiàn)在想來(lái)真是唏噓,那種狂野到不過(guò)是尋常暫別卻如生離死別一般的斷腸和痛苦,那種在大庭廣眾也忍不住仿佛要把對(duì)方揉進(jìn)自己身體里去的死命擁抱和痛哭,那種可以為對(duì)方舍生忘死的“痛快”,如今再也不會(huì)有了,今生也不會(huì)再有了。只有那時(shí)的我們,才擁有對(duì)時(shí)間的放肆,擁有對(duì)自己生命的主宰權(quán)。現(xiàn)在卻唯有一聲冷笑,我們的命哪里還是我們的?不要說(shuō)死,連生病都害怕得要死。是啊,“死了”,誰(shuí)來(lái)照顧我們?誰(shuí)來(lái)照顧需要我們照顧的親人?
他和我是異地戀,但因我一直自詡為流浪兒,并未在意空間的距離。
蘋果就是那個(gè)時(shí)候吃怕的。他見(jiàn)我愛(ài)吃,便一箱一箱地買了來(lái)給我,哪怕我回到老家,他也寄了來(lái)。那個(gè)時(shí)候,在整個(gè)云南省,都是昭通蘋果的天下——即便是交通網(wǎng)絡(luò)如此發(fā)達(dá)的今天,昭通蘋果仍然占據(jù)著半壁江山呢!
空間的距離可以忽略,兩個(gè)人的性格卻無(wú)法忽略。
年輕與氣盛,總是相依相生。針尖對(duì)麥芒,也總是形影不離。時(shí)間久了,吵鬧得倦了,便拼了死地分了。愛(ài)到盡頭覆水難收,不如一別兩寬。
時(shí)光漫卷,那份情感也早已時(shí)過(guò)境遷。但即便到如今,每每看見(jiàn)昭通蘋果,仍是忍不住地想起那個(gè)人,想起那些整箱整箱的蘋果。
五
父親17歲離家,如今已白發(fā)蒼蒼,已近80歲。
我,從出生就缺席的人,在黑夜中,回到這塊養(yǎng)育了父輩祖輩的土地上,一路地尋找到昭通。父親的長(zhǎng)安車“奔奔”在這樣的道路上顯得笨拙但實(shí)用。對(duì)于回鄉(xiāng)的路,父親顯然也不太記得了,一路行一路問(wèn)。剎車、詢問(wèn)、起步,給油。接近那個(gè)叫“28戶”的村莊時(shí),心里竟然惶惑起來(lái)。
父親在逼仄彎多的村里土路上駕駛著車,顯得手忙腳亂,還要記得時(shí)不時(shí)給我指出,這兒是家里的老宅,那里是我二叔現(xiàn)在的家。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切,我曾經(jīng)來(lái)過(guò)的這里,現(xiàn)在,它們?nèi)种牡胤奖焕⑼粱⑸惩梁鸵恍┟婺坎磺宓亩逊e物所覆蓋和掩埋,三分之一突兀地蓋著嶄新的樓房。父親看出我的情緒,他只是笑:“發(fā)展過(guò)程么,都是這樣,再過(guò)幾年就好了。”
是的,這是我的老家,一個(gè)真實(shí)的村莊,并不是文人心目中的田園。
新的覆蓋了舊的。舊的被新的取代。淹沒(méi)、填充、層疊式的覆蓋,遺忘了遺忘的伊始。
這種覆蓋,是碾壓式的,極具毀滅性的,或者也可以以“再創(chuàng)”而代之。
零亂和規(guī)整,局部和整體,唏噓和欣慰,交織成一張龐大的網(wǎng)。
我站在現(xiàn)實(shí),卻被過(guò)去淹沒(méi)。
記憶中的故鄉(xiāng)是冷的空氣,甜的蘋果,香的洋芋,時(shí)至今日,時(shí)間已經(jīng)將這種種,全部發(fā)酵成一個(gè)血緣式的名詞:昭通,昭通,昭通!
文字中離不開的故鄉(xiāng),對(duì)應(yīng)的是現(xiàn)實(shí)中傾盡半生也難以回去的離人。
抵達(dá)熟悉,卻如抵達(dá)陌生。
抵達(dá)陌生,卻是抵達(dá)熟悉。
六
每一個(gè)人,都是被關(guān)在故鄉(xiāng)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