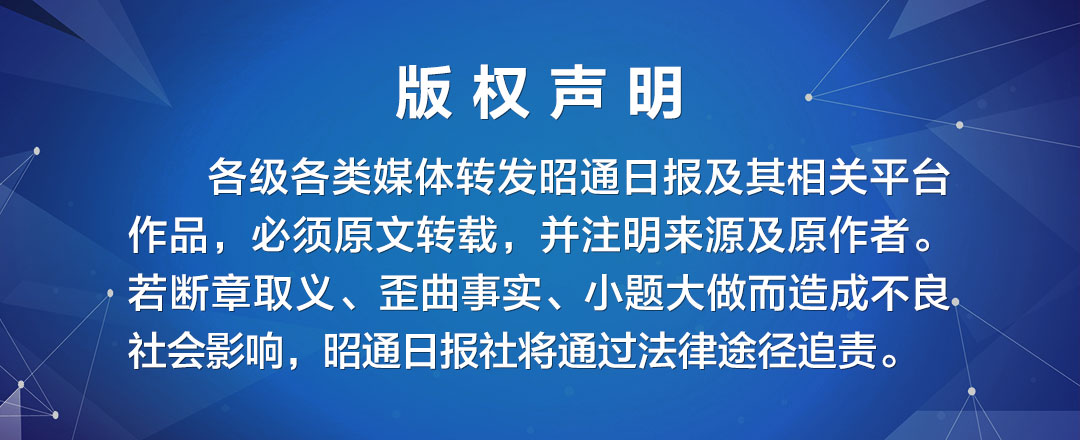2021-03-17 11:43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古 道 春 色?
?◆張永權(quán)
去鹽津縣尋訪秦五尺道的遺跡時(shí),已是深秋初冬時(shí)節(jié)了。氣溫突降,寒風(fēng)襲來,卻難掩沿途的滿眼風(fēng)光。烏蒙崇山峻嶺中,火紅的楓葉,沉甸甸的一樹樹紅蘋果,呈現(xiàn)出秋的豐碩,又燃燒成滿眼燦爛的春色。
秋光和春色相融,把烏蒙山浸染得分外神奇妖嬈。突然一條清流穿過磅礴的烏蒙群山,在鹽津縣境內(nèi)被一道斧劈刀削的千仞峭壁擋住了它前行的腳步,只聽它一聲怒吼,那銅墻鐵壁的一面懸崖,頓時(shí)裂開一道萬丈深淵,如打開的摩天石門,江水便奔騰咆哮而去了。
伴隨這條烏蒙山中的關(guān)河,我們攀上了懸崖上的古道。道路依山而上,路陡蜿蜒,路面凹凸不平,走起來讓人氣喘吁吁。2000多年來,歲月的風(fēng)雨陰晴和千千萬萬的人馬踩踏,青石被磨亮了,閃著碧玉般的光芒。那些被馬蹄踩踏出的蹄印,深深淺淺,密密麻麻,有的比拳頭碗口還大,有的就像留在化石上的痕跡,有的是馬蹄打滑時(shí),從青石邊沿踩刮出的一道道蹄削印,實(shí)為罕見。
道路不寬,約五尺多,又十分規(guī)范,它已經(jīng)穿越2400多年的歷史了。現(xiàn)存于朱提江(又稱關(guān)河)畔的這段古道,就是聞名中外的五尺道。在這里還完好地保存著350多米的古道,呈現(xiàn)出的馬蹄印就多達(dá)243個(gè),差不多一米一個(gè)蹄印,單從這些蹄印,就讓我們感受到五尺道所承載的歷史滄桑是何等的豐厚,是何等的偉大。
峽谷的山風(fēng)在敘說,關(guān)河的濤聲浪語在回應(yīng),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可忽視的年代。秦朝為統(tǒng)一中國,西征巴蜀后,時(shí)任太守的李冰,是一個(gè)目光遠(yuǎn)大、有才干、精通水文地理又干實(shí)事、業(yè)績突出的專家型政治家,他在成都岷江修筑都江堰等水利設(shè)施,化水害為水利,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的糧倉。都江堰歷經(jīng)2500年風(fēng)雨,至今仍發(fā)揮著疏浚和灌溉的作用。同時(shí),他奉秦孝王之命,為打通中國和彩云之南阻塞的封閉狀態(tài),發(fā)展西南邊陲的經(jīng)濟(jì),造福各族人民,從宜賓起,修筑一條穿越烏蒙群山的大通道。面對崇山峻嶺、深谷奇峽,他騎著川驢滇馬,進(jìn)出原始森林,勘察地理線路,征集當(dāng)?shù)貎k人,開山修路。《華陽國志》記載,那時(shí)沒有炸藥,他就用伐薪燒巖的辦法,把一座座大山堅(jiān)硬的巖石燒紅潑冷水使之開裂,再砸石打碎開道,終于把一條連接云南邊疆與中原內(nèi)地的大道修成。這條大道從四川的宜賓開啟,穿過烏蒙群山經(jīng)滇鹽津石門進(jìn)入朱提(今昭通)南下,越過珠江源頭曲靖,直達(dá)昆明的滇池邊。這條大道,也實(shí)行秦“車同軌”的標(biāo)準(zhǔn),統(tǒng)一成五尺寬,史稱五尺道。這一切在歷代史籍,如《蠻書》《舊唐書》等都有記錄。
一條五尺道,承載著2000多年的歷史風(fēng)云,實(shí)在太多太沉,僅眼前的這段350多米的遺存,就有許多讓人震驚的故事,就有許多寫不完、道不盡的古今傳奇。
有道必有關(guān)。因五尺道是中國內(nèi)地連接邊陲的官道,如當(dāng)今的國道要沖。它從宜賓過來,進(jìn)入烏蒙群山的今鹽津縣朱提江岸,面對這里的一道天然的屏障,五尺道自然就在這里筑壘設(shè)關(guān)開鎮(zhèn)了。山頂?shù)揽陉P(guān)隘,只要兩扇大門一關(guān),再加一根內(nèi)杠,就是“一夫當(dāng)關(guān),萬夫莫開”了。千百年前,因江河沖開的石壁峽口,如一道巨大的石門屏障,就取關(guān)名為石門關(guān),古鎮(zhèn)叫石門鎮(zhèn)。但如今關(guān)門上方卻赫然寫著“豆沙關(guān)”的名字,關(guān)上古鎮(zhèn)也叫豆沙鎮(zhèn)。我在仰望豆沙關(guān)名字時(shí),問身邊一昭通農(nóng)民豆沙關(guān)名字的由來,他說鹽津盛產(chǎn)豌豆、黃豆、蠶豆,做成的豌豆粉和豆花是鹽津的名小吃,加上昭通綠豆糕盛名國內(nèi)外,鹽津人便因此而叫其豆沙關(guān)了。不過他說這只是民間的說法,書上還有多種記載呢。我思忖關(guān)名的幾種來源,覺得這位農(nóng)民兄弟的說法,很鄉(xiāng)情,更切合實(shí)際。關(guān)名、地名,自然要顯當(dāng)?shù)靥攸c(diǎn)。在豆沙古鎮(zhèn)吃午餐,那可口的豌豆粉和細(xì)膩雪白的豆花,讓我垂涎,食欲大增。豆沙關(guān),名副其實(shí)。
沿著這些深深淺淺的馬蹄印,我們向上攀緣著,耳畔似有馬嘶的轟鳴,人喊的嘈雜。這些重走五尺道的旅人,漸漸化成了南來北往的商旅,一隊(duì)隊(duì)馬幫,一行行的挑夫,鐵具、銅器、竹簡、布匹、蜀錦、川鹽、云茶……還有一乘乘往南傳旨的官輿龍騎,一隊(duì)隊(duì)戍守邊關(guān)的士卒,把這條五尺道擠滿了人流車馬流,烏蒙山從未有過如此熱鬧和繁榮的景象。昭通一帶,也從未有過如此開放的情景。雖然昭通之名是清代才有的,但這條五尺道使昭通處于北接巴蜀中原,南連云貴甚至南亞、西南亞的交通樞紐位置,早在2400年前,就已昭明通達(dá)天下了。昭通之名,是2400年前的這條五尺道,就給它起好了的。
站在烏蒙山五尺道的雄關(guān)隘口,穿越幾千年的歷史風(fēng)云,這個(gè)雄關(guān),這條通道,實(shí)在太偉大了。也許李冰修五尺道時(shí),就想到和看到了,這條連接邊地與中原的五尺道,一定還會(huì)有更大的作為,它必定會(huì)成為中國最早通向世界的國際大通道。秦統(tǒng)一中國后,以更遠(yuǎn)大的目標(biāo),更寬廣的胸襟,把大秦置于四通八達(dá)面向世界的位置,五尺道從滇池邊再向西、向南延伸,越哀牢,過洱海,成博南古道出緬甸,進(jìn)印度,到西夏(今阿富汗),甚至進(jìn)入了歐洲,建立起了偉大的蜀身毒道,即古南方絲綢之路。漢武帝時(shí)張騫從北方出使西域,就在西夏見到了中國的絲綢、蜀布、茶葉、竹杖等,令他驚異。原來從五尺道岀去的南方古絲綢之路,比之北方絲綢之路,早了200多年。
五尺道,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中國道路的奇跡,中國開放之路的奇跡。如今站在烏蒙雄關(guān)的關(guān)口,遙望南天,秋光滿眼,春色明媚,那一條條連接南亞、西南亞的高速公路和高鐵,不是就始于2400多年前的這條五尺道么?不是也把“一帶一路”的源頭,提前到了秦漢時(shí)代的五尺道?它丈量著中華民族遠(yuǎn)大的目光和海闊天高的胸襟,唱響了一曲中國人最早的開放之歌。
把目光收回,觸摸身邊的巍峨雄關(guān),品讀留在歷史遺跡背后的故事,我要為中華民族先輩的遠(yuǎn)見卓識驕傲,我要為云南邊疆各民族為維護(hù)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團(tuán)結(jié)和邊疆的發(fā)展繁榮作出的巨大貢獻(xiàn)放聲高歌。這是一塊并不宏大的摩崖石刻碑,它的歷史價(jià)值和意義,是因?yàn)檫M(jìn)入了國家級的歷史文物保護(hù)名單,就得到的證明。石刻位于五尺道雄關(guān)西側(cè)的崖壁上,其云:“大唐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內(nèi)給事倶文珍,判官劉幽巖,小使吐突承璀,持節(jié)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jiān)察御史崔佐時(shí),同奉恩命,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shí),節(jié)度使、尚書后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統(tǒng)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石紀(jì)之。袁滋題。”石刻為袁滋手跡,歷經(jīng)1200多年仍清晰完好。石刻記錄了袁滋一行,于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奉皇帝之命,赴云南冊封南詔異牟尋為云南王的經(jīng)國大事。其背景是由于南詔與唐王朝連年的戰(zhàn)爭,給國家和邊疆各族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南詔王反思叛唐的后果,決心重歸于唐。唐德宗大悅,故派御史中丞袁滋一行持節(jié)冊,經(jīng)五尺道赴滇。袁滋夜宿石門關(guān)時(shí),為記其行,便題寫了這塊摩崖石刻。
豆沙關(guān)的五尺道袁滋摩崖石刻碑,更添古道雄關(guān)厚重的歷史價(jià)值和深遠(yuǎn)的意義。別看摩崖石刻小,卻被譽(yù)為“維國家之統(tǒng),定疆域之界,鑒民族之睦,補(bǔ)唐書之缺,正在籍之誤,增袁書之跡”的政文大碑。有此碑刻于古道雄關(guān),古道萬世流芳,雄關(guān)更加巍峨。
1000多年前云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維護(hù)國家統(tǒng)一、增強(qiáng)民族團(tuán)結(jié)的歷史貢獻(xiàn),在時(shí)代的進(jìn)程中不斷發(fā)揚(yáng)光大,特別是中國共產(chǎn)黨實(shí)行的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在云南得到了生動(dòng)的體現(xiàn),新中國成立后云南的8個(gè)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大多在古五尺道南方絲綢之路沿線。云南的26個(gè)民族,團(tuán)結(jié)和睦,親如一家。今天,在脫貧攻堅(jiān)奔小康的道路上,為使每一個(gè)少數(shù)民族都不掉隊(duì),穿越過百年風(fēng)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不忘初心,舉全社會(huì)之力,全國貧困縣全都精準(zhǔn)脫貧,創(chuàng)造了讓世界驚異的奇跡。我們從五尺道走進(jìn)烏蒙山,昔日的茅草屋被白墻青瓦的樓房所代替;五尺道上的馬幫,變成了金龍飛奔的內(nèi)昆鐵路,鐵馬揚(yáng)蹄的G85高速公路。在昭通昔日的五尺道上,一座安置了烏蒙山中貧困戶5萬余人的靖安新區(qū),拔地而起,成為烏蒙山全面精準(zhǔn)脫貧的時(shí)代新神話。這些從烏蒙山中的魯?shù)椤㈡?zhèn)雄、鹽津、大關(guān)、威信、昭陽等縣(區(qū))遷來的貧困戶,涵蓋了漢族、彝族、苗族、白族、回族等民族。新區(qū)為他們的生活、就業(yè),法律、培訓(xùn)、醫(yī)療、教育等,建立了完整的綜合服務(wù)體系,使他們真正做到了搬得進(jìn)、住得好、穩(wěn)得住、脫了貧、奔小康。在新區(qū)大街上,筆者見到一位搬進(jìn)新居的苗族老大爺,他不時(shí)無償、自愿在街上打掃衛(wèi)生。他說:“過去古歌說好生活在天堂,現(xiàn)在從高山茅草屋遷到新區(qū)樓房,新區(qū)就是我們的天堂。我要把天堂打掃得干干凈凈,才對得起國家的關(guān)懷,才對得起黨中央和習(xí)主席。”說著他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來:烏蒙巍峨苗嶺高,哪有黨中央的恩情高……各族人民奔小康,生活天天賽天堂……
老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歌聲,唱出了五尺古道上燦如春天的新氣象,在我聽起來,就是一曲五尺古道上的新時(shí)代頌歌。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原副主席,《邊疆文學(xué)》原主編)
?
 (張永權(quán)/文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張永權(quán)/文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