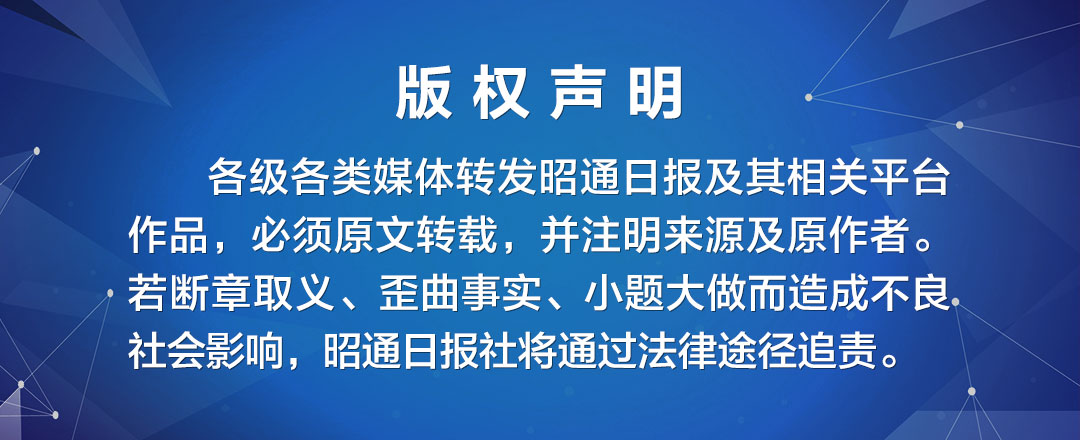2021-03-29 17:45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魯?shù)潞哟┰綅{谷,沿山崖奔瀉而下,推著爐房河奔騰向前。兩側(cè)的群山往后一仰,腹部稍稍抬起,從河床到山腳,形成幾塊平緩的坡地。人們在這里起房蓋屋,世代耕耘。在清晨和黃昏寧靜的光影中,幾縷淡淡的炊煙飄起來,掩映著破舊的老屋。青煙裹著黃土在風里輕蕩,呈現(xiàn)出極不真實的景象,讓人陡生一種隔世之感。入夜后,那些電燈漸次亮了,微如螢火的光在風中喘息。幾個小時后,所有的燈同時熄滅,大山再次陷入無邊的黑夜。
這是我對魯?shù)麓遄钤绲挠洃洠覍﹄姷挠∠螅彩菑哪抢镩_始的。魯?shù)麓濉夷赣H的故鄉(xiāng),隸屬昭通市巧家縣爐房鄉(xiāng),20世紀90年代,還是一個陳舊、破落的小村子,蜷縮在山河的交界處。村子不大,但人們居住分散,從山腰到山腳,零星散落著一些泥墻瓦頂?shù)姆孔印D赣H帶我回娘家時,住在山腳下小舅的瓦房里,那里離河不遠,屋后是一片松林,我夜夜聽著松濤和水聲入眠,時常夢見在搖晃的水下從一盞燈走向另一盞燈。多年后,那里變成了爐房水庫,當我一動不動凝望著幽暗的水面時,年少的記憶在腦海中泛起波瀾,我突然明白了那個夢境的喻示。
群山與流水碰撞擠壓,讓魯?shù)麓逡荒昴昕s小。河水在時光里堆積,一點點淹沒房屋、土地,一個完整的村子被水流擊成很多碎片。一部分人留下來,守護祖宗埋骨的土地,一些人如四散的蒲公英逃離故鄉(xiāng)。有人去了省外,有人去了昆明,有人不知下落。小舅一家遠走思茅,投石問路般,艱難經(jīng)營和老家完全不一樣的生計。
天地不語,逝者如斯,每個人都在時代變遷中經(jīng)歷或好或壞的境遇。當我透過浪濤聆聽水底那片土地翻騰的回聲時,冥冥中覺得,每個人都該有所承擔,每一塊土地都有使命。人生的魅力,在于每個人都要面對未知的旅途,盡管難免遇到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但我們用大山里微弱的燈火指引腳步,努力靠近光,靠近心中搖搖欲墜的理想。
魯?shù)潞酉掠危貏蓦U峻,水流湍急。源于水的恩賜,山谷中一片狹窄平緩的河床上,建起一座小型發(fā)電站。我不知道電站建于何時,從記事起,它就有些破爛。幾間矮小的房子,門上各掛著一把大鐵鎖,里面的機器成天發(fā)出轟鳴聲。電站一側(cè)臨近懸崖,站在房頂清晰可見從崖頂飛瀉的流水,閃著透亮的白光。若是雨季,裹著泥漿的洪水從高處砸下來,像很多巨大的猛獸席卷而去,電站在巨浪拍打下?lián)u搖晃晃。平日里,電站周邊少有人跡。炎熱的夏天,小伙伴們?nèi)ズ永镉斡尽⒚~,路過電站時會調(diào)皮一下。年少未經(jīng)世面,他們對房子里發(fā)電的家伙抱有強烈的好奇心,總是湊近墻上的小洞,用一只眼往里面看,不時對旁人做鬼臉。有人夸張地比畫,說看到了什么,另一個人湊近看,黑漆漆的一片。受騙的人還納悶呢,一串笑聲已在山谷里回蕩。
電站雖小,用處卻不小。日子進入冬天,一向冷清的電站就變得熱鬧起來。那幾間房子的門難得開著,孩子們乘機溜進去,看看那些發(fā)電的大家伙,還有打糠機。通往電站的小路上,可見稀疏的人影,他們弓著腰,背著干透的紫花草,到電站打糠,準備來年的豬食。這個季節(jié),小舅格外忙碌,他是電站的管理員,還要幫村里人打糠。這是又臟又累的活計,小舅全身沾滿灰塵,像是每天鉆土洞一樣。盡管如此,小舅從不靠打糠賺錢,只收很少的錢作電費。他常常說,都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吃點虧沒什么,人一輩子,總有用得著別人的時候。
山里的人,最討厭黑夜,無法下地勞作,還漫山一片漆黑。多年來,小舅的雙腳像上了鬧鐘,他總是在八點鐘趕到電站,準時把電送到每家每戶,無論風雨,雷打不動。群山里燈光星星點點、忽明忽暗,但在人們心里,那是一團團照亮黑夜的火焰,他們滿身的疲倦也隨之融化在那些火焰里。
相比電燈,我更關(guān)心錄音機,那長長的魔盒,仿佛裝著無數(shù)精彩的聲音和故事。家里燈亮時,我的心一緊,不由自主盯著供桌上那臺老式錄音機,渴望小舅趕快回來。每個夜晚,當小舅把插頭插到燈頭上時,錄音機立刻“活”了起來。我們圍坐在火塘前,聽聽別人的故事,也聊聊家長里短。那些歡快的、悲傷的音調(diào),瞬間把我變成故事里的人。
興致正濃時,屋子漸漸暗了下來。錄音機的聲音變得渾濁,像是在哭泣。我看看那根細如線的燈絲,掙扎出點點紅光,像大火將熄的余燼。小舅關(guān)了錄音機,起身往外走,我知道,他要去電站斷電了。
我問過小舅,為什么要斷電呢?他說,這是水電,時間長了供應不上。我心里想,要是不用水發(fā)電多好。后來我知道,我們用的電大多是水電,只是那些年設(shè)備落后,水量不足,發(fā)不了太多電。那時,我對“水電”又恨又愛。恨,是因為總在故事沒講完的時候,電力變?nèi)酰浺魴C卡住了。可是我又無比盼望夜晚的降臨,因為小舅和他的錄音機,總是讓我產(chǎn)生奇妙的歡喜。
上小學后,我很少再見到小舅。偶爾聽母親說,小舅一家要搬到思茅。我問母親,為什么要搬家呢?母親紅著眼眶像剛哭過,她嘆氣說,修爐房水庫,要淹了小舅的房子和土地,政府讓他們搬到思茅,有什么辦法呢?
多年來,“思茅”像一個結(jié)懸在我心中。小舅搬家后,我再沒去過魯?shù)麓澹坏貌怀姓J,我對思茅也產(chǎn)生了淡淡的抗拒情緒,我以為時空的阻隔終將把我們變成最親的陌生人。
多年后,我路過思茅,左思右想,還是打電話給小舅說去看看他。他從手機上發(fā)了定位給我——六順鎮(zhèn)竹山河村,我開車沿著狹窄崎嶇的山路艱難前行。可我終究無法感受到,20多年前交通不便時,小舅從一座大山搬進另一座大山,經(jīng)歷了怎樣的艱難。
正是夏末,氣候炎熱,茶香從很遠處飄進我心里。小舅挎著一個篾制背簍,在家門口的茶山里采茶。陽光爬上他的臉,撫平了皺紋,他臉上浮現(xiàn)出一絲滄桑的笑容。站在那片濃濃的綠意中,我看到群山深處零星地散落著一些房子,可是少有人影。眼眸所及之處,除了茶山,便是密密麻麻的樹林,說是萬山老林也不為過。
小舅說,他來竹山河村22年了。最初的那幾年,靠著水庫補償款生活,吃了上頓愁下頓。后來開荒種茶,現(xiàn)在有了幾十畝茶山,吃穿不愁了。盡管已年過50,但小舅臉色紅潤,身體略微發(fā)福,看上去生活不錯。
那夜月亮很圓,小舅新蓋的二層樓房里,燈光亮如白晝,電視里傳出優(yōu)美的歌聲。我們心里都有很多話,可是怕觸及往事都說得小心翼翼。后來我們說到爐房水庫,說起那座被淹沒的電站,小舅突然有些難過。他說,剛來時生活無望,又回魯?shù)麓逭页雎罚伤谀抢锸裁炊紱]有了。時間停了一下,小舅勉強一笑說,那么大的水庫,總要有人作出犧牲,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他靠著茶葉活下來了。
我看著小舅,他眼里溢滿淚花。我知道,以小舅為代表的那一批移民,盡管有掙扎,不甘心離開故土,但在家國大義面前,他們選擇了犧牲。
不過可以確信,時光沒有虧待實誠的人。這么多年,小舅從清貧走向富足,我從稚拙的少年搖搖晃晃跨入青年,走進燈火閃爍的城市。略去其中的兜轉(zhuǎn)和波折,我們始終向光而行,用勤奮之燈點亮漫長黑夜。我也相信,每個人身上的一點星光,一齊灑向人間,將如陽光照耀萬物,永不消失。
 (朱金賢/文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朱金賢/文 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