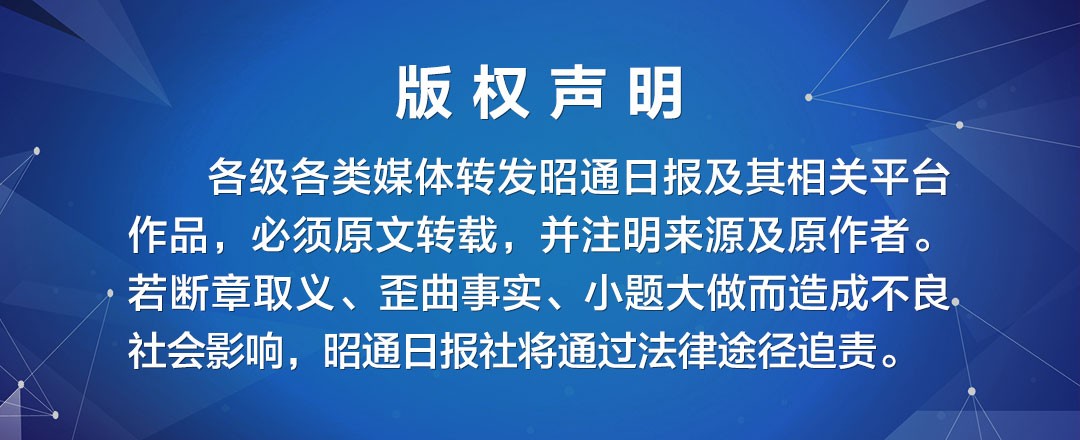2021-07-21 16:45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我是故鄉(xiāng)的孩子,也是文學(xué)的病人
——雷平陽(yáng)在昭通談詩(shī)人的故鄉(xiāng)和精神的籍貫
今天回到故鄉(xiāng)歐家營(yíng),應(yīng)該說(shuō)特別忐忑,近鄉(xiāng)情怯是每個(gè)人基本的一個(gè)常態(tài)。回家,就像前往天空、前往烏有之鄉(xiāng)一樣。去年春節(jié)我沒(méi)回來(lái),一年后,家門(mén)口的那條河竟然清澈了許多,這是我特別特別意外的一件事。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參觀雷平陽(yáng)舊居。
我在一篇散文里曾經(jīng)寫(xiě)過(guò),我大哥在父親的墳頭燒紙,媽媽就跟大哥開(kāi)玩笑:燒這么多錢(qián)給他,他根本用不完,一定要讓他把這些錢(qián)拿出一部分來(lái),把這條河流清理干凈。我當(dāng)時(shí)就站在旁邊,聽(tīng)到媽媽跟哥哥對(duì)話(huà)的時(shí)候,我覺(jué)得媽媽的幽默中有無(wú)奈,也有渴望。今天看見(jiàn)河道變清了,心里真的挺高興。
我的高興當(dāng)然也跟大家的光臨有關(guān)。我曾經(jīng)在《廣西文學(xué)》發(fā)表的長(zhǎng)詩(shī)《昭魯大河記》,寫(xiě)的就是這條河,并且它是我最偏愛(ài)的一首詩(shī)歌,因?yàn)樗尸F(xiàn)了我少年時(shí)代的記憶、恐懼和慌張,以及沒(méi)有安全感的生活,當(dāng)然也有我的夢(mèng)想,我想象中的故鄉(xiāng)。詩(shī)歌中的很多事不是真的發(fā)生過(guò),但是它曾經(jīng)在我的夢(mèng)境中出現(xiàn),或者在自己偏安一隅的時(shí)候忽然訪(fǎng)問(wèn)過(guò)我。
我們的寫(xiě)作不一定非要去寫(xiě)發(fā)生過(guò)的,或者說(shuō)看見(jiàn)的那些事件,更重要的是寫(xiě)我們內(nèi)在之眼看見(jiàn)的,心里感受到的那些東西,那些不真實(shí)的,那些屬于夢(mèng)幻的東西。怎么把它們變現(xiàn)、讓虛構(gòu)、虛無(wú)、思想之物落到實(shí)處,一直是我寫(xiě)作的趣旨。我老家的房子被拆除了,代之的可能會(huì)是一座新屋(目前還沒(méi)有),新則新矣,與之對(duì)應(yīng)的精神供給以及鄉(xiāng)村文化的墮落卻是前所未有的,令人為之嘆息。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參觀姜亮夫故居。
我曾經(jīng)在很多年以前靠記憶把我的村莊畫(huà)成一張地圖,這是一張很大的地圖——哪一家人住在哪兒,哪一家是幾間房,哪些家居住在河流的兩岸,一一精確無(wú)誤。我覺(jué)得當(dāng)年的那個(gè)村莊雖然跟現(xiàn)在的房屋質(zhì)量不可比,但是每一次想到它是溫暖的,它是金光閃閃的,仿佛總有無(wú)數(shù)的光在照耀它,現(xiàn)在的這個(gè)村莊雖然它變成了激進(jìn)的、高大的、華麗的“天堂”,可有些時(shí)候我發(fā)現(xiàn),住在里面的人,很多都變成了幽靈,遙遠(yuǎn),不可知,沒(méi)有親切感。原先那些老房子,以及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是有溫度的,真實(shí)的,你可以叫他叔叔,你可以叫他外公,叫他哥哥,叫她妹妹,但現(xiàn)在變成了統(tǒng)一、模糊不清的符號(hào)。村莊里,沒(méi)有什么父親、母親了,也沒(méi)有哥哥、弟弟和表妹了,仿佛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個(gè),血緣、表情、思想、欲望,他們都是統(tǒng)一的,區(qū)別他們,只要用一個(gè)編號(hào)就可以。這種新生的恐懼和恐慌,導(dǎo)致所有歸鄉(xiāng)的道路,變得那么的艱難,不一樣的道路似乎只通往同一個(gè)地方。我寫(xiě)過(guò)的一篇散文《霍俊明的憂(yōu)傷》,寫(xiě)鄉(xiāng)下人放陰,把自己的靈魂放出去漫游,有的靈魂結(jié)果再也不會(huì)歸來(lái)。想想,現(xiàn)代游子的境況大抵如此。每一次回家都是一種困惑,都是一次探險(xiǎn),都是一次對(duì)記憶的檢測(cè)。它帶來(lái)的沖擊和思考,我們每天都要面對(duì),一些讓人內(nèi)心難安的東西已經(jīng)成為日常。
即使你回了故鄉(xiāng),你想擁抱的人越來(lái)越少,有些時(shí)候擁抱一個(gè)人就是擁抱一件衣服,擁抱一個(gè)凳子。這帶給我的慌亂,讓人感覺(jué)你所難以想象的冷漠在現(xiàn)實(shí)中不處不在,那種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感,由不得你不將所有的人都看成“機(jī)器人”。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寫(xiě)作變得極其焦急,因?yàn)槲覀儍?nèi)心還有美,還有溫度,還有光,還希望用筆創(chuàng)造一個(gè)世界。同時(shí),我常常覺(jué)得自己創(chuàng)造的世界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一比較馬上就變得很蒼白,寫(xiě)作費(fèi)盡了所有的心思,神的視角也好,天才也好,神助也好,一并出現(xiàn)在文字中,偉大作品產(chǎn)生的時(shí)候,現(xiàn)實(shí)往往很快就否定了它。當(dāng)現(xiàn)實(shí)比你的文本更有力量的時(shí)候,我想是考察、考驗(yàn)一個(gè)作家的時(shí)候了。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參觀陡街。
上世紀(jì)90年代初,我離開(kāi)昭通的時(shí)候,寫(xiě)過(guò)一首詩(shī)《出了昭通路就平了》。當(dāng)時(shí)就想去這個(gè)世界闖蕩,可世界何其壯闊,坐在汽車(chē)上,跑了一天還沒(méi)跑出烏蒙山這顆泥丸的一半,而且多少年的一次次回望,愈發(fā)覺(jué)得小世界里存在著大世界,它的宇宙觀,它古老秩序與法相,對(duì)應(yīng)了我精神世界中沒(méi)有邊界的那片凈土。我已經(jīng)幾年沒(méi)出門(mén),一個(gè)人盡可能地往內(nèi)走,發(fā)現(xiàn)自己的內(nèi)在目光。胸懷天下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已經(jīng)過(guò)去了,現(xiàn)在需要呈現(xiàn)的是內(nèi)心那個(gè)世界,或者套用《發(fā)明故事的人》一書(shū)的書(shū)名的說(shuō)法,我想自己給自己發(fā)明一個(gè)世界,自己給自己發(fā)明一點(diǎn)時(shí)間,自己給自己發(fā)明一點(diǎn)空氣,自己給自己發(fā)明鮮花。昭通這片土地的溫暖、情感,讓自己的作品有靈魂和尊嚴(yán),甚至有一雙機(jī)靈的眼睛在背后盯著。重要的是,這片土地具有“發(fā)明”另一片土地的特質(zhì),它能滿(mǎn)足我所有的非份之想。幾年前我去往加勒比海地區(qū)的多米尼加訪(fǎng)問(wèn),帶給我一個(gè)驚心動(dòng)魄的感受:讀拉美作家的作品,都是從字面去看這些作品,但加勒比海之行,卻能在拉美的土地上遇上一個(gè)個(gè)舊靈魂和新靈魂,原生文明與西方文明共同哺育岀來(lái)的一個(gè)“文明的孩子”是如此的與眾不同,孤獨(dú)而又豐饒。除了大海之外,其實(shí)它的整個(gè)自然生態(tài)與文化生態(tài),跟云南何其相似。可那片土地產(chǎn)生了如此多的文學(xué)大師,令人由衷的敬佩!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在轅門(mén)口參觀。
生活中,我是一個(gè)極其枯燥、無(wú)聊的人,沒(méi)有什么愛(ài)好,不會(huì)炒股,不打牌,聊天也聊得不好,隨便跟人聊天,怎么把別人得罪了,自己都不知道,唯一的愛(ài)好就是近乎病態(tài)的寫(xiě)作。幾年前,我出過(guò)一本關(guān)于昭通的書(shū)《烏蒙山記》,書(shū)寫(xiě)我個(gè)體經(jīng)驗(yàn)和想象中的昭通。我不在意事情的真實(shí)性,我覺(jué)得最重要的是用你的美學(xué)方式去完成和重建某個(gè)真實(shí)。隨著人工智能化,也許電腦比人說(shuō)出來(lái)的格言還更像格言,還精細(xì)、還精彩,但個(gè)性化講故事,人工智能可能完成不了,個(gè)性化的講故事是暫時(shí)無(wú)法替代的。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在雷平陽(yáng)的舊居合影留念。
昭通是一個(gè)神靈游蕩的高原,這片土地有無(wú)數(shù)雙眼睛從天宮里面一直看著,我覺(jué)的他們也許是在監(jiān)測(cè)我,而我也奉行“寫(xiě)作乃是寫(xiě)給神看”的法則,基于這一個(gè)契機(jī),我想,也許我應(yīng)該為這些天空里的人再寫(xiě)一本新書(shū)。
簡(jiǎn)介:

雷平陽(yáng),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鄉(xiāng),現(xiàn)居昆明,供職于云南省文聯(lián)、一級(jí)作家。著有《我的云南血統(tǒng)》《雷平陽(yáng)詩(shī)選》《云南記》《基諾山》《烏蒙山記》《天上的日子》《懸崖上的沉默》《擊壤歌》《袈裟與舊紙:雷平陽(yáng)詩(shī)手稿》《送流水》等詩(shī)歌散文集。曾獲《詩(shī)刊》華文青年詩(shī)人獎(jiǎng)、人民文學(xué)詩(shī)歌獎(jiǎng)、十月詩(shī)歌獎(jiǎng)、華語(yǔ)文學(xué)大獎(jiǎng)詩(shī)歌獎(jiǎng)、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等獎(jiǎng)項(xiàng)。

重返故鄉(xiāng):精神世界的拆毀與重構(gòu)
——廣西云南作家評(píng)論家昭通交流會(huì)發(fā)言暨雷平陽(yáng)其人其詩(shī)評(píng)論精選

交流會(huì)現(xiàn)場(chǎng)。
霍俊明——《詩(shī)刊》副主編:
一個(gè)悖論的事實(shí),雷平陽(yáng)的“回鄉(xiāng)”是以“離鄉(xiāng)”為前提和代價(jià)的。雷平陽(yáng)提供的是“大地倫理”受到挑戰(zhàn)的精神背景和現(xiàn)實(shí)境遇,正如黑夜場(chǎng)景和廢墟意象在他的詩(shī)行中頻繁出現(xiàn)一樣。當(dāng)從病理式的癥候閱讀的角度出發(fā),我們會(huì)在他的“故鄉(xiāng)”“云南”看到世界主義景觀的各種病癥和暴力現(xiàn)場(chǎng)。雷平陽(yáng)拒絕做一個(gè)樂(lè)觀主義者,當(dāng)然他也不是廉價(jià)的現(xiàn)實(shí)批判者,他的寫(xiě)作更像是在針尖上點(diǎn)蘸蜂蜜,在寓言、幻象、筆記體小說(shuō)、田野考察和非虛構(gòu)的綜合想象力中展現(xiàn)了魔幻、怪誕的人性、存在以及世界本質(zhì)。提醒一下讀者,雷平陽(yáng)不是一個(gè)地方主義的寫(xiě)作者,而是同時(shí)代詩(shī)人中少有的總體性詩(shī)人。他提供的“詞條”既是見(jiàn)證、追挽和噬心的過(guò)程,也是詞與物的較量,是精神世界一次次拆毀又一次次重構(gòu)的求真意志的過(guò)程。
商? 震——著名作家、詩(shī)人:
廣西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和《廣西文學(xué)》編輯部和云南作家協(xié)會(huì)聯(lián)合發(fā)起的“重返作家故鄉(xiāng)”的活動(dòng),意義重大也深遠(yuǎn)。這個(gè)活動(dòng)不是給功成名就的作家錦上添花,是重新審視作家成長(zhǎng)的路程。這個(gè)活動(dòng)對(duì)被探訪(fǎng)的作家本人可能意義不大,但對(duì)研究者尤其是對(duì)正在從事寫(xiě)作的青年人有著很大意義。借鑒成功經(jīng)驗(yàn)是青年人成長(zhǎng)的必由之路。一個(gè)人或一件事的成功,都是有來(lái)由的。古人說(shuō),欲獲某事成功,須得天時(shí)地利人和。雷平陽(yáng)的家鄉(xiāng)及舊居,從風(fēng)水學(xué)上看,并無(wú)特別之處,甚至還有點(diǎn)欠缺。但是,古人說(shuō)的天時(shí)地利人和,并不是具體到山形水勢(shì)的樣貌走向,就一定會(huì)出什么樣的人。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當(dāng)然也要講天時(shí)地利人和,而在我看來(lái),還要有神助。是如有神助的神,下筆如有神的神。雷平陽(yáng)的心里是住著神的,所以筆下有神。他心里的神,是他的生活理想和文學(xué)信仰,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寬容與和解;是他多年閱讀他人人生經(jīng)驗(yàn)的獨(dú)到總結(jié)。他的心里永遠(yuǎn)住著一個(gè)少年,一個(gè)不斷對(duì)新事物好奇、探索、責(zé)問(wèn)的少年。心里住著少年的作家,就永遠(yuǎn)在成長(zhǎng)期。海德格爾說(shuō):歸鄉(xiāng)是詩(shī)人的天職。我認(rèn)為,詩(shī)人歸鄉(xiāng)不是回到老家,而是從肉體到精神,是把從肉體生發(fā)出的靈魂再返回到肉體中去。許多人一生找不到自己的靈魂,許多人的靈魂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肉身。我看到一些模仿雷平陽(yáng)詩(shī)歌的青年人,他們可以把句式、結(jié)構(gòu)、抒情手段學(xué)得很像,但是詩(shī)中的情感缺少來(lái)源和依據(jù),主要原因是,雷平陽(yáng)心里住著的神,他們沒(méi)請(qǐng)到自己的心里。
桫? 欏——河北作家協(xié)會(huì)文學(xué)院研究員:
昭通作為地理上的存在與我遠(yuǎn)隔千山萬(wàn)水,我對(duì)她具體的了解就來(lái)自雷平陽(yáng)的詩(shī)和“昭通作家群”這個(gè)概念。因?yàn)橐咔榈脑颍ツ甓煳夜戮釉谑仪f,每天必做的功課就是抄錄雷平陽(yáng)的詩(shī),與詩(shī)里的大地山川和人事、與孤獨(dú)的靈魂和深沉的思想對(duì)話(huà)。極難想象,昭通城鄉(xiāng)接合部的歐家營(yíng)作為雷平陽(yáng)的精神原鄉(xiāng),在很早以前就能與遙遠(yuǎn)的我以及萬(wàn)千讀者情感相通,這靠的是詩(shī)人的發(fā)現(xiàn)和建構(gòu):我在老屋和新居的對(duì)比中理解了他在詩(shī)中對(duì)塵世、故鄉(xiāng)、傳統(tǒng)和心靈世界的映射、闡釋與重構(gòu)。烏蒙山、利濟(jì)河和五尺道不獨(dú)屬于雷平陽(yáng)和昭通乃至云南的“地方”寫(xiě)作者,在他們的作品中,所謂“地方性”只是傳統(tǒng)性和同一性的另一副面相。
唐春燁——廣西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常務(wù)副主席:
就這樣,你把我們帶進(jìn)了你的家鄉(xiāng):昭通,土城,歐家營(yíng)。你告訴我們:村前的禾田是你母親換在路邊的;老屋是全村建在村東感受第一縷陽(yáng)光的第一家;你曾花了很多時(shí)間繪制歐家營(yíng)地圖,地圖里對(duì)應(yīng)的是一個(gè)個(gè)你熟悉的“眼睛”,雖然目前“家鄉(xiāng)已面目全非”;我們還見(jiàn)到了你的母親,你的母親微笑著坐在那里,睿智地看著忙碌的世界,接受著您兒子朋友們的合影請(qǐng)求,我們握著你母親的手,好像握住了解開(kāi)你詩(shī)歌密碼的鑰匙。是的,正是這“針尖上的蜂蜜 ”的品嘗,讓我們似乎抵達(dá)了雷平陽(yáng)隱秘的精神腹地。讀雷平陽(yáng)的詩(shī),總能讓人讀出一種掙扎及決絕,“讓我站在你們的對(duì)立面/一片懸崖之上,向高遠(yuǎn)的天空/反復(fù)投上幽靈般的反對(duì)票”,這種掙扎及決絕,植根于這片古老的土地,這是對(duì)故土的深情感念,而這份感念,瞬間“帶著整個(gè)世界軟下去”。正是這份柔軟,又給了詩(shī)人義無(wú)反顧的決絕,“給我子宮,給我乳房在靈魂上為我變性”“我祈盼這是一次輪回,讓我也能用一生的愛(ài)和苦,把你養(yǎng)大成人。”
李? 騫——云南省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云南民族大學(xué)教授:
雷平陽(yáng)的靈魂與故鄉(xiāng)歐家營(yíng)的符號(hào)相融化并永恒相守。他在詩(shī)中把故鄉(xiāng)符號(hào)的意涵提升到生存哲學(xué)的高度,故鄉(xiāng)的符號(hào)不但超越了個(gè)體的意義,而且它的能指和所指都產(chǎn)生了新的內(nèi)涵。如利濟(jì)河、山、故鄉(xiāng)植物、動(dòng)物等符號(hào)都在形式上實(shí)現(xiàn)了第二次整合,而符號(hào)所暗示的內(nèi)容,已經(jīng)不能根據(jù)原始的表意來(lái)解釋?zhuān)且鶕?jù)詩(shī)的審美理念去重新整理。也就是說(shuō),他詩(shī)歌中的故鄉(xiāng)符號(hào)如同利濟(jì)河的流水一樣,所描寫(xiě)的不并是流水的自然意義,而是塵世生活中的人們強(qiáng)加給“流水”的人為的內(nèi)在含義。接受者不能單純地理解其故鄉(xiāng)符號(hào)所表述的外在意義,而是要在符號(hào)原來(lái)的內(nèi)涵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擴(kuò)充延伸,要尋覓物象的背景之外的內(nèi)蘊(yùn)。
黃佩華——廣西民族大學(xué)駐校作家? 碩士生導(dǎo)師:
作為昭通作家群的代表作家,雷平陽(yáng)的創(chuàng)作始終植根于地域文化的土壤,沉浸在昭通這個(gè)具有濃郁地理環(huán)境特色氛圍之中。他的地域文化表達(dá)形式獨(dú)特且具獨(dú)創(chuàng)性,文字清新脫俗,大氣恢宏。可以說(shuō),是昭通的獨(dú)特地理人文環(huán)境孕育和造就了雷平陽(yáng)和昭通作家群。他們的成功為許多地域作家提供了樣版和經(jīng)驗(yàn)。
張柱林——廣西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廣西民族大學(xué)教授:
雷平陽(yáng)詩(shī)歌與其說(shuō)在書(shū)寫(xiě)和回憶故鄉(xiāng),不如說(shuō)是在“想象故鄉(xiāng)”,或在想象中“重返故鄉(xiāng)”。他的詩(shī)中由此太彼、虛實(shí)相生、情景交融、無(wú)中生有、動(dòng)靜結(jié)合,層次豐富。僅以《殺狗的過(guò)程》為例,詩(shī)中至少包含三重視野:殘忍(主人、屠夫)、愚忠(狗)與冷漠(旁觀者)。但首句“這應(yīng)該是殺狗的惟一方式”和尾句“說(shuō)它像一個(gè)回家奔喪的游子”卻又把一種敘事(詩(shī)歌能說(shuō)是敘事嗎?)倫理的涼薄呈現(xiàn)出來(lái),并最終在一種“齊物”的視野中變成一種悲憫。當(dāng)然我們確實(shí)能用“目的微不足道,過(guò)程就是一切”來(lái)解釋?zhuān)嗽?shī)主要在揭示人類(lèi)的殘忍。但“回家奔喪的游子”卻不允許我們停步于此。
馮艷冰——廣西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廣西文學(xué)》副主編:
家住土城鄉(xiāng),這世上還有什么能讓雷平陽(yáng)羨慕的呢?雖說(shuō)有“出云南記”,但他什么時(shí)候離開(kāi)過(guò)?盡管都是些“舊山水”,盡管他一程又一程地“送流水”,但更真切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是永遠(yuǎn)不變的“我的云南血統(tǒng)”。顯而易見(jiàn)這沒(méi)什么不好,對(duì)于云南——昭通——土城鄉(xiāng)這樣狹隘、偏執(zhí)逐漸縮小的愛(ài)的過(guò)程,土城鄉(xiāng)最后成就了他情感的沖擊坑。進(jìn)一步的探尋,我們知道這個(gè)過(guò)程不是機(jī)械單一的復(fù)制,而是由肉身的到達(dá)飛升至精神的回歸。當(dāng)我們回望他對(duì)土城鄉(xiāng)針尖一樣的愛(ài)時(shí),實(shí)際上是“我住在大海上”的遼闊;重新審視他偏倚一隅對(duì)云南的凝視時(shí),收獲的卻是“喜茫茫空闊無(wú)邊”。由次第縮減的回歸向無(wú)限空闊的出走,是雷平陽(yáng)終其一生修行的功課,詩(shī)文是他精神的舍利子。有必要提醒的是,當(dāng)我們閱讀雷平陽(yáng)作品的時(shí)候,我們隔著的并不是一個(gè)土城鄉(xiāng),一個(gè)昭通,一個(gè)云南,而是一個(gè)浩渺的天地。
李約熱——《廣西文學(xué)》副主編:
平陽(yáng)是廣西作家的好朋友,他在廣西有很多的粉絲,這次我們廣西作家、評(píng)論家來(lái)到他的家鄉(xiāng)昭通市歐家營(yíng)村探訪(fǎng),見(jiàn)到他的老母親和弟弟,還有他昭通的好兄弟們,見(jiàn)到屬于他的山川、河流和土地,他非凡的詩(shī)行后面,藏著玄機(jī)。可以這么說(shuō),平陽(yáng)的詩(shī)句燦爛,平陽(yáng)的人情溫暖。
劉廣雄——云南省作協(xié)原副主席:
現(xiàn)實(shí)總是狂飆突進(jìn)或者隨波逐流,一如雷平陽(yáng)在行政區(qū)劃及新版地圖上消失的故園土城鄉(xiāng)。雷平陽(yáng)舊居殘存的一間瓦房,以及近旁他的親人正在興建中的鋼筋水泥小樓構(gòu)成絕妙的隱喻。這個(gè)在語(yǔ)詞與思想,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生存與靈魂之間走鋼絲的人,游走于都市與山野,向上建筑,往下掘井。雷平陽(yáng)始終追求語(yǔ)言高度與思想深度的優(yōu)美對(duì)稱(chēng),就像雷平陽(yáng)舊居旁那棵巨大的核桃樹(shù),根有多深,樹(shù)冠就有多高。貯藏著六噸廟壩包谷酒的那間瓦房很快將蕩然無(wú)存,那些酒必須遠(yuǎn)走他鄉(xiāng),最終進(jìn)入雷平陽(yáng)及其友人的腸胃,核桃樹(shù)也很快將被連根拔起,連同新果和舊葉。田園將蕪胡不歸?雷平陽(yáng)修燈送流水,端居詩(shī)歌廟堂,靜觀心花怒放,以筆招魂,揮毫返鄉(xiāng)。
楊 昭——昭通學(xué)院教授:
故鄉(xiāng)是地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是一個(gè)存在,更是一種思念;回故鄉(xiāng)是一種行為,更是一種儀式,一種向來(lái)歷,向人之初,向步履致敬的儀式。雷平陽(yáng)這次返鄉(xiāng)活動(dòng),對(duì)我們每個(gè)熱愛(ài)文學(xué)的人來(lái)說(shuō)都是一次確認(rèn)自己靈魂構(gòu)造的儀式,我們自己也該探探親了。
楊榮昌——云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掛職副處長(zhǎng):
雷平陽(yáng)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置身于生活的現(xiàn)場(chǎng),真誠(chéng)地唱出生命之歌,建構(gòu)起開(kāi)闊的抒情氣場(chǎng)。云南的奇山異水歷來(lái)是詩(shī)人吟詠的重點(diǎn),也催生了無(wú)數(shù)的詩(shī)文佳作,人文與自然的交相輝映,構(gòu)成這片高原之上的獨(dú)特景觀。他的詩(shī)歌《鮮花寺》,鋪展開(kāi)一幅云南的歷史與人文畫(huà)卷,展示了個(gè)人幽微的生存經(jīng)驗(yàn)及破解當(dāng)代人精神困境的求索努力,恰如其分的修辭效果和不懈的精神追問(wèn),詩(shī)歌氣勢(shì)渾厚,匠心獨(dú)妙。
農(nóng)為平 ——大理大學(xué)教授:
在當(dāng)代詩(shī)壇,雷平陽(yáng)始終是一個(gè)特立獨(dú)行的存在。他從不追隨任何一場(chǎng)語(yǔ)言狂歡,也不屑于取媚流俗大眾,而是安靜地“蜷縮”于云嶺大地,用詩(shī)行壘砌一個(gè)充滿(mǎn)泥土氣息的詩(shī)性世界。這個(gè)世界的起點(diǎn)是歐家營(yíng)、昭魯大河、大山包,是金鼎山、瀾滄江、基諾山……這些鮮明的地域符號(hào)使其詩(shī)歌中彌散著濃烈的南高原氣息和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也是他與世界展開(kāi)對(duì)話(huà)的根祇,從而形成了既小(地域)又大(世界)的言說(shuō)空間,具有質(zhì)樸、溫暖的品格。以此為觀照,雷平陽(yáng)對(duì)現(xiàn)代化充滿(mǎn)警惕,詩(shī)歌呈現(xiàn)歌詠荒野山水、自在生命,與抨擊生態(tài)危機(jī)、道德崩塌兩個(gè)鮮明向度,流露出某種逆流而上的悲壯意味。他執(zhí)著奔走于偏遠(yuǎn)的茶林、廟宇甚至密支那,去挽留大地殘存的詩(shī)意,努力建構(gòu)一片生機(jī)盎然的“紙上曠野”。悲憫、敬畏、憂(yōu)患,始終是其詩(shī)歌令人動(dòng)容的精神內(nèi)核。
房永明——廣西作家協(xié)會(huì)秘書(shū)長(zhǎng):
?四川盆地的暖流和云貴高原的寒流在這里相撞,形成了昭通特有的高原季風(fēng)立體氣候。雷平陽(yáng)的詩(shī)應(yīng)該是人間的冷暖相融、故土與都市相撞產(chǎn)生。從他的詩(shī)里,能讀出音樂(lè)的節(jié)奏,人間的夢(mèng)想,在這里,我們更能體會(huì)《親人》的力量。雷平陽(yáng)母親在他父親墓前,讓兒子祈禱把門(mén)前的利濟(jì)河變清,讓我們真的看到了清清的利濟(jì)河,或許這就是親人的力量。讓我們有更多的詩(shī)人,雷平陽(yáng)一樣的詩(shī)人,各種不同的詩(shī)人,讓世界變得更加清爽。
?榮? 斌——廣西影視藝術(shù)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
作為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壇極具影響力的重要詩(shī)人,雷平陽(yáng)從滇東北小城昭通走向全國(guó),這既是他作為生命個(gè)體的一次孤獨(dú)遠(yuǎn)旅,也可以說(shuō)是當(dāng)下整個(gè)昭通文壇的一次集體登場(chǎng)。與大多數(shù)優(yōu)秀作家一樣,雷平陽(yáng)的創(chuàng)作一直和他腳下的這片故土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間都繞不開(kāi)鄉(xiāng)愁,繞不開(kāi)那一座座土墻搭起的家園與村莊,更繞不開(kāi)云貴高原的永恒色調(diào):灰與藍(lán)。他在貧瘠記憶的現(xiàn)實(shí)與物華天寶的背景的沖突交替中,既能昂頭凝望明艷的山川大野,亦可垂眉低首關(guān)注晦澀卑微的命運(yùn)。正如他作為一個(gè)詩(shī)人的性格:既隱忍、內(nèi)斂、偶爾孤僻,也明朗、大氣、偶爾張揚(yáng)。恰恰是這些復(fù)雜而又簡(jiǎn)單的元素,形成了雷平陽(yáng)獨(dú)特的詩(shī)歌氣質(zhì)。
柏? 樺——云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0年冬,春城,我為《大地有多重》寫(xiě)書(shū)評(píng),該書(shū)“楔子”,壯懷激烈,讓念誦著“誠(chéng)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qiáng)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詩(shī)句長(zhǎng)大的我血脈僨張,那是高天厚土無(wú)處安放的激昂與悲愴;2015年春,越南,亞太詩(shī)歌節(jié)暨世界文學(xué)大會(huì),我常看到雷平陽(yáng)遠(yuǎn)離地球村狂歡的人群,獨(dú)踞一隅在手機(jī)上寫(xiě)詩(shī),那些詩(shī)句,沉郁孤絕;2021年夏,昭通,我有幸見(jiàn)到雷平陽(yáng)的母親和弟弟,母親慈祥的目光,弟弟憨厚的笑容,讓我明白了故鄉(xiāng)和親人對(duì)雷平陽(yáng)寫(xiě)作的意義。我想,不管雷平陽(yáng)曾經(jīng)或即將摘取多少文學(xué)勛章,當(dāng)他回到鋼筋混凝土的堅(jiān)硬叢林,回到星星被城市霓虹燈遮蔽的漫漫長(zhǎng)夜,能夠溫暖、慰藉、支撐他的,依然是故鄉(xiāng)歐家營(yíng)鮮美如初的芬芳回憶。

(昭通日?qǐng)?bào)全媒體記者 楊明 毛利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