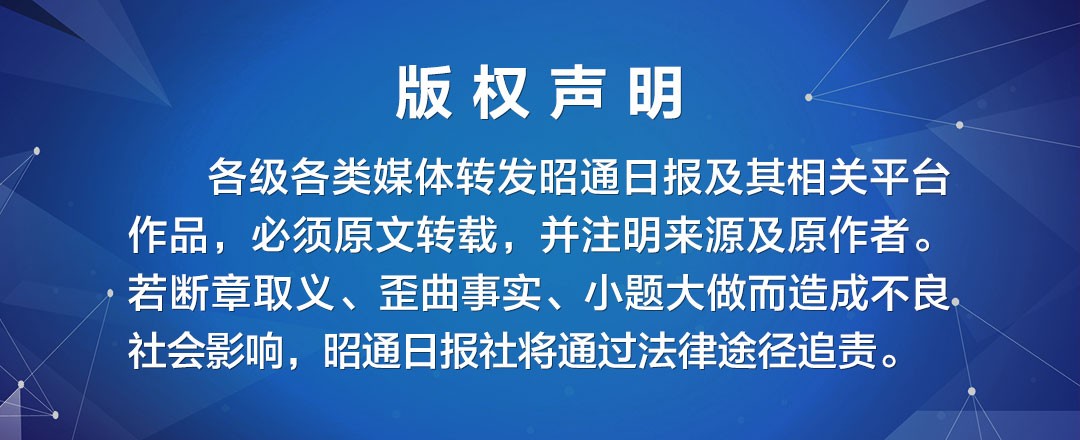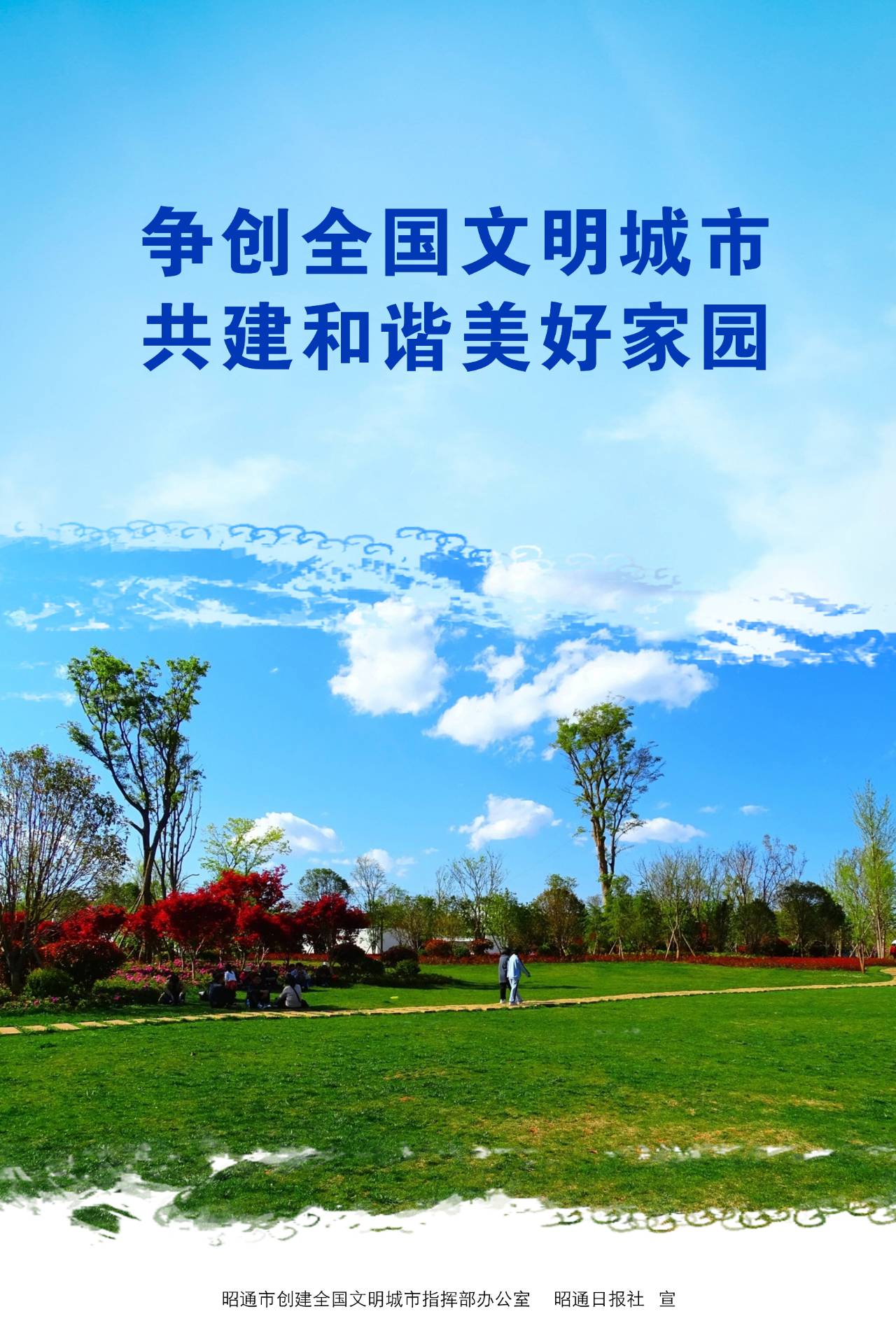2021-08-08 12:38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遷徙,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鄉(xiāng)。每一個故鄉(xiāng)長則千年,短則幾十年。
詩人尹馬對我這個威信人說,鎮(zhèn)雄是威信的故鄉(xiāng)。
是的,鎮(zhèn)雄也是彝良的故鄉(xiāng)。
歷史使然,鎮(zhèn)雄、彝良、威信,在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歷經(jīng)歲月的蹉跎和紛爭,分分合合。
公元前135年,西漢武帝建元六年置犍為郡,共12個縣,鎮(zhèn)雄被置為南廣縣,包括現(xiàn)在的昭通市鎮(zhèn)雄、彝良、威信、鹽津四縣及四川省筠連縣。
東晉咸和九年(334年),復(fù)置南廣縣。
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置芒部路軍民總管府,轄益良州(今彝良)、強(qiáng)州(今彝良東北及威信一帶)。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總督錫戶奏“鎮(zhèn)雄州距府遼遠(yuǎn),諸多不便,請將該州升為直隸州,增設(shè)一縣(彝良縣),仍隸屬鎮(zhèn)雄州”。
……
赤水河與扎西河交匯點(diǎn)水田鎮(zhèn)河壩村渡口。通訊員 任正銀 攝
三地人民穿梭在彌久的歲月中,根植故鄉(xiāng),又被剝離故鄉(xiāng)。
一條赤水河,把鎮(zhèn)雄、彝良、威信交融在一起,流向無法割舍的遠(yuǎn)方。
云南昭通是彝族的發(fā)祥地之一,在赤水河流域鎮(zhèn)雄、彝良、威信三縣居住的民族中,彝族均為本土民族,漢族、苗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為外來民族。
漢武帝開發(fā)西南時,便有漢族移居威信境內(nèi);明代初期,苗族從貴州威寧遷入彝良縣境內(nèi)。元末明初,楊姓、韓姓、熊姓從貴州畢節(jié)的林口遷居鎮(zhèn)雄母享,居住一段時間后,分為兩大支系,一支從母享遷入威信雙河天池,另一支從母享遷入鎮(zhèn)雄果珠……
遷徙是一場戰(zhàn)爭,是一場未知且驚險的生命歷程。每到一處,人類皆撒下堅(jiān)韌和執(zhí)著的種子,長成小草和參天大樹,抵擋狂風(fēng)暴雨,與山川江河日夜為伴。
在炎帝、黃帝與蚩尤在涿鹿鏖戰(zhàn)之后的五千年中,由于戰(zhàn)亂、饑荒等種種原因,苗族由北到南、由東到西、從國內(nèi)到海外,經(jīng)歷了5次大規(guī)模、大范圍的民族大遷徙,這樣長時間、大幅度、大規(guī)模、遠(yuǎn)距離艱苦卓絕的大遷徙,不僅在中華民族56個民族中少見,在世界2000多個民族中也是極為罕見的,所經(jīng)受的苦難更是不言而喻,這對苗族的歷史、文化、習(xí)俗、生產(chǎn)、生活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由于不斷地遷徙,延緩了其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進(jìn)程,生產(chǎn)力水平長期處于低速發(fā)展的落后狀態(tài)。
當(dāng)人類進(jìn)入文明時代,遷徙的目的變得多元化,它以更豐富的形式、更樂觀的態(tài)度,促成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1世紀(jì),在中國大地上開展的這場轟轟烈烈的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易地扶貧搬遷賦予了“遷徙”另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獨(dú)有的寓意。搬離積苦積貧、落后愚昧之地,叫醒心靈和身體一同向往更美好的生活——這場來自和平年代有計劃、有規(guī)劃、有依據(jù)的遷徙,改變了中華民族在此之前逃避戰(zhàn)爭和饑荒時孤單、迷茫的遷徙行動,因?yàn)樵谶@場遷徙的背后,有一個強(qiáng)大的母體——中國。

龍溪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代理媽媽”熊萍(右三)等和孩子們合影。
在威信縣龍溪小區(qū)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有一支由69名志愿者組成的“代理媽媽”志愿服務(wù)團(tuán)隊(duì),專為這場遷徙而生。威信縣城所在地扎西鎮(zhèn)內(nèi)有九條溪水,原名九龍溪,后更名為扎西河,為赤水河北支源頭。
2019年,為了幫助威信縣龍溪小區(qū)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的孩子們更好地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威信縣婦聯(lián)組建了一支定向服務(wù)龍溪小區(qū)的“代理媽媽”志愿服務(wù)團(tuán)隊(duì)。龍溪小區(qū)252個留守兒童由69名志愿者擔(dān)任他們的“代理媽媽”,她們深入到孩子的家庭和學(xué)校了解其生活和學(xué)習(xí)情況,給予孩子們陪伴和關(guān)懷。
龍溪小區(qū)A1幢2708號,是苗族小姐妹韓香義、韓香美的新家,她們一家四口于2019年初從威信縣扎西鎮(zhèn)墨黑村搬到龍溪小區(qū)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縣婦聯(lián)在為她們挑選“代理媽媽”時,特意挑選了一名苗族女干部——威信縣衛(wèi)生健康局干部熊萍。
這些孩子的父母長期不在身邊,聊天是最快樂的陪伴——這是熊萍的“代理媽媽經(jīng)”。性格開朗的她,每個周末總能和孩子們聊得熱火朝天。
在龍溪小區(qū),熊萍除了韓香義、韓香美兩個女兒,還有四個兒子分別來自另外四個家庭,孩子們都親切地叫她“熊萍媽媽”。
又是一個周末,新一輪的聊天大會開啟,這次大會地點(diǎn)是在韓香義、韓香美家。同是同班同學(xué)的四個兒子踴躍發(fā)言,他們互相“揭短”“告狀”,一籮筐的壞事被抖落一地。9歲的韓香義、8歲的韓香美在一旁安靜地聽著。他們時而捧腹大笑,時而爭得臉紅脖子粗。14歲的魏圓說道:“熊萍媽媽,放假之前吳海友拿東西砸了豪車,被老師批評了。”13歲的吳海友急忙解釋道:“不是豪車,是面包車。”熊萍說道:“我問過老師了,是面包車,但是以后不允許這樣了。” “嗯嗯。”吳海友點(diǎn)頭答應(yīng)。
“趙隊(duì)長、趙老大,說一說放假之前你有沒有干過壞事?”熊萍把話題指向了12歲的趙長林。趙長林是4個兒子中年齡最小、最大方、最調(diào)皮的,為了管好幾個孩子,熊萍讓趙長林當(dāng)了隊(duì)長。“也沒什么,就是上課講小話,還丟了紙團(tuán)打同學(xué)。”趙長林不好意思地說道。“熊萍媽媽,他還打破了教室里的玻璃。”12歲的李清海跳起來說道。“這個事情我問過老師了,玻璃沒有打碎,只是裂了縫,但是這種危險的事情以后千萬不能做了。”熊萍嚴(yán)肅地說。“我知道錯了,以后不這樣做了。”趙長林向熊萍承認(rèn)了錯誤。房間里充滿了歡聲笑語,孤獨(dú)和寂寞落荒而逃。
每次來家訪,除了陪孩子們聊天,寫作業(yè)、寫日記也是必須要完成的。這次來,熊萍還給孩子們帶來了口罩和酒精,給兩個女兒帶來了兩本《簡筆畫》。
這只是其中一個“代理媽媽”的故事。除“代理媽媽”之外,政府還采取了許多方式來服務(wù)易地扶貧搬遷群眾,如“樓棟長”“片區(qū)長”等特設(shè)崗位,他們都是實(shí)施易地扶貧搬遷政務(wù)服務(wù)的一個個小小的身影、一顆顆小小的水滴,若他們不干涸,也會成為水滴石穿的另一種傳奇。
似乎所有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qū),都在經(jīng)歷著一場由安置區(qū)蛻變?yōu)楣枢l(xiāng)的成長之路。這條路,需要接納、磨合、理解、包容,需要花時間去經(jīng)營、去釀造。
威信這座小城,將會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努力成長為龍溪小區(qū)這群孩子的第二個故鄉(xiāng)。
而有一種故鄉(xiāng),只屬于父輩;有一種故鄉(xiāng),只屬于子孫后代。
在鎮(zhèn)雄縣坡頭鎮(zhèn)大田村海拔1100米的山下,桐車河潺潺流過,這是赤水河流經(jīng)此地的名字。
巨型的牛皮鼓和蘆笙雕塑矗立在水田村寨門口。這是一個苗族村寨,雕塑旁邊是假山和池塘,“大美龍洞,田園勝景”八個大字閃耀在假山上。
距離寨門下方四五米處的柏油路邊,有一座干凈漂亮的公廁。藍(lán)色的琉璃瓦裝飾屋頂,一米高的紅色墻裙,“公共廁所”的字樣和男女洗手間的標(biāo)志明顯可見。公廁外“公廁管理人員崗位職責(zé)”“公廁管理制度”“公廁管理公示牌”整齊地掛在公廁墻上。公廁身后,是蒼翠挺拔的群山,紅藍(lán)相間的公廁在這抹綠色中間特別顯眼。
雕塑下面,一個寬敞整潔的廣場大方出落在眼前。49歲的陶廷輝,家就在廣場旁邊,一座兩層高的樓房。“嗡嗡嗡……”從他家屋內(nèi)傳來自動洗衣機(jī)轉(zhuǎn)動的聲音。
門外,陶廷輝種的葡萄蔥蔥郁郁爬滿了架子,月季花開得正好,儼然成了廣場的綠化帶。在水田村,好些村民院子前都有葡萄藤和盆栽,閑情逸致的小情趣隨處可見。
而對于房子,陶廷輝有著深刻的記憶,一部分來自父輩的記憶,一部分來自他自己的經(jīng)歷。

威信縣龍溪小區(qū)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diǎn)“代理媽媽”熊萍教“女兒”韓香美練習(xí)普通話。
民國初期,陶廷輝的爺爺原本居住在水田村猴山,猴山因山里猴子多而得名。
那時候窮,房子是用包谷稈、高粱稈搭起來的。有一年,奶奶的煤油燈意外地?zé)税取⒏吡欢挘患胰说姆孔踊癁榛覡a。房子沒了,猴子也時常成群結(jié)隊(duì)去地里掰包谷吃,已經(jīng)到了必須要離開的時候,一家人商量后,從猴山搬遷到大田村村委會所在地。
搬遷是在民國中期。新房子依舊是用包谷稈、高粱稈搭起來的,在當(dāng)?shù)刈×似甙四辍R惶焱砩希胀⑤x的二嬸點(diǎn)燃火把去茅房,一把火再次把陶家的房子燒成灰燼。
再也不想用包谷稈、高粱稈修房子了,再苦再累,也要用石頭修,陶家的男人們立下了誓言。
第二年,正值解放初期,房子修好了。用石頭砌墻,沒有石灰、水泥、瓦片,只能用泥巴敷墻,用草蓋頂。
20世紀(jì)80年代,陶廷輝家房子重建,用了石灰、水泥和鋼筋,蓋了瓦頂。90年代,蓋了水泥頂,不再漏雨。2017年,加蓋了二層樓。
大田村越來越美,村民們原本就愛干凈,在脫貧攻堅(jiān)期間,村干部們根本不用操心村子里衛(wèi)生的事情。
猴山的猴子越來越少,掰包谷的猴子已死去或老去,爺爺故鄉(xiāng)的莊稼再也沒有醒過來。
對于陶廷輝來說,每年最盼望的事,就是在外務(wù)工、讀書的兒女們回家團(tuán)年,大田村才是他們不可替代的故鄉(xiāng)。
距離陶廷輝家?guī)坠锾幍牡侣〈謇罴艺幼≈鬃逋?/span>
鎮(zhèn)雄境內(nèi)的白族,祖籍在南京、江西,明代時因躲避戰(zhàn)亂而遷徙到貴州省貴陽、平遠(yuǎn)、黔西、大定、畢節(jié)等地,還有一部分是明朝征南將士與當(dāng)?shù)厝私Y(jié)合的后代,清末時期由貴州進(jìn)入鎮(zhèn)雄,所以鎮(zhèn)雄白族與貴州白族有著歷史淵源,至今還有往來。
自小在鎮(zhèn)雄黑樹鎮(zhèn)碗水村長大的李龍祥,從鎮(zhèn)雄縣司法局退休后,移居昆明,他家和貴州白族一直保持有聯(lián)系。對于白族的風(fēng)俗、服飾,碗水村已經(jīng)沒有痕跡可尋了。
而在李家寨白族老人李龍發(fā)的往事里,還存有另一番印記。
每一個孩子眼里的母親,就是獨(dú)一無二的。梳著尖尖頭、大圓領(lǐng)上繡的五路花、系著腰帶的長裙,是李龍發(fā)對母親最深刻的記憶。那時候房子為石木結(jié)構(gòu),每一間屋子的門都有二三十厘米高的木門檻,他總能看見母親忙碌的背影,總能看見母親搭在門檻上的長裙。
70年過去了,母親依舊年輕地活在李龍發(fā)的記憶里,而他已是頭發(fā)花白、行動緩慢的80歲老男孩。從記事起,母親平日里不管是勞作,還是外出,一直穿著民族服裝。而今,石木房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棟三層近七百平方米寬的大樓房。
二姐出嫁時,李龍發(fā)剛好10歲。那天,跟母親一樣,姐姐梳著尖尖的“三把頭”,前額梳一束,后腦梳兩束,同束于頭頂呈直立形狀,頭頂上還覆上青黑色布帕,身穿大圓領(lǐng)花領(lǐng)衣服和大長裙,站在人群里簡直耀眼得很。家里擺了酒席,迎親、送親的禮節(jié)煩瑣而精致。對于這場婚禮,他大概只記得這些畫面。
時光走得太快了,70年前的送親隊(duì)伍里,李龍發(fā)還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他忘記了二姐夫當(dāng)新郎時得意的樣兒,忘記了二姐和二姐夫是否拜過堂、作過揖;他不太確定,二姐出嫁那天,母親的臉上可曾掛滿了淚珠;他更不知道,二姐出嫁時,縱然有千般不舍,也有萬般待嫁的羞澀和喜悅。他努力地回憶,可什么都記不起來了。
如果時光能倒回,李龍發(fā)想仔細(xì)看看那場婚禮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場景,那是他這一生印象最為深刻、最具有白族儀式的婚禮。首先是二姐的白族服飾,這是唯一可展示本民族屬性的物件。其次是二姐夫所具備的標(biāo)準(zhǔn)女婿條件,第一必須是白族,第二必須是本民族中13姓中的其中一姓。這13姓分別是李、毛、張、王、汪、盧、龍、羅、楊、孫、馮,還有兩姓,李龍發(fā)怎么也想不起來了。
坡頭鎮(zhèn)李家寨白族老人李龍發(fā)在回憶本民族往事。
解放前,鎮(zhèn)雄白族是不允許與外族通婚的,本族通婚也嚴(yán)論輩分,只能同輩結(jié)婚,違反了以上族規(guī)就會被家法處置。
解放后,鎮(zhèn)雄白族的婚姻制度逐漸變得開放起來,只是再也看不見梳尖尖頭、穿大圓領(lǐng)花衣服的新娘,而新郎是不是白族,似乎沒有人再去追究了。在李龍發(fā)家里,孫兒媳婦都是漢族。
如今,在這個家里,沒留下一套白族的衣服,已經(jīng)很多年沒有人穿、沒有人會做了,鎮(zhèn)雄白族原本就沒有語言和文字,現(xiàn)在連服飾都快消失了。對此,李龍發(fā)感到非常遺憾。
關(guān)于鎮(zhèn)雄白族的一切,是否還能在歷史的光影中找回記憶,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知道,鎮(zhèn)雄縣坡頭鎮(zhèn)德隆村李家寨,早已成為鎮(zhèn)雄白族22代人的百年故鄉(xiāng),如今已600多年。 (未完待續(xù))

馬 燕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