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08 12:29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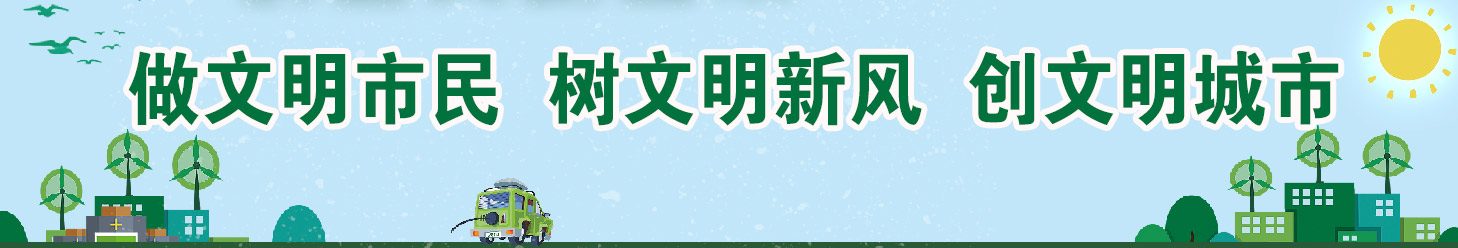
彝族是個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歷法,文化積淀厚重,作者從族群深處承接下的眾多文化元素,被他的創(chuàng)作文本大量吸納,由此,作品的創(chuàng)作風格充滿民族性和生命活力。呂翼的小說,我基本都讀過。因為同是彝族的身份,他的作品總讓我倍感親切。他也是目前為止,我跟蹤作品而寫評論最多的作家。從之前的《風過楊樹莊》《疼痛的龍頭山》,到《寒門》《嶺上的陽光》《比天空更遠》等,所有作品都沒有離開他的母族,以及族群心靈圖景或靈魂寄居,小說集《馬嘶》同樣顯示出這一寫作特點。
小說集《馬嘶》的創(chuàng)作范圍涉及彝村、鄉(xiāng)間民俗、金沙江流域、烏蒙山脈及縣級官場,作家的民族性體現(xiàn)濃重而深厚。通讀全集6篇小說,其中,《冤家的鞋子》《馬嘶》為歷史題材,應算為上下篇承接關系的小說。民族特性與地域特色,造就了整個故事的起因與發(fā)展。歷史上,彝族確實有搶親的風俗。所以,小說的開篇是彝族漢子烏鐵騎著他最心愛的,名叫“馬老表”的棗紅馬,把漢族姑娘開杏搶走。這兩篇各有側重、總情節(jié)描述的作品,從開杏對烏鐵的怨恨,到無奈再到接受,疊加成一雙納好的布鞋的最終歸屬而層層展開,并在這個起因中完成了上下承接的故事延續(xù)。這兩篇作品沒有“去歷史化”,啟用了抗戰(zhàn)時期的大背景環(huán)境,引入滇軍各民族子弟參與抗日的歷史元素。這個情節(jié)線的設計,使作品的精神構建變得高貴而悲壯。呂翼憑借自身的民族認知,準確地把控地域文化內(nèi)涵,從歷史的角度切入,建立了族群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共生體系。作品的根性寫作還體現(xiàn)在《冤家的鞋子》的結尾,從戰(zhàn)場九死一生返回且失去了雙腿的烏鐵,面對要給他穿鞋的開杏,顫抖了一下說:“沒有必要了,算了吧。”《馬嘶》的結尾是,見到開杏的初戀,即將奔赴陜北的漢族青年胡笙,烏鐵說:“開杏,把你做的那雙鞋給他吧,只有他才配穿!”戰(zhàn)爭與民間的融合描寫,將邊地民族原始記憶中壯美的血性,彝族漢子的硬朗和柔情與愧疚,坦蕩蕩直呈于文字間。呂翼說過,他的寫作,是將民族的精神張揚和重塑。一位彝族作家,迸盡全身的溫度,塑造這樣的同族男人,他對族群的熱愛,毫無掩飾地表明是源于根脈。
少數(shù)民族作家與族群的聯(lián)系,是一種與生俱來、深植骨髓的精神牽絆。作為金沙江流域土生土長的彝族作家,呂翼的寫作是留在族群中的寫作。盡管他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他的創(chuàng)作界面是基于鄉(xiāng)村族地詮釋中的延伸。他的作品訴求,仍然是從現(xiàn)實和精神的原鄉(xiāng)向外行走。
彝族傳統(tǒng)的家支習俗和畢摩文化對呂翼產(chǎn)生的影響,在他本集小說中均得到展現(xiàn)。如,人去世,要請祭司念消災經(jīng)、指路經(jīng)、取魂經(jīng);家族支系間的追殺,稱為打冤家;彝族不與外族通婚;出門前,要殺雞看卦;畢摩和蘇尼,可以作法等。呂翼的民族意識與其生活的烏蒙山脈密不可分,對族群的往昔和現(xiàn)狀的反思,作為作品的基礎底色,呂翼系列小說也給予了此類釋放。《逃跑的貔貅》《來自安第斯山脈的欲望》《命定的石頭》《割不斷的苦藤》都是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前三篇講述了普通彝族村民不同的故事。這份族群情懷和立場,是一種流動的血脈,在人物塑造的選擇中,常以成年男女來體現(xiàn)。如《逃跑的貔貅》中的舍且和芬芳;《來自安第斯山脈的欲望》中的二娃、卓雅和格布;《命定的石頭》中的覺布和阿枝,馬寬與英姿。這些人物表面是族人外化的形式,但實質是內(nèi)化了。外在,以經(jīng)濟至上的價值觀,在改變著彝人淳樸的內(nèi)部視野。社會的現(xiàn)代進程,商品經(jīng)濟取代了祖輩流傳的自然經(jīng)濟,理智與非理智的行為方式,使族人的世界觀發(fā)生著改變。明清思想家王夫之有言:“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呂翼正是清楚全面的“所以然”,所以他作品中人物及故事必然沒有離開族地,必然是在烏蒙大地上艱難生存的生活原型。他們在現(xiàn)代進程中迷茫和迷失過,但是,不管過程如何,都依然保持著頑強努力的內(nèi)心,保存著族性中的尊嚴。《割不斷的苦藤》很有官場小說的味道,充滿憂患意識及悲憫情懷,主要人物以悲劇結束,寫作風格也較以上幾篇小說略有不同。民族成分弱化,人物、語境、言詞、情節(jié)脈絡等,鋪陳了官場中的拘謹和小心翼翼。苦寨里,吃百家飯長大的辛苦,官至副縣長,最終因權力產(chǎn)生的傲嬌,讓他忘了他為苦寨割去苦藤的初心,終了只好自己作了了斷。這部小說的根性寫作轉向以傳統(tǒng)敘事的形式拓展,與審美傳統(tǒng)和審美習慣緊密相連。文學是人學,源于根性的文學,依然是把人性、道德倫理放在審美關照下進行的。
無論歷史或現(xiàn)實,呂翼作品的現(xiàn)場和在場,必置于族群人物、地域風物里,而人物與風物必相互照應、互相滲透。作家有意將人物和風物放置于烏蒙山水中這個整體加以考量,幾個故事的人物塑造就體現(xiàn)出了時代背景的龐大影響。
莫言稱,鄉(xiāng)土是他的根;同樣,族群也是呂翼的根。 呂翼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覺,他的彝族身份強化出了他獨有的民族眼光和民族意識。寫作中,他一直保持著深扎的狀態(tài),所以,他的文字行走是有根的行走,寫作也是根性的寫作。小說集《馬嘶》沒有停留在族性層面的獵奇上,而是深入族群的內(nèi)部,以特有文化背景推動全體作品的進程。
 作者? 師立新
作者? 師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