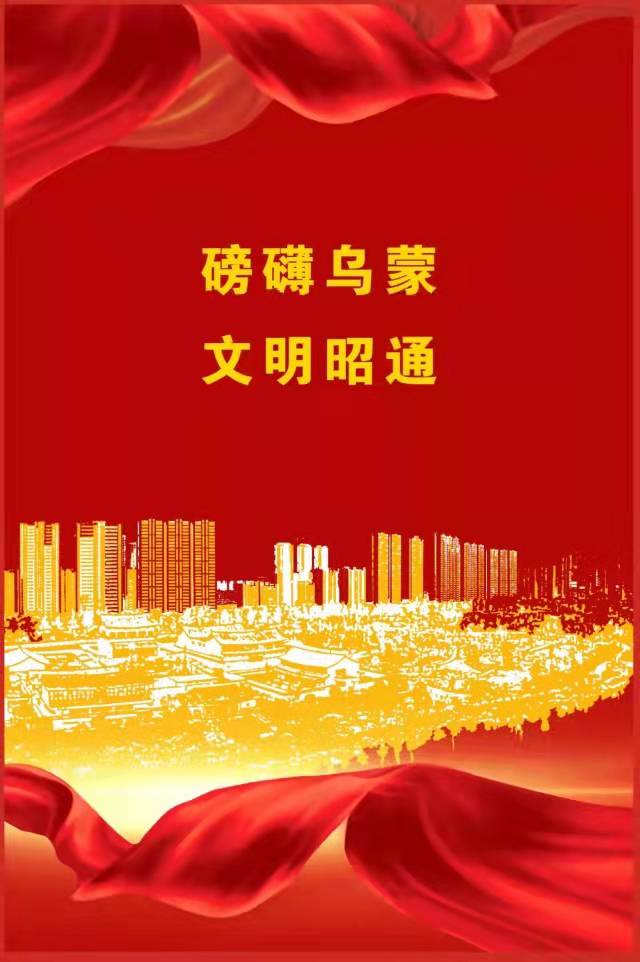2022-01-15 20:30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摘 ?要:呂翼中篇小說(shuō)成就顯著,表現(xiàn)為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交匯。以精準(zhǔn)扶貧為重心展開(kāi)的對(duì)彝族當(dāng)代命運(yùn)的民族志敘述,構(gòu)成了呂翼中篇小說(shuō)的重要敘事維度。而對(duì)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彝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掘,及對(duì)彝族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意義的展示,體現(xiàn)出呂翼中篇小說(shuō)民族志敘述疆域的拓展。呂翼中篇小說(shuō)同時(shí)以彝、漢關(guān)系與抗日戰(zhàn)爭(zhēng)為背景,積極進(jìn)行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作出了貢獻(xiàn)。
關(guān)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呂翼;中篇小說(shuō);彝族;民族志
作者:吳道毅,中南民族大學(xué)
21世紀(jì)以來(lái),彝族70后作家呂翼在文學(xué)道路上快速成長(zhǎng),取得了十分豐碩的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僅長(zhǎng)篇小說(shuō)就出版了《土脈》《村莊的喊叫》《疼痛的龍頭山》《寒門》等七部。2015年以來(lái),呂翼又進(jìn)入到一個(gè)創(chuàng)作高峰期,推出《冤家的鞋子》《逃跑的貔貅》《馬腹村的事》《逃亡的?貀》《馬嘶》《竹筍出林》《主動(dòng)失蹤》等十多部中篇小說(shuō)——這些作品在《人民文學(xué)》《民族文學(xué)》《中國(guó)作家》等文學(xué)期刊發(fā)表,或被《小說(shuō)月報(bào)》《小說(shuō)選刊》《中篇小說(shuō)選刊》等廣泛轉(zhuǎn)載,或進(jìn)入年度“中國(guó)中篇小說(shuō)精選”行列,顯示出很高的思想藝術(shù)水準(zhǔn),作品《馬嘶》還于2020年榮獲第十二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駿馬獎(jiǎng)”。呂翼中篇小說(shuō)一方面以云南烏蒙山區(qū)為地域背景,以精準(zhǔn)扶貧為焦點(diǎn),描繪彝族的生活巨變,充分發(fā)掘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的彝族傳統(tǒng)文化,形成了濃厚的民族志敘述特色;另一方面則以彝、漢文化交往與抗日戰(zhàn)爭(zhēng)為背景,表現(xiàn)彝、漢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換言之,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交匯構(gòu)成了呂翼中篇小說(shuō)的總體創(chuàng)作特點(diǎn),并在探索當(dāng)代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敘事路徑與推動(dòng)當(dāng)代文化建設(shè)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
一、地方社會(huì)變遷的民族志敘述
?“民族志主要是對(duì)一個(gè)特定民族群體的社會(huì)和文化制度進(jìn)行詳細(xì)的調(diào)查、描述和研究。”[1]作為彝族作家,呂翼有著自覺(jué)的民族意識(shí),對(duì)本民族深懷赤子之心,深切地盼望彝族同胞過(guò)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呂翼中篇小說(shuō)的一個(gè)重要敘事維度,是對(duì)彝族生活進(jìn)行的民族志敘述。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關(guān)注彝族父老鄉(xiāng)親的生存命運(yùn),是他義不容辭的責(zé)任與光榮的歷史使命。因此,書寫改革開(kāi)放時(shí)代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描寫彝族人民在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中擺脫絕對(duì)貧困、走向小康的輝煌歷程,是呂翼中篇小說(shuō)民族志敘述的主要內(nèi)容。
在對(duì)脫貧攻堅(jiān)的民族志敘述中,呂翼中篇小說(shuō)沒(méi)有回避對(duì)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父老鄉(xiāng)親貧困生存狀態(tài)的客觀書寫。呂翼清楚地知道,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父老鄉(xiāng)親的貧困是一種令人憂慮的現(xiàn)狀,是阻撓他們過(guò)上幸福生活的嚴(yán)重障礙。在呂翼筆下,云南烏蒙山區(qū)屬于地處云南、貴州、四川三省毗鄰的烏蒙山區(qū)的一部分,由于生存環(huán)境較為惡劣,在改革開(kāi)放的今天,這里依舊很貧窮。《馬腹村的事》中的馬腹村是個(gè)彝族村莊,地理位置險(xiǎn)要,稱得上“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zhēng)之地”,但到了和平年代,不僅面臨著“行路難,飲水難,做產(chǎn)業(yè)難”等問(wèn)題,而且村民住房條件普遍“原始落后”——“整個(gè)村子都是土墻房,木桿串斗,茅草苫頂”,其中大多都是幾十年的老房子,一旦遭遇風(fēng)雨與地震災(zāi)害,隨時(shí)都會(huì)倒塌。因此,“世世代代住這里的老百姓,日子就過(guò)得煎熬”。《竹筍出林》中的背篼村長(zhǎng)期以來(lái)就是貧窮的彝族村寨。千百年來(lái),由于地處偏遠(yuǎn)、山高水深與交通不便,基礎(chǔ)設(shè)施簡(jiǎn)陋,本地資源優(yōu)勢(shì)無(wú)從轉(zhuǎn)化為商品優(yōu)勢(shì),加之戰(zhàn)亂、自然災(zāi)難頻發(fā)與文化教育落后,“窮鬼蘇沙尼次”扼住了背篼村人的“脖頸子”。過(guò)去,背篼村人的祖先從平原地區(qū)來(lái)到烏蒙山深處的背篼村,為的是躲避戰(zhàn)亂,但在和平時(shí)代,背篼村人卻陷入貧困。即使到了改革開(kāi)放時(shí)期,麻達(dá)的母親因?yàn)榇┎簧弦患](méi)有補(bǔ)丁的衣服而受到城鎮(zhèn)人的鄙視與人格侮辱,便偷偷地跟著外地貨郎跑了,一去不回。村支書勒吉的兒子吉地不由得怨天尤人,責(zé)怪自己生錯(cuò)了地方,感到生在背篼村是一種“恥辱”。背篼村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窮鬼蘇沙尼次趕跑”。
呂翼中篇小說(shuō)民族志敘述的著重點(diǎn)與主旋律,是書寫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在云南烏蒙山區(qū)打響的偉大壯舉,詮釋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對(duì)于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人民的劃時(shí)代意義,展示云南烏蒙山區(qū)各族干部、群眾投身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熱情、干勁與斗志,并因此歌頌黨和政府實(shí)施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略決策的正確性。呂翼認(rèn)識(shí)到,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發(fā)起的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從根本上改變了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人民的命運(yùn),為他們帶來(lái)福祉,使他們擺脫貧困,解決了溫飽,進(jìn)而過(guò)上了小康生活的好日子。在《馬腹村的事》中,在省住建廳扶貧干部澤林的帶領(lǐng)下,在上級(jí)相關(guān)部門大力支持下,經(jīng)過(guò)全村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道路與交通等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舊房與危房改造、文化旅游業(yè)開(kāi)發(fā)、勞務(wù)輸出等在馬腹村有序?qū)嵤撠毠?jiān)任務(wù)逐步完成,最終取得全面勝利。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澤林更是發(fā)揮出讓黨的精準(zhǔn)扶貧工作落地生根的重要作用。經(jīng)他的努力,村里爭(zhēng)取到巨額資金,在一年內(nèi)就修通出山公路,避免了村子被整體搬遷的命運(yùn)。此后,他繼續(xù)帶領(lǐng)全村干部群眾按脫貧標(biāo)準(zhǔn)改造舊房與危房,開(kāi)發(fā)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文化旅游業(yè)……最終使馬腹村呈現(xiàn)出全新面貌,徹底告別了貧困。在《生為兄弟》中,省交通廳處長(zhǎng)賀南森擔(dān)任倒馬坎村扶貧隊(duì)長(zhǎng),與曾經(jīng)結(jié)拜的兄弟、馬腹村扶貧隊(duì)長(zhǎng)馬多不期而遇。在扶貧工作中,他們并肩作戰(zhàn),相互支持,誓死趕跑窮鬼“蘇沙尼次”。倒馬坎村群眾對(duì)賀南森工作的支持欠積極,馬多暗中囑咐鄉(xiāng)親們要學(xué)會(huì)感恩。馬腹村發(fā)生大面積豬瘟,賀南森第一時(shí)間趕到現(xiàn)場(chǎng)幫助馬多解困。兩年內(nèi),二人都如期完成各自村寨的脫貧攻堅(jiān)任務(wù)。在《竹筍出林》中,縣政府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作出對(duì)背篼村進(jìn)行整體搬遷的決策,同時(shí)決定在背篼村原有的竹林、竹筍上大做文章,大力推進(jìn)竹林、竹筍、竹編工藝品的產(chǎn)業(yè)化與商品化進(jìn)程,窮鬼“蘇沙尼次”被徹底“降服”。在《主動(dòng)失蹤》中,金沙江連心大橋的立項(xiàng)與建設(shè)具有劃時(shí)代意義。它既是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人民脫貧致富的橋梁,承載著他們幾千來(lái)的熱切愿望,也是一條黨和彝族人民心連心的橋梁。
呂翼中篇小說(shuō)民族志敘述還通過(guò)對(duì)脫貧攻堅(jiān)中內(nèi)生型人才的書寫,隱喻新時(shí)代云南烏蒙山區(qū)彝族的成長(zhǎng)。《竹筍出林》中的吉地是背篼村村支書勒吉的兒子,父子間曾經(jīng)發(fā)生過(guò)強(qiáng)烈的代際沖突和文化觀念矛盾。勒吉擔(dān)任村支書30多年,辦事敬業(yè),為人正直,曾在農(nóng)村土地承包、發(fā)展生產(chǎn)等方面作出過(guò)突出貢獻(xiàn),與年少時(shí)的兒子吉地父子情深。然而,他輕視教育、不懂商品經(jīng)濟(jì)規(guī)律、容不得吉地反駁他的觀點(diǎn),遇到吉地經(jīng)商失敗便簡(jiǎn)單粗暴地與吉地決裂,也引發(fā)吉地對(duì)他的仇恨與反叛。生活的封閉、文化的落后、觀念的保守與方法的簡(jiǎn)單,導(dǎo)致勒吉跟不上改革開(kāi)放的步伐,難以改變生存的現(xiàn)狀,更難以帶領(lǐng)群眾走上富裕之路。與父親相反,吉地在遭受生活的挫折中不斷成長(zhǎng)。吉地非常熱愛(ài)家鄉(xiāng),但他與父親勒吉最大的不同,是他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姿態(tài)與對(duì)生存環(huán)境的深刻反思,他敢于走出山寨到山外闖蕩世界。本地的商海沉浮,東莞打工創(chuàng)業(yè)的磨礪,回縣城開(kāi)公司當(dāng)老板的順?biāo)欤蚬r(shí)接受黨組織的教育等經(jīng)歷,把吉地鍛造成時(shí)代的弄潮兒,讓他在背篼村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中擔(dān)起了大梁和重任。《主動(dòng)失蹤》中的劉仁貴是馬腹村人,初中沒(méi)畢業(yè)便輟學(xué)。十多歲跟他父親學(xué)會(huì)了石匠手藝,后來(lái)到廣東建筑公司打工,經(jīng)過(guò)十多年打拼后自己當(dāng)上老總,成為村里有名的富人與能人。在馬腹村脫貧攻堅(jiān)的關(guān)鍵階段,劉仁貴在縣領(lǐng)導(dǎo)感召下回到村里擔(dān)任村主任,在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中發(fā)揮出強(qiáng)有力的領(lǐng)導(dǎo)作用[2]。吉地、劉仁貴的成長(zhǎng),喻示了新時(shí)代彝族的成長(zhǎng)。
二、地方性知識(shí)的發(fā)掘與呈現(xiàn)
地方性知識(shí)是帶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人類智慧結(jié)晶,關(guān)聯(lián)著民族或族群獨(dú)特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民族風(fēng)習(xí)、倫理體系與宗教觀念等,凝結(jié)著民族地域文化的精神內(nèi)核。正如人類學(xué)家吉爾茲指出:“承認(rèn)他人也具有和我們一樣的本性則是一種最起碼的態(tài)度。但是,在別的文化中間發(fā)現(xiàn)我們自己,作為一種人類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為眾多個(gè)案中的一個(gè)個(gè)案,作為眾多世界中的一個(gè)世界來(lái)看待,這將會(huì)是一個(gè)十分難能可貴的成就……如果闡釋人類學(xué)家們?cè)谶@個(gè)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話,他就應(yīng)該不斷申述這稍縱即逝的真理。”[3]在全球化與后現(xiàn)代語(yǔ)境下,地方性知識(shí)愈益凸顯它的價(jià)值與魅力,展示著民族文化的豐富多樣性。呂翼察覺(jué)到,彝族傳統(tǒng)文化不僅是一種獨(dú)特的地方性知識(shí),而且在當(dāng)代彝族人現(xiàn)代性訴求中釋放著強(qiáng)勁活力。呂翼中篇小說(shuō)的另一重要維度,是對(duì)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重要組成部分的彝族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掘,并進(jìn)一步拓寬了民族志敘述的領(lǐng)域。
呂翼中篇小說(shuō)對(duì)彝族地方性知識(shí)的發(fā)掘,突出地表現(xiàn)為對(duì)彝族獨(dú)特生存方式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知識(shí)的發(fā)掘上。一個(gè)民族或族群的生存方式與生產(chǎn)知識(shí)往往同他們的地域背景密切相關(guān)。正如德芒戎指出:“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包含著他們和地域基礎(chǔ)之間的一種必然的關(guān)系。”[4]呂翼體察到,在云南烏蒙山區(qū),千百年來(lái),面對(duì)山高水險(xiǎn)的生存環(huán)境,當(dāng)?shù)匾妥迦罕娨揽繜o(wú)畏的勇氣與無(wú)盡的智慧獲得了獨(dú)特而寶貴的生存技巧和知識(shí),也錘煉了強(qiáng)大的生存能力。《主動(dòng)失蹤》表明,在高山峻嶺中求生,在懸崖上定居,與毒蛇猛獸為鄰,與驚濤駭浪的金沙江打交道或通過(guò)溜索越過(guò)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等,是彝族生存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dāng)?shù)兀乩憝h(huán)境是那樣奇異而險(xiǎn)峻:“金沙江兩岸山高坡陡,河底水流湍急,奔騰洶涌”;烏蒙山“莽莽蒼蒼”,氣勢(shì)雄渾;許多村莊坐落在高峻的山腰或山頂上,成為險(xiǎn)要而與世隔絕的懸崖村落;通往村莊的路,常常是“惡狼”“野兔”和人共同通行的小徑。盡管生存環(huán)境如此惡劣,彝族人民卻視同尋常,世世代代在這里繁衍生息。尤其是面對(duì)金沙江的雄偉湍急與桀驁不馴,他們也能夠找到辦法對(duì)付它——驚心動(dòng)魄的溜索就是有效辦法之一。在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由于溜索用的繩索多由簡(jiǎn)陋的藤條做成,索斷人亡事件時(shí)有發(fā)生,但彝族人民并不會(huì)因?yàn)橛袪奚屯O逻^(guò)江的腳步。《竹筍出林》中的背篼村坐落在金沙江邊,“山高水深,路途艱險(xiǎn)”,滿山遍野長(zhǎng)著茂盛的竹林。在這種環(huán)境下,彝民背著用竹子編織的背篼運(yùn)送沉重的物資“爬坡上山”,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與必然選擇。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背篼是勞動(dòng)工具,也是離不開(kāi)的伙伴。而心靈手巧的麻達(dá)則用竹子編織成精美絕倫的生活用品,練出一種精湛的竹編技藝。
呂翼中篇小說(shuō)發(fā)掘?yàn)趺缮絽^(qū)地方性知識(shí)的重要著力點(diǎn),是開(kāi)掘彝族獨(dú)特的宗教文化。彝族是一個(gè)信奉原始宗教的民族,崇尚萬(wàn)物有靈論,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在他們的觀念中,“神靈被認(rèn)為影響或控制著物質(zhì)世界的現(xiàn)象和人的今生和來(lái)世的生活,并且認(rèn)為神靈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舉一動(dòng)都可以引起神靈高興或不悅:于是對(duì)它們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說(shuō)必不可免地導(dǎo)致對(duì)它們的實(shí)際崇拜或希望得到它們的憐憫”[5]。在呂翼看來(lái),正是萬(wàn)物有靈觀念形成了彝族獨(dú)特的原始宗教意識(shí)與對(duì)鬼神的虔誠(chéng)信仰,使他們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而且高度重視人死后靈魂的歸宿。《馬腹村的事》通過(guò)對(duì)“靈筒”的敘述,深刻挖掘彝族注重靈魂的獨(dú)特宗教信仰,充分凸顯其在脫貧攻堅(jiān)中的重要思想價(jià)值。馬腹村的彝族村民普遍有著獨(dú)特的民族民間宗教信仰,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保持對(duì)祖先的崇拜,銘記祖先的歷史功勛,而且高度重視靈魂的安居,重視人的精神生活,重視精神的皈依。比如,村里人都認(rèn)為,仙逝的人有三個(gè)靈魂:一魂歸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靈筒。而靈筒,正是祖先靈魂在家中的住地。馬腹村人認(rèn)為:“他們每家都有靈筒,靈筒里住有祖先的靈魂,只能供好,不能搬走。”靈筒的擺放位置,是老家的正堂屋。活著的成年男子,也有靈筒,但比供放祖先的靈筒小,外出時(shí)必須懸掛。可見(jiàn),這里的彝族村民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而且把靈筒當(dāng)做靈魂的寄居之地,并形成了他們獨(dú)特的居所觀念與重視精神安居或靈魂歸宿的獨(dú)特宗教觀念。在扶貧工作中,馬腹村彝民之所以不愿意整體搬遷,除了交通等問(wèn)題解決之后可更好生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樗麄冇兄⒅仂`魂歸宿的宗教信仰。他們認(rèn)為,一旦村子搬遷,祖先和活人的靈魂就失去安頓之所。正因?yàn)槿绱耍鲐毟刹繚闪衷谏钊胝{(diào)查與通盤考慮之后,決定尊重彝族村民的獨(dú)特宗教習(xí)俗,果斷地調(diào)整了扶貧方案。《逃亡的?貀》中的?貀,也包含著烏蒙山區(qū)彝族獨(dú)特的鬼神觀念或宗教信仰。馬腹村彝族人認(rèn)為,?貀是一種聚集百毒、禍害深重的惡鬼。人在社會(huì)中壞事做多了,就會(huì)遭致?貀纏身。作品中的彝族商人烏斯都大肆從烏蒙山區(qū)向大都市走私野生動(dòng)物,喪心病狂地殘害穿山甲,又為不法商人賈二哥非法集資充當(dāng)?shù)昧Ω蓪ⅲ斐舌l(xiāng)親們巨額血汗錢的虧損。因此,他回村后被村民當(dāng)成?貀纏身乃至被視作與?貀無(wú)異,他身為畢摩的父親吉薩老爹還親自為他驅(qū)鬼。
呂翼中篇小說(shuō)發(fā)掘地方性知識(shí)的另一側(cè)重點(diǎn),是發(fā)掘彝族獨(dú)特的倫理準(zhǔn)則。在所有民族的宗教中,往往滲透著濃厚的倫理觀念,包含著相應(yīng)的道德規(guī)訓(xùn),規(guī)定著人的道德義務(wù)與責(zé)任,隱含著揚(yáng)善懲惡的道德取向。呂翼深刻認(rèn)識(shí)到,彝族的道德準(zhǔn)則與彝族的宗教意識(sh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彝族宗教意識(shí)尤其是死亡意識(shí)里,滲透著嚴(yán)格而獨(dú)特的倫理價(jià)值體系,它們?cè)谝妥迳钪邪l(fā)揮出倫理誘導(dǎo)與道德規(guī)約的重要作用。《馬腹村的事》表明,彝族不僅高度重視人死后靈魂的安居,而且特別重視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修養(yǎng),提倡美德與善行,鄙棄惡行與罪惡,大力張揚(yáng)人的精神。在外出成年男子的靈筒的懸掛問(wèn)題上,彝族就有著嚴(yán)格的倫理準(zhǔn)則,凡認(rèn)為是“干了壞事,禍害百姓,罪惡累累的靈魂”,靈筒就不能進(jìn)正屋。在彝族部落戰(zhàn)爭(zhēng)史中,還形成一個(gè)獨(dú)特的“規(guī)矩”:“這里械斗不斷,死人是常事。但這里有個(gè)規(guī)矩,在戰(zhàn)場(chǎng)上犧牲,不能就說(shuō)你有多了不起,還得驗(yàn)傷口。刀槍穿過(guò)的孔,要是在正面,沒(méi)說(shuō)的,你是迎敵而上,家族都為你自豪,以你為英雄,隆重祭奠。傷口要是在身后,哪怕就是在腦勺子上,說(shuō)明你是逃兵,死得沒(méi)有價(jià)值。對(duì)不起,尸陳荒野,任狼撕狗啃,還要被吐口水詛咒。”[6]盡管彝族部落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帶有嚴(yán)重局限性與悲劇性,但這一檢驗(yàn)烈士傷口的“規(guī)矩”卻顯示出彝族獨(dú)特的道德指向性,它提倡勇士精神,反對(duì)臨陣脫逃與貪生怕死,形成了彝族人在戰(zhàn)爭(zhēng)中勇于沖鋒陷陣、恥當(dāng)逃兵的習(xí)俗。作為地方性知識(shí),這種推崇勇往直前的倫理價(jià)值在當(dāng)今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中保持持久的活力。村主任木惹因?yàn)楫?dāng)村主任待遇低、幾年得不到提拔等原因,意欲辭職去城里打工,在脫貧攻堅(jiān)關(guān)鍵時(shí)刻當(dāng)逃兵。村里最年長(zhǎng)老人半是指責(zé)半是提醒地給木惹講馬腹村人戰(zhàn)死驗(yàn)傷的傳統(tǒng),瞬間便激起木惹作為彝族男子的豪氣、膽氣和榮譽(yù)感,使他以全新的姿態(tài)投入到村里的脫貧工作當(dāng)中。《逃亡的?貀》也在詛咒惡鬼?貀的同時(shí),凸顯著馬腹村彝族正面的道德規(guī)約。在馬腹村,每家彝族人正堂屋的上方,都供有祖靈瑪都,而“祖靈面前,不可有污臟的行為,也不可有污臟的物體”。任何人不得違反,否則便會(huì)殃及全村。違反者輕則受全村人唾棄,重則被家族開(kāi)除。在外面做了壞事或品質(zhì)敗壞的人,回到家中不許進(jìn)正屋,否則就是褻瀆祖靈,罪不容赦。作為在外干過(guò)不少壞事的不肖子弟,烏斯都從大都市逃回馬腹村之后,受到了全村嚴(yán)厲的道德審判。他的父母不許他進(jìn)正屋,罰他睡豬圈,逼他懺悔與改邪歸正[7]。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書寫
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是一個(gè)多民族國(guó)家,各民族在歷史發(fā)展中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正如費(fèi)孝通先生所說(shuō),各民族歷史上相互往來(lái),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guān)系,最終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8]的政治格局。作為中國(guó)人,呂翼對(duì)祖國(guó)有著自覺(jué)的認(rèn)同意識(shí),深切體會(huì)到中華各民族一家親與彼此之間文化交融的關(guān)系的重要性。呂翼中篇小說(shuō)的另一重要敘事維度,是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書寫彝、漢民族融合,凸顯彝、漢高度自覺(jué)的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呂翼在“駿馬獎(jiǎng)”的獲獎(jiǎng)感言中談到中篇小說(shuō)姊妹篇《冤家的鞋子》與《馬嘶》:“寫動(dòng)物之痛,寫人物之苦,寫時(shí)代之變,寫民族之間的碰撞、糾結(jié)、交流與融合,寫世道人心的起落、輾轉(zhuǎn)與澀重,力圖表達(dá)一個(gè)底層負(fù)重者對(duì)世界的張望。其間既有個(gè)人的恩怨情仇,又有著更多的家國(guó)情懷。”[9]這些話可謂兩部小說(shuō)主題的注腳,體現(xiàn)出作者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高度自覺(jué)。
《冤家的鞋子》與《馬嘶》的主要人物相同,故事情節(jié)則前后承接與相互交叉。《冤家的鞋子》主要講述了彝族小伙烏鐵通過(guò)“搶親”,拆散了漢族情侶開(kāi)杏與胡笙,并由此產(chǎn)生諸多矛盾與仇恨的故事。在金沙江上游的金河兩岸,一邊是漢族的楊樹(shù)村,一邊是彝族的龍頭山。楊樹(shù)村十七八歲的美麗少女開(kāi)杏,與在縣城教書的同村青年胡笙真心戀愛(ài)。而龍頭山的烏鐵年方二十,出生于彝族土司世家。一天傍晚,騎著棗紅馬偶然來(lái)到楊樹(shù)村的烏鐵,遇到了在草堆上納鞋的開(kāi)杏,用“搶親”的方式強(qiáng)迫開(kāi)杏做了妻子。為躲避叔父的追殺,烏鐵帶著開(kāi)杏來(lái)到烏蒙城里的挑水巷,靠做小生意為生。他最想得到開(kāi)杏當(dāng)初在稻草堆上做的那雙鞋,開(kāi)杏卻寧死也不給。后來(lái),胡笙、烏鐵都走上抗日前線,烏鐵在戰(zhàn)爭(zhēng)中被炸斷雙腿。《馬嘶》以雙腿殘廢的烏鐵尋找“馬老表”(即棗紅馬)為線索,講述了烏鐵與胡笙在共同經(jīng)歷了保家衛(wèi)國(guó)、抵御外敵之后,化解仇恨,冰釋前嫌的結(jié)局。在烏鐵上前線后,開(kāi)貴終于在挑水巷找到了失蹤的妹妹開(kāi)杏,并找借口牽走了烏鐵的棗紅馬。對(duì)烏鐵來(lái)說(shuō),沒(méi)有“馬老表”的日子意味著精神的毀滅。直到楊樹(shù)村祭悼岳父時(shí),烏鐵才發(fā)現(xiàn)了病入膏肓的“馬老表”。最后,金枝陪著騎著棗紅馬的胡笙來(lái)到烏鐵家,烏鐵主動(dòng)讓開(kāi)杏取出當(dāng)初的那雙鞋給胡笙,開(kāi)杏親自給胡笙穿上,胡笙百感交集,淚如雨下。
通婚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種重要形式,不但可以促進(jìn)民族之間血緣的融合,而且可以推動(dòng)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與認(rèn)同。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族際通婚是民族民間文化交流融合過(guò)程中最直接、最徹底的一種形式,也是民族關(guān)系融洽和諧的直接反映和表現(xiàn)。”[10]呂翼中篇小說(shuō)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一個(gè)重要基石,是呈現(xiàn)民族通婚帶來(lái)的彝、漢之間的文化沖突與融合。《冤家的鞋子》與《馬嘶》的重要共同主題之一是通婚帶來(lái)的彝、漢民族之間的文化碰撞與融合。一方面,“搶親”造成了彝、漢文化的強(qiáng)烈碰撞。令烏鐵后悔不及的是他對(duì)開(kāi)杏的“搶親”。開(kāi)杏作為漢族純情少女,有著對(duì)美好愛(ài)情與幸福生活的追求,“搶親”讓她遭受了極大的羞辱,心理和情感備受致命打擊,同時(shí)也摧毀了胡笙對(duì)幸福愛(ài)情的夢(mèng)想。其間接后果是造成開(kāi)杏一家人骨肉離別,導(dǎo)致開(kāi)杏父親傷心而死,改變了開(kāi)杏一家人的命運(yùn)。正因?yàn)槿绱耍_(kāi)杏一家人對(duì)烏鐵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更重要的是,“搶親”背后折射出彝、漢文化的巨大差異與沖突。對(duì)烏鐵來(lái)說(shuō),“搶親”是金沙江一帶彝族“久有的習(xí)俗”,包含著人口繁衍高于一切的文化取向。而對(duì)開(kāi)杏來(lái)說(shuō),貞潔具有至高無(wú)上的倫理價(jià)值,比生命還要貴重。被“搶親”后,開(kāi)杏不斷地清洗身子,最想做的事就是尋死,她甚至不敢返回楊樹(shù)村——哪怕父親去世需要守孝,她也絕不回村,因?yàn)榛卮寰蛣?shì)必“羞辱祖先”。所以,即使烏鐵不停地向她賠禮與贖罪,她也不肯原諒他。另一方面,隨著在長(zhǎng)期交流過(guò)程中彝、漢之間增進(jìn)了解,消除了彼此的隔閡,帶來(lái)了彝、漢文化的不斷融合。由于對(duì)烏鐵心地、性格與身世不斷加深了解,開(kāi)杏對(duì)烏鐵的態(tài)度由仇恨、拒絕、冷淡逐漸變成關(guān)心、支持、贊許、接受與認(rèn)同。當(dāng)烏鐵要上前線打日本時(shí),開(kāi)杏第一次表示出對(duì)烏鐵的肯定,并主動(dòng)對(duì)烏鐵履行妻子的義務(wù)。烏鐵上戰(zhàn)場(chǎng)后,她把烏鐵心愛(ài)的棗紅馬養(yǎng)得又肥又壯。誤聞烏鐵陣亡后,她不顧個(gè)人安危回到龍頭山,幾乎傾盡家產(chǎn),以妻子名義為烏鐵舉行隆重的葬禮。烏鐵抗戰(zhàn)歸來(lái)之際,她一反常態(tài),第一時(shí)間給烏鐵拿出了他夢(mèng)寐以求的那雙鞋子。烏鐵勸她離婚嫁一個(gè)健全人,她卻對(duì)烏鐵不離不棄。至于烏鐵,他對(duì)開(kāi)杏始終真心相愛(ài)。他婚后對(duì)開(kāi)杏的疼愛(ài)、照顧、保護(hù)與贖罪,一直在慢慢融化開(kāi)杏心中仇恨的堅(jiān)冰。而烏鐵兩次到楊樹(shù)村都沒(méi)有遭到報(bào)復(fù),表明他的善意也逐漸被楊樹(shù)村漢族群眾所認(rèn)可與接納。
展示彝族對(duì)國(guó)家的認(rèn)同與忠誠(chéng),書寫彝、漢兩個(gè)民族自覺(jué)而強(qiáng)烈的愛(ài)國(guó)情懷,是呂翼中篇小說(shuō)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軸心。《冤家的鞋子》與《馬嘶》的另一重要主題,便是突出地表現(xiàn)彝族的國(guó)家認(rèn)同觀念與愛(ài)國(guó)情懷,表現(xiàn)彝、漢人民誓死保衛(wèi)祖國(guó)主權(quán)與領(lǐng)土安全、捍衛(wèi)民族尊嚴(yán)的集體無(wú)意識(shí)與愛(ài)國(guó)主義精神。烏鐵與胡笙雖然“身份”“民族”與“文化”不同,但“在大難來(lái)臨之時(shí),居然有著相同的理想和主張”,這一“理想和主張”便是“男兒就應(yīng)該血灑疆場(chǎng)”抗日救國(guó)。正因?yàn)槿绱耍瑸蹊F、胡笙才在臺(tái)兒莊戰(zhàn)役中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均不愧為民族英雄。烏鐵保家衛(wèi)國(guó)的大義,得到妻子開(kāi)杏、土司叔叔與金枝等彝漢民眾的廣泛認(rèn)同,如金枝偷偷地為棗紅馬喂食療傷,在人們要?dú)⑺浪劳鲮`時(shí),不惜以犧牲一頭豬的代價(jià)救下它,表達(dá)了對(duì)抗日英雄烏鐵的敬愛(ài)。在兩部作品中,像烏鐵這樣勇赴抗日疆場(chǎng)、舍身報(bào)國(guó)的彝族人十分普遍——不但包括龍?jiān)啤⒈R漢、張沖等著名彝族上層人士,而且還包括由云南四萬(wàn)各族子弟組成、由龍?jiān)坪捅R漢等彝族統(tǒng)帥與將領(lǐng)領(lǐng)導(dǎo)的抗日第六十軍中許許多多的彝族人。尤其是在第六十軍中,有包括眾多彝族子弟在內(nèi)的三萬(wàn)人,在臺(tái)兒莊戰(zhàn)役中為國(guó)捐軀。“在抗擊日軍的過(guò)程中,云南各族人民的命運(yùn)被緊緊的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生死相助、禍福相依,沖破了由于歷史、統(tǒng)治者壓榨等原因所造成的民族隔閡,結(jié)成了相互依存、生死與共的民族關(guān)系。”[11]彝人烏鐵與漢族情敵胡笙化解仇恨,在抗日戰(zhàn)場(chǎng)上結(jié)成生死兄弟,既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成果,也是各民族團(tuán)結(jié)一心、共同保家衛(wèi)國(guó)、抵御外來(lái)強(qiáng)敵的生動(dòng)象征。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中,呂翼中篇小說(shuō)還嚴(yán)厲地批判了置民族與國(guó)家大義于不顧的狹隘個(gè)人主義思想與貪生怕死的人生哲學(xué)。《馬嘶》中的開(kāi)貴便是個(gè)人主義與貪生怕死的典型代表。開(kāi)杏被搶后,開(kāi)貴尋妹不著,又逢縣政府組織青壯上前線抗日。在國(guó)家危難時(shí)刻,開(kāi)貴打起小算盤。先是故意在割谷時(shí)將右手指割去一截,繼而又在家中裝病,最后把當(dāng)兵的責(zé)任推卸給妹妹從前的男友胡笙。他恨烏鐵搶走妹妹,因?yàn)檫@毀掉了他想通過(guò)換親娶到金枝的夢(mèng)想,于是喪心病狂地役使乃至虐待被烏鐵視為生命的“馬老表”,完全沉溺于個(gè)人的私仇中不能自拔。最終,他的卑劣思想與行為,遭到了彝、漢民眾的一致唾棄。金枝拒絕嫁給開(kāi)貴,說(shuō)到底是因?yàn)樗皇且粋€(gè)愛(ài)國(guó)的熱血男兒——正如開(kāi)杏對(duì)開(kāi)貴說(shuō),如果開(kāi)貴上前線,金枝是會(huì)嫁給他的。因此,對(duì)于背叛中華民族共同體或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舉動(dòng),包括彝、漢在內(nèi)的各族人民一致表示譴責(zé)與不屑。
綜上,在呂翼中篇小說(shuō)中,彝族生活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構(gòu)成了生動(dòng)的交匯,不僅重新鍍亮了彝族傳統(tǒng)文化的光芒,而且自覺(jué)參與了時(shí)代主流文化的大合唱。這一書寫模式,有效地探索出基于民族地方社會(huì)歷史生活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路徑。
參考文獻(xiàn):
[1] ?李紹明.序[M]//姚光麟.西藏民族志.北京:中國(guó)藏學(xué)出版社,2006:2.
[2] ?吳道毅.烏蒙山區(qū)精準(zhǔn)扶貧敘事的華美樂(lè)章——評(píng)呂翼中篇小說(shuō)集《生為兄弟》[N].文藝報(bào),2021-07-05(7).
[3] ?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shí):闡釋人類學(xué)論文集[M].北京: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9.
[4] ?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xué)問(wèn)題[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9-10.
[5] ?愛(ài)德華·泰勒.原始文化:神話、哲學(xué)、宗教、語(yǔ)言、藝術(shù)和習(xí)俗發(fā)展之研究[M].連樹(sh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350.
[6] ?呂翼.馬腹村的事[J].民族文學(xué),2019(7):4-30.
[7] ?吳道毅.彝族文化視域下的抗疫敘事——讀呂翼中篇小說(shuō)《逃亡的?貀》[J].民族文學(xué),2020(12):26-28.
[8] ?費(fèi)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89:1.
[9] ?呂翼.獲獎(jiǎng)感言[N]//第十二屆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jiǎng)獲獎(jiǎng)感言.文藝報(bào),2020-09-25(4).
[10] ?蒲文成,王心岳.漢藏民族關(guān)系史[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264.
[11] ?王文光,龍曉燕,李曉斌.云南近現(xiàn)代民族發(fā)展史綱要[M].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9:269.
(責(zé)任編輯 ?丁 ?靜)

來(lái)源:中南民大學(xué)報(bào)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