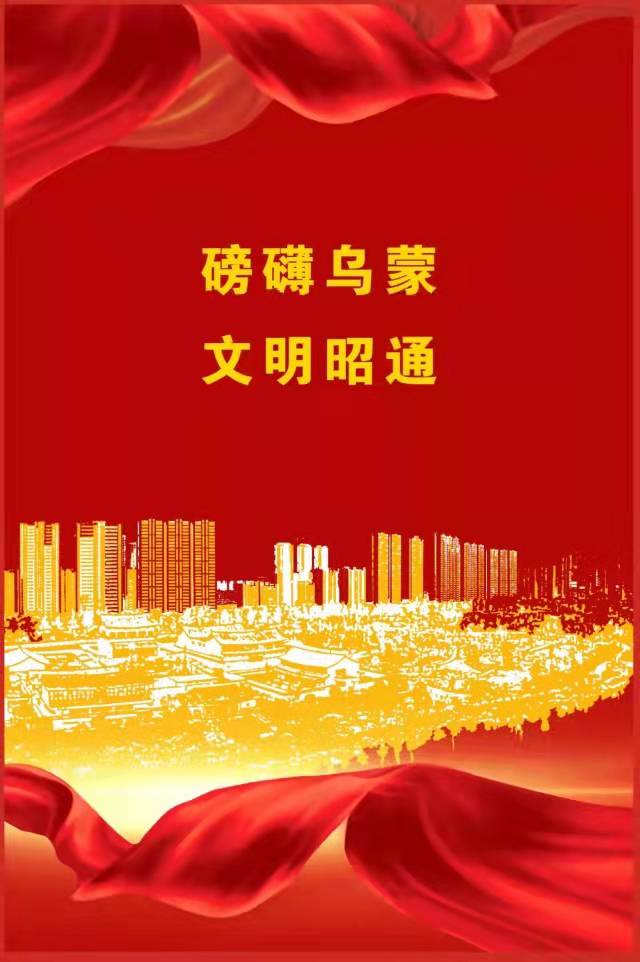2022-08-25 11:36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你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原本屬于哲學(xué)范疇的話題。但在遲子建老師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的右岸》里,也可以找到答案。
讀《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我頭腦里首先冒出的就是一個“地理方位”的指代,一個特定地方或者區(qū)域、一個將要發(fā)生故事的地方。相對于一條河流,朝著流向,那便有了左岸和右岸。額爾古納河的右岸,就是《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故事發(fā)生的地方,也是故事里“敖魯古雅部落的鄂溫克族”走不出的“故鄉(xiāng)”。
我讀《額爾古納河的右岸》,不僅僅因為這部作品獲得過“第七屆茅盾文學(xué)獎”,還有一個緣由是自己曾經(jīng)與額爾古納有過一段美好愉悅的記憶。那是6年前,我與幾個好友相約,到了北方,去了呼倫貝爾,穿過茫茫的大草原到達額爾古納,行走在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找尋草原的日落日出、探尋白樺林演繹的故事、傾聽草原牧歌的旋律和風(fēng)吹草低的韻律!記憶尤為深刻的是,額爾古納河、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恩和、室韋,以及曾經(jīng)發(fā)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我想在這部作品里,探尋作家筆下那一段歷史的滄桑、那一份故事的厚重;找尋自己那段“北上”的足跡,探尋額爾古納河右岸的秘密……由此而看,我讀作品就顯得輕松、愉悅,有情感和情調(diào),常常把自己置身其中,與作家同喜同悲,也便有了一份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的境界。
然而,當(dāng)我信心滿滿地讀《額爾古納河右岸》時,我才發(fā)現(xiàn)這部書是飽含民族元素、厚重得讓人憂傷和激動的作品,那些50多個人物的名字,還有他們之間那種錯綜復(fù)雜的血脈和人緣關(guān)系,獨特的民風(fēng)民俗,擬人化的雨、雪、馴鹿、獵鷹等,都是自己能否讀完這部書的一個“坎”。當(dāng)我想放棄又不忍放棄時,是那些優(yōu)美的描寫、詩意的表達,留住了我;是那些“平鋪直敘”又出人意料、讀得讓人心疼的故事情節(jié),留住了我;是“酋長的女人”懷揣故事的注腳,從久遠的歷史深處走進光鮮的現(xiàn)實詮釋的“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生存拷問和故土情結(jié),留住了我。讓人不得不佩服的是,遲子建不愧是把“根”深植于“自然”的“詩人”,是為社會代言、為歷史證言的“講述者”。
有人說,《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是一部生態(tài)題材的長篇巨著;有人說,《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是一部充滿傳奇色彩的“家族式”的囈語;還有人說,《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是一個民族家庭成員之間最坦誠的對話。作為文學(xué)大家的作品,對于作品本身我不敢妄言,而是以小學(xué)生般的虔誠,以求知者的忐忑,走進《額爾古納河右岸》去聆聽,以十二分的努力,去解讀“那位最后一名酋長的女人,訴說了一段怎樣感天動地的民族故事;那通靈薩滿的曠世大愛,如何為疲憊的人們點亮歸航的明燈”。追隨故事的脈絡(luò),我“從清晨到正午,再到黃昏”,讓我聽到的是“清脆的鹿鈴聲”,如何化作“越來越近的馴鹿”,如何化作“掉在地上的半個淡白的月亮”,如何“讓人落淚,讓人分不清天上人間”!
我在想,既然是讀一部作品,首先要讀懂的就應(yīng)該是標(biāo)題,弄清楚作者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要表達的內(nèi)涵。手捧墨香,“額爾古納河的右岸”言簡意賅、簡明扼要,但又高深莫測、一紙懸念,猶如一道美味佳肴,喚起人急不可耐的欲望。“額爾古納”為蒙古語,意為“捧呈、奉獻”之意,也有“折返”的意思。我去過的額爾古納河,位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東北部呼倫貝爾地區(qū),是黑龍江的正源,史稱“望建河”,為中俄界河。在《舊唐書》中稱之為望建河,在《蒙古秘史》中稱之為額爾古涅河,在《元史》中稱之為也里古納河,在《明史》中稱之為阿魯那么連,從清代開始稱之為額爾古納河。公元1689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確定額爾古納河為中俄界河。隋唐時期,額爾古納蒙兀室韋部落就在這里游牧狩獵,繁衍生息。當(dāng)海拉爾河從大興安嶺發(fā)源,流至呼倫貝爾草原西部扎賚諾爾北阿巴該圖附近時,突然轉(zhuǎn)向東北流去,千回百轉(zhuǎn),有如人“捧呈遞獻”之狀。額爾古納根河濕地,有“亞洲第一濕地”之稱,也是中國目前保持原狀態(tài)最完好、面積最大的濕地。
穿越大興安嶺所到的額爾古納、根河、恩和、室韋,就是《額爾古納河右岸》這部作品中故事的發(fā)生地。恩和是中國唯一的俄羅斯民族鄉(xiāng),居民多數(shù)是俄羅斯后裔;室韋,這個呼倫貝爾最北端、額爾古納河邊的一個小鎮(zhèn),依山傍水,鑲嵌在大興安嶺北麓,隔額爾古納河與俄羅斯小鎮(zhèn)奧洛契遙遙相望,是華俄后裔的聚居地。
任何一次創(chuàng)作,都不是憑空想象和臆造的。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創(chuàng)作于2005年,作品背后的故事本身就特別感人、留給人思考的東西太多。17年后,再讀這部作品,故事中成為歷史的現(xiàn)實更具有厚重感和“幽默感”。在大興安嶺西北麓、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原始森林中,曾經(jīng)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少數(shù)民族部落“敖魯古雅”,這里是森林與草原的界線,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大草原在這里交會,這里居住的鄂溫克人,是國內(nèi)唯一放牧馴鹿的地方,也是中國唯一的使鹿部落,也被稱為“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當(dāng)年,媒體報道“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人下山定居”的消息,引起社會廣泛關(guān)注。從2003年開始,鄂溫克人陸續(xù)從大山中遷出,搬進政府所建的定居點。但敖魯古雅使鹿部落里90多歲的女酋長卻舍不得大山和馴鹿,她說:“山下的房子是特別好,但馴鹿住的地方不好,不想下山。”當(dāng)許多人蜂擁到內(nèi)蒙古的根河市,見證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偉大的時刻”時,遲子建在為“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思考著,為“柳芭帶著才華走出森林,最終又滿心疲憊地辭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痛心著,一種憂郁和蒼涼感揮之不去,也觸動了遲子建“寫作鄂溫克族人這個民族的歷史”的創(chuàng)作靈感。
遲子建便到根河市追蹤馴鹿的足跡,找到了山上的獵民點,找到了筆下“女酋長”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媽媽,傾聽他們內(nèi)心的苦楚和哀愁,聽他們歌唱,聽他們述說,以一個記錄者的身份,以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女人”的口吻,滿懷憂傷和激情,用溫柔的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弱小民族頑強的抗?fàn)幒蛢?yōu)美的愛情,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以“力透紙背”之力講述一個少數(shù)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
《額爾古納河右岸》分為上部、中部、下部、尾聲四個部分,以清晨、正午、黃昏、夜晚的時序講述,樂感滿滿,滿卷散發(fā)著“田園交響曲”的韻味。正如作者所說,“清晨”單純清新、悠揚浪漫;“正午”沉靜舒緩、端莊雄渾;“黃昏”急風(fēng)暴雨、斑駁雜響;“尾聲”則是回歸初始、和諧安恬,是一首滿懷憧憬的小夜曲,或是一首鐘聲曠遠的歌曲。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字里行間,充盈著豐厚的生態(tài)意蘊,有對大自然的熱愛與敬畏,對生靈的關(guān)愛與體貼,對人的自然天性的禮贊與頌揚;有對人類所面臨的“生態(tài)困境”的憂慮與不安,有對宇宙“生態(tài)平衡秩序和諧”的祈盼與暢想。
《額爾古納河右岸》通篇彌漫著“萬物有靈”的觀點,以身邊的“自然”風(fēng)物賦予創(chuàng)作的支點和焦點,為“自然”構(gòu)建起與人平等對話的平臺,從而恢復(fù)“自然”的靈性主體地位,“自然萬物”被賦予了靈性,擁有了和人一樣的“生命尊嚴(yán)”。
馴鹿,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絕對是能與人類平等對話的靈物。還有達西的老鷹,在與主人的朝夕相處中培養(yǎng)的感情,足以讓它愿意為主人失去生命……這些富有靈性的“自然生命意象”與人和諧共處。
在這個不可多得、耐人尋味的好故事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故事。每個人都是純真的,充滿了“做自己”的勇氣;他們一見鐘情,卻又忠貞不渝;他們尖酸刻薄,卻又感恩圖報……他們有自己簡單的大原則,除此之外,皆是灑脫。
作者既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又是回憶的主體和故事的講述者。作品中,遲子建從“一個原始傳統(tǒng)部落民族與現(xiàn)代社會文明的沖撞”的矛盾糾葛,從“文學(xué)藝術(shù)”的視角,提出了一個讓人思考的關(guān)于“生存”的命題——人從“自然”中來,最終也都回到了“自然”中去。敖魯古雅的鄂溫克族,崇尚自然、逐水草山林而居,他們生活的那片被稱為“綠色寶庫”的土地被開發(fā)前,森林是茂密的,動物是繁多的,他們對于大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他們以及他們的馴鹿從來都是膜拜、親吻著森林的。故事的尾聲,最終落腳于“生態(tài)保護”這一主題,讓作品的現(xiàn)實意義更加強烈。
在“半個月亮”爬上山頭時,“老酋長”一整天的故事也就講完了。在作品的“尾聲”里,我看到的是“沒有路的時候,我們會迷路,路多了的時候,我們也會迷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到哪里去”。到此,額爾古納河“右岸是故鄉(xiāng)”的意象,也躍然紙上。
故事總會有結(jié)局,但民族和民族傳統(tǒng)文化是不能有尾聲的。額爾古納河的右岸,江河湖泊懷揣自然的磨礪和歲月的洗禮,最終或激浪滔滔、或洶涌澎湃、或靜靜游走,向東出發(fā),注入大海、回歸大洋,這是自然規(guī)律。東方,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乃河流的流向,那是一種方向,是點亮歸航的路標(biāo)!

作者 陳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