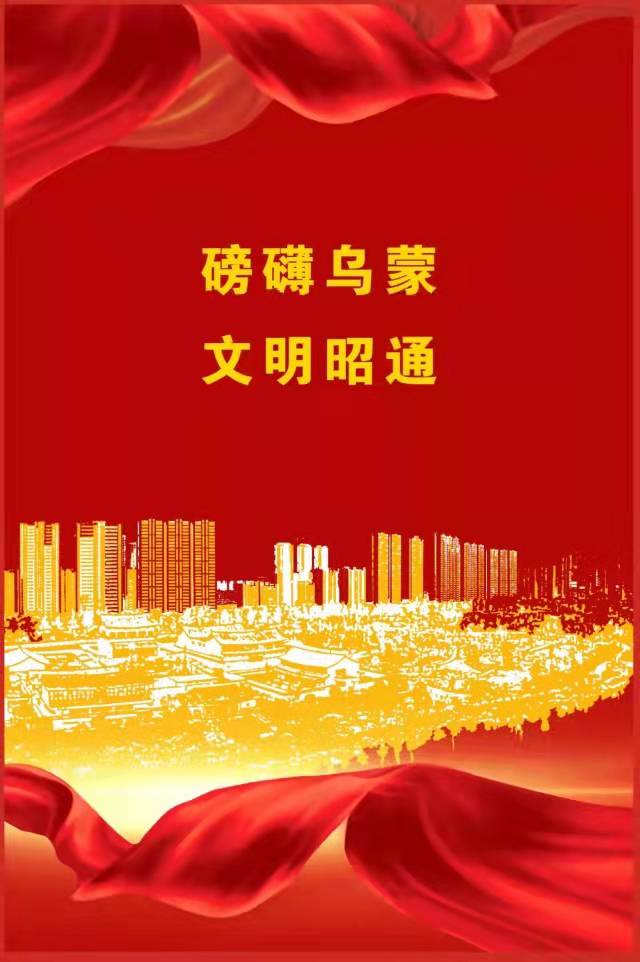2022-08-25 11:39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汽車(chē)順著烏蒙山山脈往下行駛到海拔僅600米左右的大峽谷里,峽谷底部窄得像刀口,公路要么是架在河面上的橋梁,要么是穿山越嶺的隧道。
這里已經(jīng)是昭通市鹽津縣地界,再有1個(gè)多小時(shí)的車(chē)程就到水富市,跨過(guò)水富大橋就是四川宜賓,金沙江一路奔忙流淌到宜賓,便改叫長(zhǎng)江了。
公路橋下面的河流,呈翠綠色,河兩邊山勢(shì)筆立陡峭,房屋全部建在河堤或陡峭的懸崖邊上,都是干欄式的吊腳樓,四根細(xì)細(xì)的柱子打在地下,像踩高蹺的細(xì)桿,支撐著離開(kāi)地面的房子。
迎面就是豆沙關(guān),刀劈斧削般陡峭的絕壁上高聳著兩扇巍峨的大門(mén),大門(mén)下邊流水潺潺。豆沙關(guān)又名石門(mén)關(guān),是秦漢以來(lái)中原通往云南的驛道之一,是古代“鎖滇扼蜀”的重要關(guān)隘,也是“南方絲綢之路”以及“茶馬古道”的要沖,故有“咽喉西蜀,鎖鑰南滇”之稱(chēng)。明末清初,特別是康雍乾盛世時(shí)期,豆沙關(guān)又成了“滇銅京運(yùn)”的重要驛道,十萬(wàn)馬幫,人背馬馱,源源不斷地把銅材運(yùn)往京都,供朝廷鑄幣之用。
眼下,這條驛道旁新修的高速公路,則是滇東北通向四川、通向祖國(guó)各地的重要交通干線。
豆沙關(guān)南邊絕壁距離地面約7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個(gè)長(zhǎng)條形的洞穴像一張被撕裂的嘴巴暴露在中央,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僰人懸棺。史料記載,僰人是夏朝遺民,商朝的戰(zhàn)俘,驍勇善戰(zhàn),在周武王伐紂時(shí)立下赫赫戰(zhàn)功,其首領(lǐng)被封為僰侯,在今四川宜賓建立僰侯國(guó)。明朝末年,由于戰(zhàn)亂,僰人紛紛遷往他鄉(xiāng),隱姓埋名,與其他民族融合,逐漸消失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長(zhǎng)河中。歷史上,豆沙關(guān)一帶是僰人聚居區(qū),其懸棺葬與盛行于西南地區(qū)的祖先崇拜密切相關(guān),被安置在洞穴中的棺槨現(xiàn)存11件,尚有9具遺骸,一定是這個(gè)民族的部落首領(lǐng)或名望極高的宗教人士。
用觀測(cè)鏡仔細(xì)觀察,洞穴中的棺槨原本是用木樁支撐,懸在半空的,但天長(zhǎng)日久,歲月侵蝕,一部分已經(jīng)垮塌,零亂地堆在一起。經(jīng)科學(xué)測(cè)定,這些棺槨放上去已經(jīng)600多年。陡峭的絕壁,上段至少還有300多米,兩邊少說(shuō)也各有幾百米,壁虎都難得爬上去,棺槨是怎么放上去的呢?學(xué)術(shù)界一直爭(zhēng)論不休,各種推測(cè),模擬試驗(yàn),結(jié)論僅只一家之言,無(wú)法印證,也說(shuō)服不了誰(shuí)。
因此,這一直是個(gè)謎。
豆沙關(guān)左邊的絕壁上,是秦漢時(shí)期開(kāi)鑿的五尺道,現(xiàn)存350多米。這條驛道是古代由川入滇,到緬甸、印度的重要通道,是云南東北方向通往中原的門(mén)戶(hù),修成后促進(jìn)了云南與中原各民族的融合,使云南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得到空前的發(fā)展。
拾級(jí)而上,步入古道,滿目蒼茫。幾天前下過(guò)雨,路還濕潤(rùn),歲月打磨的路面,坑坑洼洼,石頭裸露,泛著青光,泥土中拌有歷史的風(fēng)塵。馬蹄踏出的腳窩大大小小、深深淺淺,可以丈量出時(shí)光的深度。這是中國(guó)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道。懷著敬意回眸一望,古道就像一行墨跡淡去的文字,記載了2000多年的商旅遺事,以及云南文明發(fā)展的進(jìn)程。當(dāng)?shù)厝苏f(shuō)五尺道是中國(guó)古代交通博物館,一點(diǎn)不假。修筑時(shí)采用的“火燒水潑”技術(shù),就是烏蒙山腹地土著民采礦時(shí)普遍使用的技術(shù),這項(xiàng)技術(shù)來(lái)自大自然的啟發(fā),并在古代推廣,成為古代采礦、筑路、建筑的關(guān)鍵技術(shù)。
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大理國(guó)王異牟尋派三路使臣前往長(zhǎng)安,要求與唐重修于好,歸附大唐。于是唐德宗詔告西川節(jié)度使派崔佐時(shí)為代表來(lái)到大理,于貞元十年(公元794年)正月五日,在點(diǎn)蒼山神祠與異牟尋會(huì)盟,簽訂了《云南詔蒙異牟尋與中國(guó)誓文》,異牟尋發(fā)誓歸附漢唐,并訓(xùn)誡子孫,永無(wú)離貳。同年,鑒于異牟尋的誠(chéng)意,唐王派袁滋等人為專(zhuān)使前往大理,冊(cè)封異牟尋為南詔王,恢復(fù)一度中斷的隸屬關(guān)系。袁滋一行從長(zhǎng)安經(jīng)四川入滇,來(lái)到豆沙關(guān),袁滋便在五尺道旁的崖壁上刊刻一文,記述了這段史實(shí)。如今,這塊“袁滋摩崖石刻”成為歷史上中華民族大團(tuán)結(jié)的見(jiàn)證。
袁滋是唐代大書(shū)法家,史評(píng)其“工篆籀書(shū),雅有大法”,但他的手跡傳世極少,豆沙關(guān)石刻彌足珍貴,特別其篆書(shū)落款“袁滋題”三字,絕無(wú)僅有。
2000多年前,銅鈴悠悠,喚醒寂靜的山林百鳥(niǎo);馬嘶聲聲,將趕馬人的古道柔腸帶到遠(yuǎn)方。一路研讀腳下的古道,不難辨出歲月的滄桑,有趕馬人嘶啞的吆喝聲;有銅錠錚錚的碰撞聲;有草鞋踩在青石細(xì)微的摩擦聲;有馬蹄節(jié)奏鮮明的踢踏聲;有憂傷的歌謠在回蕩;有埋鍋造飯的裊裊炊煙飄出山林,在殘陽(yáng)輝映的天空中飄散……

作者 曹衛(wèi)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