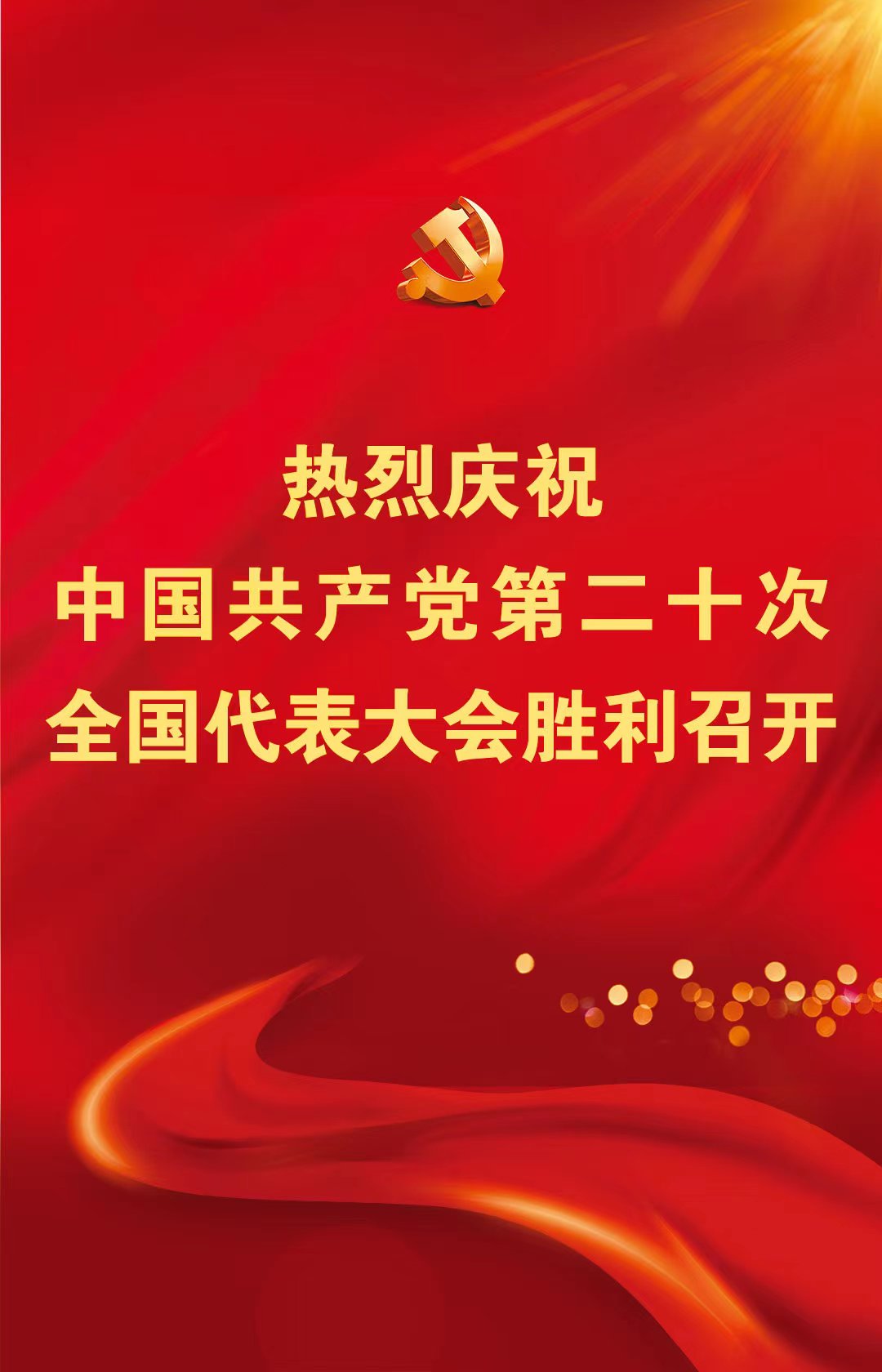2022-10-16 11:50 來源:云南發(fā)布

“大家好,我叫朱有勇,是中國工程院在云南省瀾滄縣蒿枝壩村的駐村科技特派員。瀾滄縣地處我國的西南邊陲,曾經(jīng)是深度的貧困地區(qū)。2015年我60歲,成為了脫貧攻堅(jiān)的一員,我把實(shí)驗(yàn)室搬到了田間地頭,幫助農(nóng)民把冬閑田種上了冬季馬鈴薯,推廣了林下中藥材,開辦了農(nóng)民技能培訓(xùn)班,讓農(nóng)民人人都有技能,家家都能有收成。我將繼續(xù)扎根在鄉(xiāng)村振興的第一線,為廣大農(nóng)民群眾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奮斗,謝謝大家。”

采訪活動(dòng)上《人民日?qǐng)?bào)》記者向朱有勇代表提問:
習(xí)近平總書記希望廣大科技工作者把論文書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yīng)用在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偉大事業(yè)中。那么您被稱為“土豆院士”,請(qǐng)問在科技助力鄉(xiāng)村振興的過程中,您和您的同事們都有哪些新的實(shí)踐呢? 二十大代表 中國工程院院士 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名譽(yù)校長(zhǎng) 朱有勇:
我駐的蒿枝壩村脫貧摘帽后,農(nóng)民口糧從粗糧換成了大米,但我們村沒有水田,只有旱地,稻米不能自給。針對(duì)這個(gè)問題,我們成功研發(fā)了水稻旱地種植新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了水稻上山,解決了山區(qū)農(nóng)民口糧問題。
水稻上山有兩個(gè)創(chuàng)新點(diǎn),第一個(gè)創(chuàng)新點(diǎn)是旱地水稻分蘗。自古水稻種在水田里,一棵秧苗變成一叢稻谷,這就是水稻分蘗。我們利用雜交優(yōu)勢(shì)選育了一系列新品種,這些新品種在旱地條件與水田一樣分蘗旺盛,解決了這個(gè)難點(diǎn)。第二個(gè)創(chuàng)新點(diǎn)是旱地除草。旱地雜草比水田多得多,我們根據(jù)雜草生長(zhǎng)發(fā)育規(guī)律,創(chuàng)建了雜草萌芽的封草技術(shù),解決了這個(gè)難點(diǎn)。
水稻上山得到廣大農(nóng)民群眾的歡迎,今年云南推廣了50萬畝,我們村推廣了405畝 ,最高畝產(chǎn)788公斤,最低634公斤,總產(chǎn)28萬公斤。全村277人,人均稻谷超過1000公斤,飯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水稻上山是我們學(xué)習(xí)總書記“解決吃飯問題,根本出路在科技”的具體實(shí)踐,我們將牢記總書記的囑托,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為鄉(xiāng)村振興做出更多的科技創(chuàng)新。

朱有勇
“時(shí)代楷模”
中國工程院院士
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名譽(yù)校長(zhǎng)
他下鄉(xiāng)扶貧、辦班教學(xué)
改善了一大批農(nóng)民的生活
他的故事讓無數(shù)人感動(dòng)
被人們親切地稱呼為
“農(nóng)民院士”
這位農(nóng)民院士接地氣、心系百姓
把個(gè)人榮辱與家國命運(yùn)、百姓福祉緊緊相連
他的很多話語都讓人心生敬佩
他說:
“我更愿意把全部的時(shí)間和精力
放到科研上。”
他說:
“歸根結(jié)底我就是一個(gè)會(huì)種莊稼的農(nóng)民,
所以農(nóng)民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他說:
“把科技論文寫在大地上,
要比寫在紙上艱難得多,
但是在我們心中、在拉祜族群眾心中,
科技成果漫山遍野飄香的分量,
比一紙論文要重要得多。”
……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gè)舊市一個(gè)農(nóng)村家庭。從小抓過魚、摸過蝦。1977年恢復(fù)高考,朱有勇抓住機(jī)會(huì),考取了云南農(nóng)大。從此,他跟農(nóng)業(yè)打了一輩子的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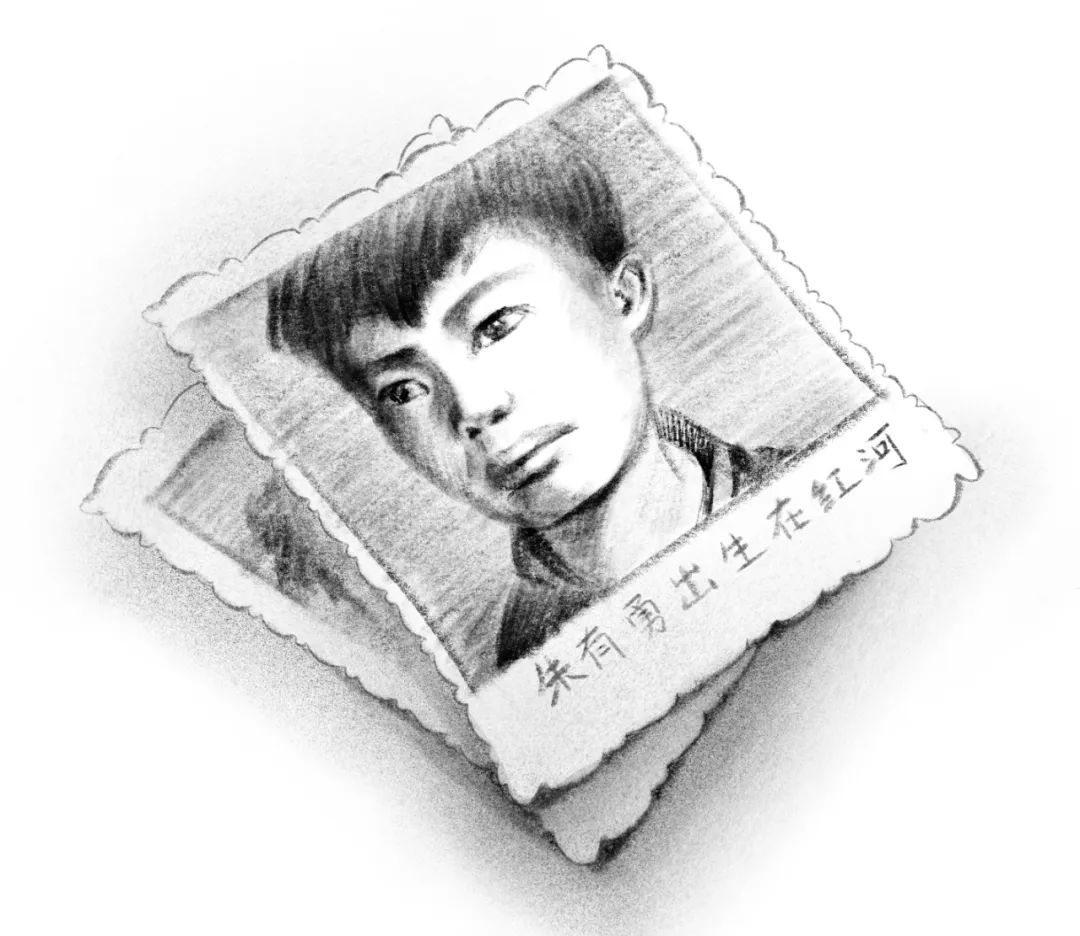
“團(tuán)結(jié)廣大群眾,為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服從祖國的需要,把自己的知識(shí)貢獻(xiàn)給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
為了這句誓言,1996年,朱有勇在悉尼大學(xué)完成了分子植物病理學(xué)有關(guān)項(xiàng)目研究,回到了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我能回到祖國,為自己的家鄉(xiāng)做事,比什么都有意義。”
為了這句誓言,2011年,剛剛當(dāng)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有勇向組織提出,希望繼續(xù)專心搞科研,不再擔(dān)任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校長(zhǎng)。
朱有勇長(zhǎng)期從事稻瘟病研究,他跑遍了云南省內(nèi)62個(gè)縣研究了2000多種水稻的基因抗性問題;2000年,朱有勇終于找到了水稻的品種搭配規(guī)律,為控制稻瘟病這一世界難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他的這一重大研究作為封面文章發(fā)表在了國際權(quán)威期刊《自然》上。
幾十年來,朱有勇團(tuán)隊(duì)研發(fā)的“遺傳多樣性控制水稻病害”技術(shù),在全國10省區(qū)市推廣6000多萬畝,榮獲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科研一等獎(jiǎng),他們研發(fā)的“物種多樣性控制作物病害”技術(shù),已在國內(nèi)外應(yīng)用于3億多畝旱地作物。這兩項(xiàng)技術(shù)都可以減少60%的農(nóng)藥使用,并能增產(chǎn)20%~30%。

2015年,已經(jīng)60歲的朱有勇接到了一個(gè)特殊的任務(wù):到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扶貧。朱有勇剛到這里時(shí),被眼前的一切震驚了,一進(jìn)村子就是一股臭氣,豬牛糞、肥料、茅草到處都是,水杯、炊具上落滿了蒼蠅,人住的是四處漏風(fēng)的籬笆房、茅草屋。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元。

朱有勇心里頓時(shí)壓著一股難以言表的痛,他對(duì)同行的博士生們說:“這里這么窮,怪我們這些人沒有深入下來,老百姓享受不到你的研究成果,作為院士,這就是失職!”
朱有勇一次次走進(jìn)田間地頭,到深山密林開展實(shí)地調(diào)研,然后在村里租了一塊地,帶著團(tuán)隊(duì)種起了土豆。三個(gè)多月過去,土豆采挖的時(shí)候,農(nóng)民從沒見過這么多、個(gè)頭兒這么大的土豆。
朱有勇跟老百姓算了一筆賬,每畝地平均3.1噸土豆,賣價(jià)3000元一噸,一畝地農(nóng)民收入9000多元,種一畝就能脫貧,種兩畝就能奔小康。
2017年,朱有勇在蒿枝壩村開起了土豆種植培訓(xùn)班,62歲的朱有勇常常俯下身、半蹲半跪在土地上手把手地教大家種冬季土豆。

老百姓的土豆豐收了,朱有勇并未停下腳步,只要有機(jī)會(huì),就不遺余力地“吆喝”起來。2018年3月,全國兩會(huì)的代表通道里,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朱有勇把老鄉(xiāng)種出來的土豆“吆喝”到了人民大會(huì)堂向全國媒體展示。

為了幫農(nóng)產(chǎn)品擴(kuò)大銷路,朱有勇而后又打造了農(nóng)村電子商務(wù)班,把這些農(nóng)產(chǎn)品賣出去。他甚至親自上陣展示瀾滄大土豆、炒土豆絲,幫助鄉(xiāng)親直播帶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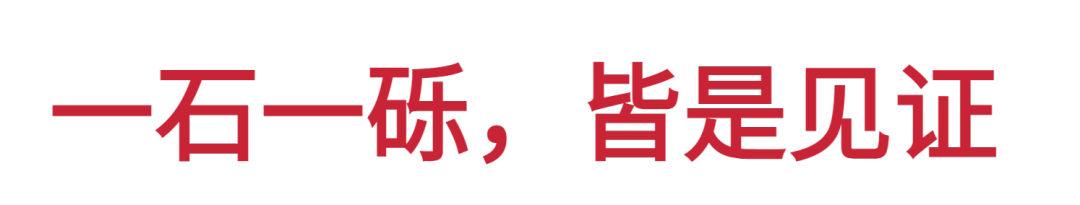
大山無言,一石一礫皆是見證。朱有勇腳步丈量的地方,就是一個(gè)村寨脫貧發(fā)展的希望。

除了種土豆,朱有勇和團(tuán)隊(duì)還開設(shè)了林下三七、冬早蔬菜、茶葉種植林業(yè)班、豬牛養(yǎng)殖班等前后共計(jì)24個(gè)技能班,培訓(xùn)了1500多名鄉(xiāng)土人才。這些學(xué)員回鄉(xiāng)后又發(fā)揮帶頭作用,變成一顆顆脫貧致富的“種子”灑遍瀾滄大地。
2020年11月,瀾滄縣正式實(shí)現(xiàn)“脫貧摘帽”。目前,當(dāng)?shù)匾褜?shí)現(xiàn)了從昔日深度貧困的“民族直過區(qū)”到“云南省科技扶貧示范縣”的跨越。
回顧這幾年的駐村幫扶,讓朱有勇最欣慰的就是通過技術(shù)技能培訓(xùn),在當(dāng)?shù)嘏囵B(yǎng)出了一大批鄉(xiāng)土人才。
“這幾年我們培訓(xùn)的農(nóng)民學(xué)員超過1500多人,之后其中90%靠自己脫了貧,50%帶領(lǐng)親友脫了貧,10%帶動(dòng)全村實(shí)現(xiàn)了脫貧。”朱有勇說,人的變化才是最大的希望。這幾年,當(dāng)?shù)厝罕娋珰馍裼辛撕艽蟾淖儯瑥脑瓉淼囊蕾嚒暗取⒖俊⒁保浆F(xiàn)在自力更生想進(jìn)步、求發(fā)展,大家都更加積極、更加自信了。“智力、志氣都扶起來了,以后的日子肯定會(huì)越來越好。”

潘彬瓊?繪

策劃:李茜?和曉
海報(bào)設(shè)計(jì):張艷萍
部分內(nèi)容綜合整理自央視新聞客戶端、云南日?qǐng)?bào)、科技日?qǐng)?bào)、時(shí)代楷模發(fā)布廳、人民日?qǐng)?bào)、新華網(wǎng)、人民網(wǎng)
編輯: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