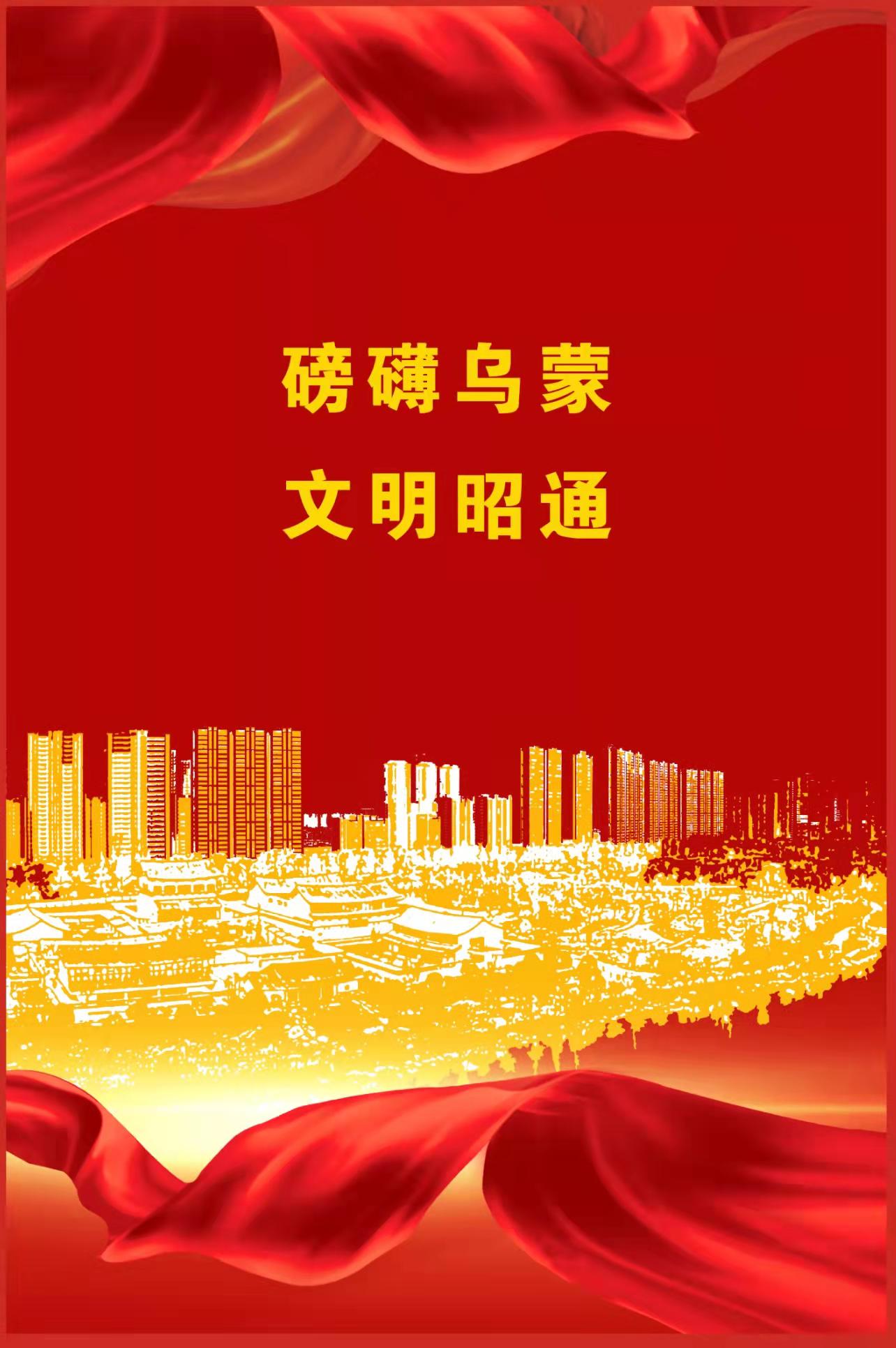2023-04-18 10:13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有人說,詩歌是以分行排列的結構方式對客觀存在與主觀存在的細微體現(xiàn),并與語言無限接近,坐落在“是”與“非”之間。詩歌給讀者的感受亦應是“似懂非懂”,留下回味和二次創(chuàng)作空間。對此,我基本上是贊同的。我想,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彝族詩人柏葉與他那貫穿于詩句間“似之而非也”(莊周《莊子·山木》)的詩作,也一定贊同此說法。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就是佐證。譬如,狗肉、羊肉看起來差不多,于是乎,有人就干起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然而,在關乎人格和立場問題上,應當做到是非之涇渭分明。如果是非顛倒、黑白不分、好壞無別、榮恥不辨,就會讓信仰迷失、公信倒塌、誠信缺失。
柏葉是個接地氣、貼近現(xiàn)實生活的詩人,知道如何思考現(xiàn)實生活中的“表面”與“實質”的兩極或多極,并藝術地隱喻于詩中。他十分看重各種不同尋常的“似之而非也”,力求在詩作中反映這種文文莫莫的,甚至讓他的詩作因對物(含“事”)們“似之而非也”的多維度審視,達到在趨于思辨性的某些細節(jié)或細處,發(fā)掘出微觀詩意中朦朦朧朧、隱隱約約的藝術效果。可以說,他的詩作,能排除一般抒情詩中較常見的“單一”思辨或思辨性的簡單敘述模式,自如地進入思想與情感所交織的、屬于語言藝術空間的“多維度”敘述模式。竊以為,最能凸顯他“多維度”敘述模式的詩,也是讓人心動的詩,要數(shù)他的《丟失的羊群》《老鷹巖》《猊江獨木橋》《貓頭鷹》與《啄木鳥》等。
《丟失的羊群》之“丟失”,可以說是一個牧羊人最不情愿看到的結果。為了這生機勃勃的羊群,辛辛苦苦的牧羊人花去了自己多少心血、存放了自己多少期待啊!作為詩人的柏葉,肯定深知“其中味”,不然的話,他不會讓“我”在不同敘述里有那么多的深情感知:
在一個大霧彌漫的正午/我把奶奶留給家族的羊群丟失了/咩咩的叫聲突然消失在眼前/山野里頓時一片沉寂
我不敢走進霧海里尋找/我不知道如果自己也丟失了/結果會怎么樣
我也不敢肯定/羊群是否真的丟失了/它們會不會跟著奶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我在草地上坐下來/閉上眼睛想那些熟悉的羊的模樣/想著想著,羊的模樣/越來越模糊/最后,不敢再想下去
我只能等待天慢慢黑下來/ 那時候,才能確定/奶奶留給家族的羊群/在我手里是否真的丟失了
“丟失”,在“我不知道如果自己也丟失了”的詩句中,成為一個富有雅致內涵的大詞。當然,柏葉也十分注重“我把奶奶留給家族的羊群丟失了”的失去或暫時遺失之原本義的口語化實錄。從詩中所顯示的情景來看,羊群的丟失與牧羊人的丟失之疑慮,其主因全在于“大霧彌漫”與一片“霧海”。這樣,牧羊人在他的慣常經(jīng)驗與自主意識里,就有了自己的一番考量。柏葉懂得運用這種發(fā)自內心深處的“考量”,為“我”的這種不敢肯定(“它們會不會跟著奶奶/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或不輕易否定(“最后,不敢再想下去”“奶奶留給家族的羊群/在我手里是否真的丟失了”)的比較式“考量”,注入了語言辯證中的張力與趣味。
寫詩的人在詩中十分看重關鍵詞的作用,擅長發(fā)揮詞語潛能、使詞語充滿活力的柏葉也一樣。他在詩中反復使用“丟失”一詞,與看不清眼前之物的大霧天相聯(lián)系,與牧羊人因看不見羊群而產(chǎn)生的一些確定與不確定之疑慮相聯(lián)系。在這種難以抑制的疑慮里,他把牧羊人內心的萬分焦急以及想早一點得知羊群之實情的無限期待,進行了一番心理上的情緒白描。他對“我”的一番情理相融的心理展示,可視為在精微的體驗中訴諸個人化的想象力。真的,柏葉這種源自自然狀態(tài)的情感敘述,是有力度的敘述,是凸顯異質性辯證經(jīng)驗的敘述。
在《丟失的羊群》里,柏葉沒有直截了當言及“似之而非也”的相關語義,只讓或“是”或“非”的語義深隱其中。然而,在《老鷹巖》一詩中,也就是面對著老鷹那“裸露在遍體鱗傷的巖石上”的巢穴,他除了送去那讓人尊敬的悲憫情懷,還在“似”與“非”的義理情趣的辯證里直接言及或深度思考:
千萬年無法風化的懸念
垂直而下
似醒非醒
似是而非
在“無法風化的懸念”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里,以意象的方式對老鷹的“巢穴”進行了多維度思忖。也就是說,詩中由“巢穴”到“懸念”實與虛的藝術描繪,再由“似醒非醒”擬人化到“似是而非”的辯證感知,悄悄地告訴我們這只老鷹的居所有其特別之處,彰顯了老鷹隨遇而安的極為強大的生命力。繼而,引出想象中的一切:
面對沉沉浮浮的歲月
巖石紋絲不動
只有鷹的影子
在想象之外的天空里
苦苦尋找著巖石盛開的鮮花
柏葉的想象力“在過去與現(xiàn)在時中任意穿越”(《打開“想象能力的匱乏”之枷鎖——讀柏葉的〈登云寺〉》)。而后,又讓其在“似之而非也”多角度的思辨中,靜靜地感悟著老鷹巖與“鷹的起飛”所留給人們“沉睡”與“醒來”、“逃亡”與“回歸”獨特的警醒或啟示。應該說,這是一個清醒者或是先知先覺者從適者生存的大自然健將——“老鷹”那里,帶給我們的一盤盤精神食糧:
該沉睡的已經(jīng)沉睡
該醒來的已經(jīng)醒來
該逃亡的已經(jīng)逃亡
該回歸的已經(jīng)回歸
老鷹巖,在神話的濃霧里
用異常堅硬的聲音
等待著鷹的起飛
無論是針對日常生活中的“丟失的羊群”與“至少我認為有落葉的地方/要比沒有落葉的地方/自然,干凈,熱鬧,瘋狂”(《落葉記》)、“我愿意變成一片花瓣/在春天透明的襯衣里/醉生夢死”(《一樹梨花》),還是考量容易被人們忽視的自然動物的“老鷹”與“除了孤芳自賞/它還學會了剔除一切悲傷”的《貓頭鷹》、“它要啄死所有害蟲/啄出一樹的綠/啄出一山的綠/啄出一個綠的世界”的《啄木鳥》,柏葉都試圖寫出最生動的部分、最值得思考的部分與最能入心或攝人心魂的部分,以期形成具有洞見的生命詩學。我覺得柏葉的這種既對外又對內或是同時面對“是”與“非”的詩學展示,成就了他那越來越靠近生命哲學的某種分析性、思辨性寫作。
柏葉一方面以記事的方式直接切入《丟失的羊群》的“大霧彌漫”的生活現(xiàn)場。另一方面,又以觀物的方式放射《老鷹巖》“似醒非醒”“似是而非”的那道詩性微光。除此之外,他還將對自然的思考帶進自然景觀:
我知道被時間遺忘的古井
永遠不會老去
老去的是模糊的日子
那些清澈透明的水
永遠溢流在山寨人心中
溢流在一個個風光無限好的景色里
這是《古井》中辯證地對待“時間”與“古井”的詩句。柏葉發(fā)現(xiàn)“被時間遺忘的古井”并沒有“老去”,而真正“老去”的是“時間”。只因“古井”的生命力全都集中體現(xiàn)于“溢流在山寨人心中”的那泓源源不絕的“清澈透明的水”。其意不言自明,“古井”的生命價值全在于自己的一份無私的奉獻。
盡管如此,柏葉亦不忘《古井》已“被歲月一口一口吸得干干凈凈”的現(xiàn)實。在我看來,他的這種帶著仰慕與悲憫的“不忘”,是我們值得關注的地方。大家十分清楚,自然世界里不僅僅是“古井”,還有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否還承受得住我身體的重量”的《猊江獨木橋》等自然存在物。《猊江獨木橋》之“是否”的運用,既讓作者與讀者的思悟處于“似之而非也”的辯證思考層面,又在不經(jīng)意之中將“猊江獨木橋”置于可觀看、可感受、可深悟的位置。那些可觀看的,是“每次經(jīng)過/我都會停下腳步”“每次經(jīng)過/我都會坐在旁邊”的“停下”與“坐在旁邊”;那些可感受的,是“考慮一下/它是否還承受得住我身體的重量”“想象一次/它曾經(jīng)擁有的桃花盛開的歷史”的“是否”與“曾經(jīng)”。而那些可深悟的,則與前面的“可觀”與“可感受”略有不同。柏葉將“可深悟的”的內涵,悄悄地分為實則虛之的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直接面對自然世界客觀事物中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實”);第二個層面,是間接面對人生或人世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虛”)。在面對自然時:“江還是那條江/岸還是那個岸/改變的是流水的聲音/改變的是行走的習慣”。而在面對人生或人世時,更多的是柏葉辯證式的多維度之審視、窮思與細味:
有人走過千山萬水
一輩子走不出故鄉(xiāng)的獨木橋
有人可以呼風喚雨
一生一世看不清故鄉(xiāng)的模樣……

作者 陳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