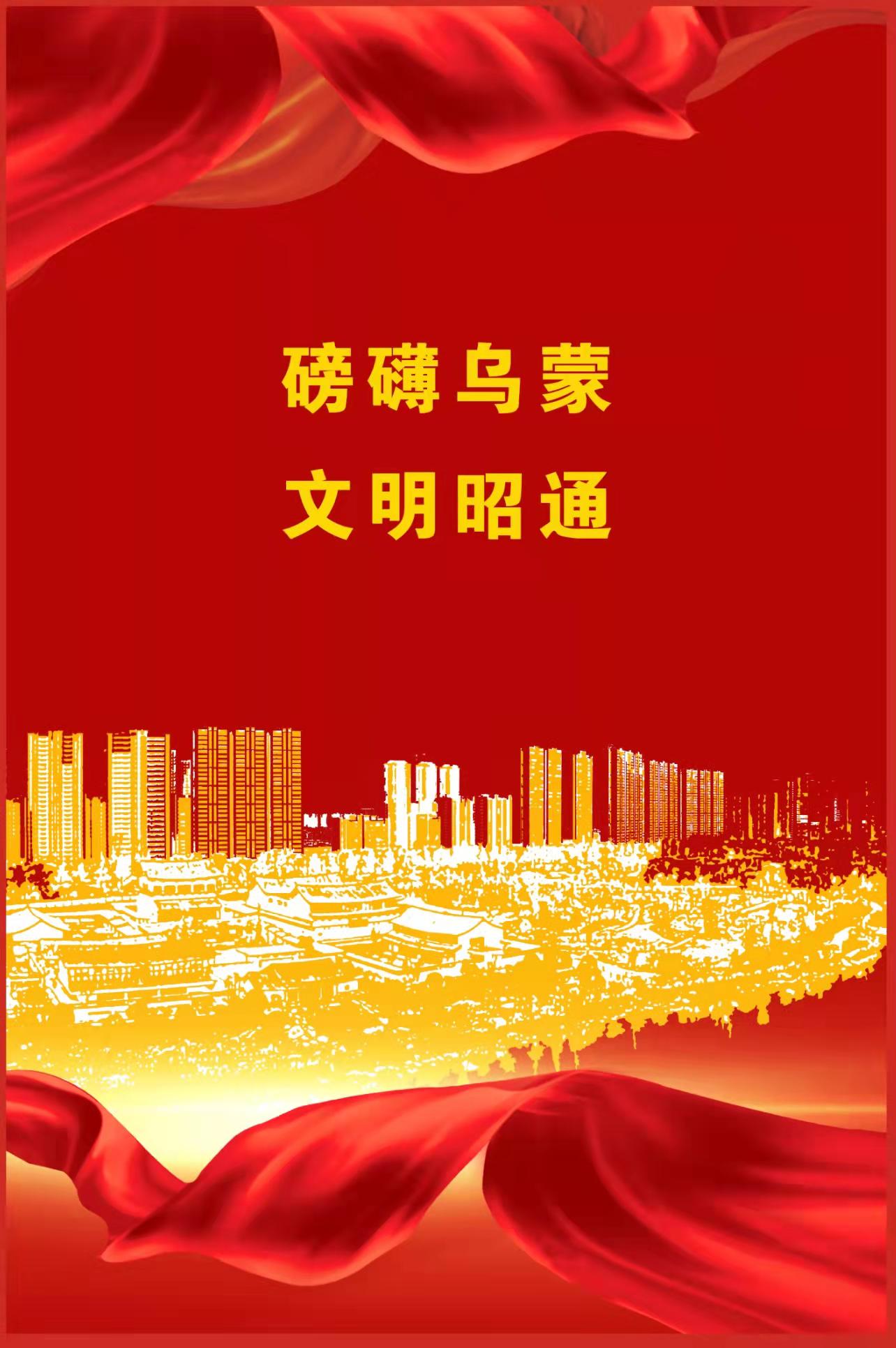2023-05-09 10:25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北 雁原名王燦鑫。1982年生,現(xiàn)居云南大理。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出版長篇作品3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散文選刊》《作品與爭鳴》《延河》《滇池》《陽光》《中國鐵路文藝》《邊疆文學》《大地文學》《短篇小說》等報刊發(fā)表小說、散文170余萬字,曾獲第九屆云南文學獎藝術獎(文學類)。
小 果
小果村位于大理白族自洱源縣城至茈碧老線3公里處,村民依壩子西緣山腳而居。現(xiàn)今,50余戶200多人居住在一塊向陽的坡地上,從村頭至村尾,延伸出大約400米。據(jù)村子背后的墳山墓志可知,村民大都為明洪武年間自南京應天府遷居而來。漢族白族雜居,民風淳厚,古樹彌天,整個村落似一片小森林,終年翠團環(huán)抱。
村民多以種植業(yè)為主,輔以林果和農(nóng)牧。村落的得名,乃是因為村民房前屋后或村后的坡地林地之中,均種有大量的木瓜、花紅、蘋果、石榴、桃子、李子、梅子、杏子、柿子、梨、無花果、香櫞、佛手、柑橘,還有核桃、板栗、花椒、山楂,一年四季彌散著濃濃的果香。
時光如逝,小果村早已成了一個虛無的名字。除了隨處可見的木瓜和庭院內(nèi)外尚存的花紅、梅果,幾十年前那么多種類的果樹,似乎在一夜之間就不見了蹤影。當然,類似這樣虛無的村名數(shù)不勝數(shù),比如大樹莊沒有大樹,石橋村沒有石橋,桃花村沒有桃樹,打鐵營里找不出一戶鐵匠,趕羊澗村沒有了趕羊的小道,換之而來的卻是一條條高速公路……
小果村村民之所以為這個村名而自豪,那是因為村落之中還留有四五株樹齡超過八九百年的參天巨樹,學名黃連木,當?shù)厝朔Q之為大漆樹。每到春天,樹枝上便結(jié)出一串串小果子似的花蕾,村里一首民歌開頭一句便這樣唱道:“千年大樹結(jié)小果。”因此,村民以為村落的得名,乃是因為這幾株黃連木,以為村落的歷史和這幾株古樹一樣悠久。
在小果村后的半坡之中,還有一個叫“花果山”的果園,至今還留有大量的老梨樹、老核桃樹和老柿子樹,芳草萋萋、樹木陰翳,仿若隔世桃源。據(jù)說“花果山”自古即有之,村民出工出勞,種藥養(yǎng)茶,培育大量果木,每年所得收入充入公益基金,用于修橋造路、興學辦校等。位于滇西群山腹地的洱源縣,屬于北亞熱帶高原季風氣候,冬春偏寒少雨,每年大地春回之時,村后的花果山一派勃勃生機,時有游人前來露營觀光。記得有一次,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騎著自行車,提著錄音機戴著旅游帽,來到村口,也不下車,開口便向石崗上一位納涼的老頭問路:“哎,‘花果山’的路怎么走?”老頭也不回答,側(cè)身往后一指,幾個學生便順著老頭的指引穿過村莊,沿著村后經(jīng)常不見陽光的牛馬道上山,泥濘路滑,行至難處,只得把自行車扛在肩上。感覺“花果山”近在眼前,卻總到不了。無路可走之時,才想起問路時有些趾高氣揚,只得有禮有節(jié)地向地里耕種的農(nóng)人問路,才知道他們要去的是隔得不遠、交通方便的龍泉公園。如此一番折騰,外人方才知道小果村后山路何等艱險,村民生計何等艱辛。
南溝邊
村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除了一個被巨樹掩映的古舊村盤外,小果村還有大量的山地、林地和耕地,不僅豐富了村落的內(nèi)涵,還成為小果村物產(chǎn)豐饒的象征。
小果村的耕地分為旱地和水田。旱地分布在村落背后的坡頭箐底,不知多少年前,就被辛勤的村民修整為階梯狀,一直伸延到入云的山間。因水利不暢,村民多種以果木,同時種上不需要時時灌水的作物,如洋芋、芋頭、玉米、小麥、大蒜、油菜、百合、蠶豆、黃豆、豌豆等。水田主要分布在平坦的壩子里。古時,往往以一塊田地是否可以種植水稻作為衡量土地價值的標準,小果村也是這樣。幾塊為數(shù)不多的水田,分布在南溝邊、小溝哈(小溝旁邊)、水田壩、四田壩,是村落最重要的糧倉。
在這幾塊水田地中,只有南溝邊是平平整整、方方正正的。南溝邊面積寬廣,從古至今都是小果村最核心的耕作地。南溝邊面積大約300畝,因為水利和交通的優(yōu)勢,糧食的出產(chǎn)量大約占全村產(chǎn)量的六成以上。考究這塊耕地的得名,興許與它的地理位置有關。南溝邊夾在村子和往東大約500米的下小果之間,一條河溝從地塊南緣流過,一直流經(jīng)下小果村南頭,成了村子與南邊村落的界線,同時也成就了這個地名。
南溝邊又被稱為土山神。那是因為有一座小土丘兀立于這片耕地的西北邊緣,整塊耕地極為平整,中間地帶略有些低陷,如點將臺一般格外醒目,人們便稱之為土山神。小土丘邊有兩戶雜姓人家,據(jù)說是早年政府安置的外地人。他們初來小果村時連地都沒有,于是,各家各戶從田頭地角分出一小塊地,作為他們的口糧田。在南溝邊壩子,每家每戶的地都是大田,人口多的一塊田差不多有兩三畝。雜姓人家的田卻如同拼圖一般,細細碎碎,沿著水溝排列。很多年后,當我知道這些淵源,著實為村民當年的慷慨感嘆,因為小果村的耕地并非多得種不完。
我家的兩塊水田就在土山神邊。水田是我們最重要的依靠。一年四季,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把大量的時間“泡”在這里。從四五月份把秧苗栽入地里開始,接著要補水、修埂、薅苗、割稗、趕雀、追肥、噴藥、割谷、種豆、拔草、收豆、犁地、耙地、放水、復栽……然而,小時候我卻十分害怕從土山神邊路過。據(jù)說,有一家一個和我同齡的男孩夭折了,沒有地安葬,就被大人連夜葬在了土山神中。后來我向他的兩個哥哥問過這事,他倆哈哈一笑,說這怎么可能?葬這里不被野狗給刨了?早被大人葬到山后的義地里去了。說完還怕我不相信,兄弟倆掄起鋤頭,三下五除二就把土山神給掘平了,果然沒有葬過人的跡象。
我一直覺得,土山神同樣也是小果村和諧的象征。人們卻將這塊地改成了另外一個名字,可能是因為順著南溝修了一條直通到縣城的機耕路,而且也習慣了南溝邊這個稱謂。
寺
現(xiàn)今的小果村僅留下一座寺廟,即村子正中古樹彌蓋下的華嚴庵。庵內(nèi)正西的大殿里塑有釋迦牟尼、彌勒佛和觀音之像,旁邊的耳房里則有土地和財神。幾十年來,門口的對聯(lián)幾乎全是那樣:山神保佑山中客,土地扶持土上人。橫批:有求必應。北房正中供奉的是手執(zhí)長卷的孔子,慈眉善目,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每年孔子誕辰,村民都要在這里集會共祭孔子。包括其他各個節(jié)慶,這里絕對是村子里最神圣的地方,蓮池會的老人要在這里誦經(jīng)祈福,村民們要在這里磕頭求安。香煙環(huán)繞,鐘磬和響,整齊的誦經(jīng)聲如同唱詩一般,讓古寺極富古韻。
在小果村,寺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位詞。因為村落四周,就有許多地塊因寺得名。比如“寺門口”“寺后頭”,還比如村南的一塊梯地被稱作“寺南”,村子北上角的一塊坡地被稱作“寺北”,寺北斜上方又有一塊坡地被稱作“上寺門口”。村里的老人說,早年村子上頭的確還有一座寺廟叫上寺,不知什么時候毀壞了,但幾個代表方位和地名的農(nóng)耕地卻因此保留了下來。
歷數(shù)小果的耕地或林地,有的從名字上就能確定地的用途。比如水田壩、秧田壩、竹園、花果山、蘋果園、桃子園,但還有許多地塊指示不明,如寺南、寺北、上寺門口等,村民們有時將其用作秧田,有時作為旱地,但更多的時候,是將之作為蔬菜地使用。
因幾塊地就在村落附近,很多人的勞動都是從這些地塊開始的。小時候,我常會跟著姐姐們,挎上小籃子到寺北給豬牛割一籃草,或到寺南自家地里代父母澆地。春荒二三月,小果村也常陷入水荒,大半夜里挖不到水,地總是澆不透,人只能站在埂上干著急,我也曾悄悄把水源上游幾塊秧田的水壩掘開,讓積水流到我家地里。但這樣的“勾當”很快就被人發(fā)現(xiàn)了,秧田主人指著我家地里的浮萍指桑罵槐,害得我很長時間不敢從他家門口經(jīng)過。
更多的時候,我會跟村里的同齡人一樣,和父母一起伏在地里精耕細作。初夏的蒜地板結(jié),固如堅冰,我們找來水源,澆在上面,趁著有濕氣用條鋤挖開泥土,再將蒜苗一棵一棵拔出來。但水不能澆得太透,否則人在蒜地里就如踩爛泥一般深陷其中;若是澆不透,蒜又拔不出來。在泥土里長了一季的蒜瓣,像極了這塊土地上人的脾性:寧為“蒜”碎,不為瓦全。縱使你使出吃奶的力氣,把蒜葉拔脫,把蒜稈拔斷,也休想將蒜拔出來。最終只能拿來條鋤,使足力氣再刨個坑,才能將早已碎散的蒜瓣刨出地面。蒜碎了,就沒有了賣相,可不挖出來,卻又影響下一季的耕作,因為它依舊會在地里生長,奪走玉米的養(yǎng)分。
有時,我也會跟著父親在玉米地里培土。烈日當空,人們頭昏眼花,汗流浹背,腰酸背痛,直不起身。待到晚間休息時,臉上臂上手上脖子上,全是玉米葉劃出的細口,又辣又痛,渾身上下就像被人毒打了一頓似的。冬日嚴寒到來,我還會陪著父母到山箐里挖百合。那些常年少陽光的箐地,山風一陣緊接一陣,從山頭急疾而過,吹散的泥灰就如同雨點一般往人身上澆,有時讓人睜不開眼睛,有時讓人滿身都是灰。大人掄起鋤頭挖開了百合墑,我們就跟著彎下腰如同捉蟲一般,把百合一粒一粒“捉”進籮子里,順手抹掉泥巴掐掉根須,按大小歸類。一天下來,我們用10個指頭將一畦泥土一把一把翻碎,身子常常如深陷冰窖一般。
我確信,小果村背后一塊塊魚鱗狀的大小梯地,珍藏著一代代村民最辛勤的汗水,同樣珍藏著歷代村民對土地的忠誠和熱愛。
牛滾塘
牛滾塘位于小果村后山之中。據(jù)說幾十年前,這里是一片高山草甸,綠樹成蔭,飄嵐走霧,水草豐美,有大量的牛群出沒,牛滾塘因此得名。
一年到頭,村民們在這附近的山地摞松毛、撿松球、砍松柴、采松脂、割茅草、拾菌子、挖草藥。從牛滾塘發(fā)源的一溪箐水,流經(jīng)汽早澗、汽早坡、回下登、竹園、秧田壩,最終從寺南流過,沿途滋青吞綠,與花果山背后的龍水,成為村落最重要的兩大灌溉水源。
幾十年前,村民們竟將牛滾塘附近幾個山頭的大樹小樹砍伐一空,甚至連樹根都一塊兒刨走,妄圖把梯地一直修到與天齊平的山巔。令人惋惜的是,牛滾塘消失不見了。從此,村民們砍柴拾菌得多走十幾里路,到達后山背后的石照壁,甚至是更遠的羅坪山腹地。讓老輩人至今談之色變的是,有一個夜晚突降大雨,村落后山發(fā)起了大水,差點將整個村子淹沒。
植樹造林很快成了村落的一大主題。幾十年后,小果村后山又被蔥郁的松樹覆蓋,人們又可以在其間牧牛采菌了,但牛滾塘和水塘沿途的好幾口井,卻成了一個永久的傳說。
阿榮坡坡
小果村與后山之間,有一條回環(huán)的山路,沿途連通了秧田壩、竹園、回下登、汽早澗、汽早坡、赤登間、花果山等一系列坡地、箐地和山地,后山卻不是終點,因為后山的背后是石照壁和石門檻,過了石照壁和石門檻,路繼續(xù)向前伸延,最終消失在了起伏連綿的羅坪山中。
如果把村落當作起點,那么從出村至秧田壩一段,還較為平緩。但百米過后,前面便出現(xiàn)了一個急坡,村民稱之為阿榮坡坡。水從坡上往下流,狹窄的坡路就在溝邊伸延。路是土路,土是黏土,下雨的時候,路就變得異常濕滑,牛走到這里,差不多都不用走路,只需定定地站著,便能順著坡穩(wěn)穩(wěn)地滑下來。
這是小果村里為數(shù)不多的以人命名的地點。大人們說,阿榮是村里的一位老人,已經(jīng)去世50多年了。據(jù)說,早年政府鼓勵村民墾荒造田,多打糧食,但別人墾的荒都成了私田,種上幾蓬刺籬笆,就把上百畝的山地、坡地據(jù)為己有。有的種上樹,有的種了糧食,有的蓋上房子成為自己和子孫后代的家園,還有的什么都不種,就讓一大塊地荒著,只有阿榮坡坡成了村里的公路。古往今來,村子里老老少少逝去那么多人,只有阿榮至今還念在人們嘴里。
花石坡
花石坡位于牛滾塘后山,兩者相距大約500米。遠遠看去,只見一面樹木蔥郁的山坡上,有一條蜿蜒的小路如同飄帶系在山腰。小路上面,有一塊碩大的花白石頭,如同美玉一般被銜在山腹之中,異常奪目,這就是小果村地界的終點。
對于小果村而言,花石坡還有一個美妙的傳說。據(jù)村里的老人講,早年羅坪山中常有山匪出沒,搶劫山下的村莊,弄得生靈涂炭、民不聊生。一天,一幫匪徒?jīng)Q定搶劫山下的小果村,哪知剛行至山中的花石坡,便遭遇了一場瓢潑大雨。電閃雷鳴、大霧彌漫,連面對面都看不清誰是誰,匪徒只能躲進山坡中避雨。好不容易大雨停了,大隊人馬一路馬不停蹄,浩浩蕩蕩殺入小果村中,卻發(fā)現(xiàn)整個村子一片死寂,家家關門閉戶,沒有一點生機。匪徒心中疑惑,撞開幾戶人家,卻發(fā)現(xiàn)房子里空空的,連谷倉都被打掃得干干凈凈。最終人困馬乏,匪徒只能悻悻離開。半年后,匪徒舊計復施,半山之中又遇到暴雨,同樣只剩一個空村。
匪首心中疑惑,便令手下化裝后潛入村中暗中偵察。每當匪徒行至花石坡,羅坪山瞬間烏云密布,電閃雷鳴,傾盆大雨倏然而至。來勢洶洶的土匪只得躲進密密匝匝的松林中避雨,銳氣大挫。而村民們收拾好糧食細軟,順著白光往東山腳跑去。
村莊屢屢得救,于是村民們甚至想籌資起工,建一座石神廟。后來,花石玉被匪徒破壞了,但他們?nèi)匀粺o法在村里作惡。因為小果村中還有一位“保護神”,按輩分我還得稱他一聲大爺。他長得牛高馬大、滿臉暗瘡、胡子拉碴、面色黧黑,遠遠看去,儼然一頭直立行走的黑熊。大爺天生神力,早年上山打柴,別人每天一個來回都夠嗆,他卻可以每天兩三個來回。天色破曉,他就翻身起床,胡亂吃點飯食,就帶上繩索刀具上山了。連綿起伏的羅坪山腹里,到處是郁郁蔥蔥的山竹。村民們上山大多是為了砍山竹,也有的是為了砍柴。大爺動作麻利、刀快如風,刀子到處,山竹、櫟木就被他一茬茬放倒,眨眼工夫,便將兩挑山竹或櫟柴綁扎好,然后挑上就從山腹中那狹長的山道上晃蕩下來,如同撲騰的山風一般輕快,眨眼走出兩三里路。別人歇息他不歇息,放下?lián)佑众s山路來接第二挑。如是幾番倒騰,卻總會趕在別人前面到家。
聽說山匪洗劫了村落,正在南溝邊地里干活的大爺拿起手中砍刀,一路狂追,終于在花石坡追上了他們,20多個殺人不眨眼的匪徒,被他全部撂倒在地。匪徒趕緊拾起刀槍一溜煙返回山里,再不敢進犯小果村。但他們卻不甘心,10多年后,大爺變老了,匪徒又再次舉兵進犯,一進村莊便四處搶劫,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村子里娘哭兒泣,老老少少如鳥獸散。正當匪徒猖狂施暴之時,忽有人報告匪首,稱村頭一個庭院內(nèi),居然有一個老頭端坐在火塘邊,氣定神閑地烤火喝茶。匪首立即帶上匪徒來到庭院,遠遠就能看清那就是當年把他們?nèi)苛痰乖诘氐膲褲h。老頭兩眼里透出一種怡然的神情,像是對他們的嘲弄和輕蔑。是可忍,孰不可忍!匪首氣急敗壞,快步上前,舉起利刃就朝大爺?shù)哪X門砍了下來,大爺也不躲閃,伸出一只老手輕輕一揚,一團紅霧便在天空中散開。匪首就覺得眼睛里鼻子里嘴巴里頓時一陣熱辣,難受極了,連續(xù)打了十幾個噴嚏,滿臉涕淚橫流,接著手上又被人砍了一刀,一把利刃瞬間落地。
原來大爺早在火塘邊準備了一罐辣椒面和一把鋒利的柴刀,當匪首舉刀砍來,他利索地把那罐辣椒面往他臉上撒去,又在他手上砍了一刀。匪首睜不開眼睛,鼻里嘴里和眼里的辣嗆遠比手上挨的一刀難受,全然不顧自己一條命已握在大爺手里。
大爺卻對他說:“我不殺你!要殺你,10年前花石坡一戰(zhàn),你已經(jīng)是我的刀下之鬼。如今四下兵荒馬亂,當兵做匪種莊稼,全是苦命人,告訴你的手下,不要殺人,要東西你們拿走便是!”
匪首羞愧難當,正當他轉(zhuǎn)身離開之際,卻聽得背后一聲槍響,一個小頭目開槍把大爺打死了。匪首惱怒異常,罵小頭目不該在人背后開槍,手起刀落,就把小頭目給殺了。此后幾十年,山匪依舊在茈碧壩子橫行,卻對小果村秋毫無犯。新政府成立后,肅清了土匪,遠近村落重現(xiàn)安寧。據(jù)說,大爺就被村民葬在花石坡中。
義 地
對于一個千百年來沿襲土葬習俗的村落,村子的后山就是墳場。牛滾塘附近,直至花石坡,大大小小的私家墳場大多以家族姓氏命名,譬如“王家墳”“小王家墳”“楊家墳”“五弟兄墳”,還有些以地理地貌命名,如“大墳”“七登墳”等等,村里有老人去世,子孫后代自會把他葬到自家的墳地里。
然而從花石坡到小王家墳之間,有一塊墳場居然沒有姓氏,被村民們稱作義地。據(jù)說這曾是一塊風水寶地,誰家有人葬到這里,后世就會特別旺,誠所謂“為士者程高萬里,為農(nóng)者粟積千鐘,為工者巧著百般,為商者交通四海”。村里曾為這塊地爭得不可開交,甚至發(fā)生好幾次械斗,鬧出了人命。最終告到了縣衙里,縣太爺親自下來裁決,就把這塊地劃為義地。
在小果村村民的信念里,那些年少早夭者、客死異鄉(xiāng)者、死于非命者,是不能葬到祖墳的,否則就會壞了自家的風水,只能安葬到義地里。后來我們這個村落,曾經(jīng)接納了好幾個安置戶,他們沒有墳山,老人去世后沒有安葬之地。在家里停柩數(shù)日,尸體都要發(fā)臭了,也想不出個辦法。于是小果村村民共同商定,讓他們把老人葬到義地里去。轉(zhuǎn)眼幾十年過去,義地已經(jīng)接納了他們幾輩人中的十幾口人,當然也包括了土山神前那個早夭的少子。于是這塊窄窄的土地,居然也成了小果村仁義團結(jié)的另一種象征。
 作者:北 雁
作者:北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