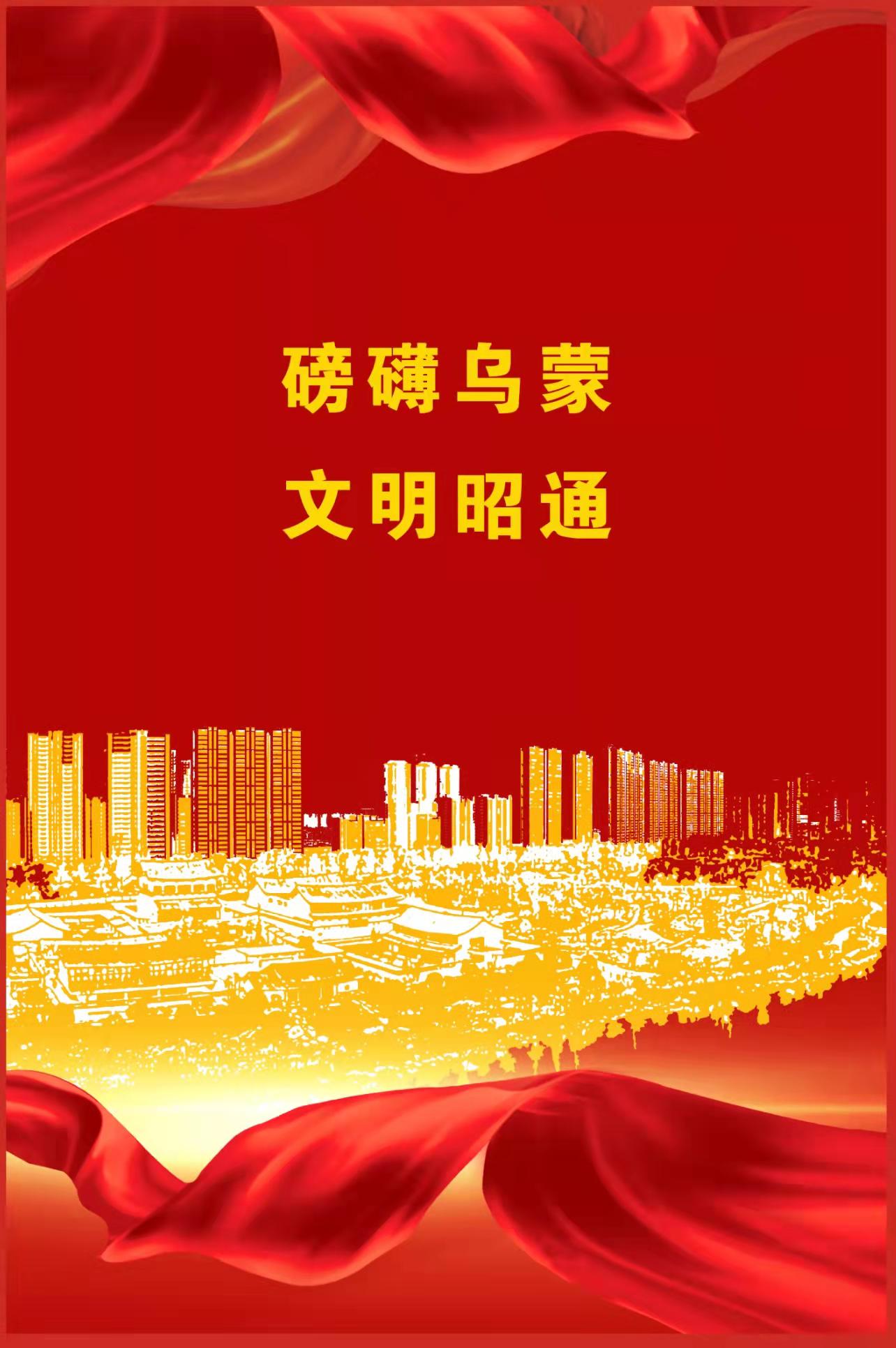2023-05-18 10:23 來(lái)源:昭通新聞網(wǎng)

我乘坐的中巴車穿越陽(yáng)光的海洋,撥開河谷氣候的幔帳,在玉溪市易門縣峽谷中的綠汁鎮(zhèn)小廣場(chǎng)停下。
小廣場(chǎng)是2個(gè)燈光籃球場(chǎng),正前方是當(dāng)年的舞臺(tái),燈光設(shè)備依舊,長(zhǎng)方形的舞臺(tái)頂部正中是熟悉的五星大圓章,左右有3面紅旗護(hù)衛(wèi),下方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guó)共產(chǎn)黨萬(wàn)歲”一排紅色大字。久違的時(shí)代烙印,一目了然的舞臺(tái),頃刻間將時(shí)光拉回到當(dāng)年沸騰的時(shí)代。
我從沉思中回到現(xiàn)實(shí),扭頭看見2棵巨大的攀枝花樹,一左一右仿佛云里金剛般聳立在路的兩邊,只能仰視其筆直的威儀。
攀枝花樹下是露天衣攤,懸掛著價(jià)廉物美的各類衣物。攤主們坐在小板凳上,將掉落的攀枝花摘去花瓣,留下金黃色的花蕊。這花蕊是綠汁鎮(zhèn)獨(dú)有的美食,帶著綠汁江邊的香甜,爆炒之后,在口腔中激蕩起不能復(fù)制的綠汁江風(fēng)味。
在綠汁鎮(zhèn)稍作休息后,一行人到達(dá)三家廠礦山的鐵橋邊。2座雜木亂草籠罩的山體間,青灰色山坡從山頂一直蔓延到山腳,將兩山的峽谷堆積成山坡和新的山梁。
抵近深邃的礦道,努力復(fù)原當(dāng)年那群最勤奮的人,大步走進(jìn)礦井,坐著罐籠深入大山底部,甚至到達(dá)綠汁江之下的深井中,雙手握著鑿巖機(jī),將鋼釬奮力扎進(jìn)巖石的情形。可惜,身邊沒有當(dāng)年的掘進(jìn)工,想象的場(chǎng)景畢竟有虛幻的陰影,并不能真實(shí)地再現(xiàn)歷史上那段時(shí)光的精彩。
所幸,身邊隱藏著一位當(dāng)年的掘進(jìn)工。他就著一杯白開水,端坐在辦公室一把普通的椅子上,不動(dòng)聲色間,用滑潤(rùn)的語(yǔ)言,洇開歷史的粉塵,清洗出那段塵封已久的往事……
身邊的掘進(jìn)工,是云南省報(bào)告文學(xué)學(xu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楊紅昆。他退休前的身份,是云南省作協(xié)副主席、秘書長(zhǎng)。這位滿眼睿智的作家,謙和文靜,跟掘進(jìn)工完全搭不上邊,更想不到他竟然還有4年的礦工經(jīng)歷。他不僅見證了易門銅礦的興盛,還是用鑿巖機(jī)將鋼釬硬生生打進(jìn)礦脈的青年掘進(jìn)工,并且曾經(jīng)代表青年突擊隊(duì),在千人大會(huì)上宣誓表態(tài),要以優(yōu)異的成績(jī),大戰(zhàn)紅五月,向勞動(dòng)節(jié)獻(xiàn)禮。
話題打開,他的回憶從初進(jìn)礦山開始,娓娓道來(lái)。平靜的敘述中,厚重的生活經(jīng)歷帶著銅的質(zhì)感,沉甸甸直達(dá)心房深處。
1971年12月,19歲的他以知青身份參加工作,由瀘西縣前往易門銅礦報(bào)到。背著塞滿行李的一個(gè)樟木箱子,用網(wǎng)兜裝上洗臉盆、搪瓷口缸、毛巾、牙刷,跳上解放牌卡車,跟車上的知青一起,踏上了銅礦工人之路。
卡車沿著山路緩慢前往綠汁鎮(zhèn),車后卷起的灰塵,落到車廂里的人身上。漸漸地,興奮被疲憊取代,以至于到了72道拐,俯視山下的綠汁鎮(zhèn)時(shí),大家只將“到了”這句話沖到喉間就咽回去。
卡車走完72道拐,進(jìn)入綠汁鎮(zhèn)的時(shí)候,滿心歡喜的他發(fā)現(xiàn)卡車沒有停下來(lái)的意思,而是穿過綠汁鎮(zhèn),駛進(jìn)綠汁江邊的山路,繼續(xù)向前行駛。扭頭看著遠(yuǎn)去的小鎮(zhèn),隱隱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看來(lái),之前將礦山的環(huán)境想得太好。
爬上一座山坡,穿過一個(gè)隧道,眼前豁然開朗,大片廠區(qū)出現(xiàn)在眼前,這才到達(dá)此行的終點(diǎn)——易門銅礦鳳山分礦。長(zhǎng)途跋涉,讓剛參加工作的興奮消失殆盡,那后悔之心,無(wú)法言說。不過人的情緒可以轉(zhuǎn)換,可以調(diào)節(jié),可以由意志控制,既來(lái)之,則安之。
情緒轉(zhuǎn)換的節(jié)點(diǎn)來(lái)自工作服。報(bào)到之后,新工人每人發(fā)2套工作服,包括口罩、安全帽、一雙黑色高筒膠皮水鞋。1971年,藍(lán)色的工作服堪稱禮服和標(biāo)簽,就算是出入高級(jí)廳堂,也自帶浩蕩之氣。車站、碼頭處,更是引人注目。穿上工作服,左胸前的部位赫然印著“云南冶金第三礦”幾個(gè)字。情不自禁間,有了些許釋然。
工業(yè)生產(chǎn)有自身規(guī)律,崗前教育培訓(xùn)必不可少。第一堂課便是到三家廠憶苦思甜爬老洞,體驗(yàn)解放前的舊礦洞,感受那個(gè)時(shí)代的礦工生活。易門銅礦開采早在明朝萬(wàn)歷年間就有一定規(guī)模,清乾隆年間達(dá)到鼎盛,之后一直開挖不斷,遺留大量舊礦洞。
同伴依次進(jìn)入出口只能容納一個(gè)人身的礦洞,局促感令人緊張、壓抑。到新礦井,進(jìn)到開采面,高大的空間,令人豁然開朗。新礦井跟舊礦洞有交集,交集處會(huì)有神奇的場(chǎng)景出現(xiàn)。盡管舊礦洞封閉良久,但銅礦的耀斑肉眼可見,藍(lán)色的孔雀石在頭頂閃閃發(fā)光。“這就是銅礦”,他被眼前細(xì)碎的光芒吸引。足夠卡車行駛的新礦井,開闊、通暢、明亮、透氣性好,19歲的他感覺稍好。
4年的掘進(jìn)工生涯,在大山的肚腹中端著45千克重自動(dòng)鑿巖機(jī)工作的情景,至今鐫刻在他的腦海中。封閉影像的高潮部分是打天井,只要回憶的“按鍵”啟動(dòng),便如激光三維畫面,栩栩如生地展現(xiàn)在眼前。
作為掘進(jìn)工,在整個(gè)礦井掘進(jìn)過程中,打天井最難。穿著雨衣、長(zhǎng)筒膠皮水鞋,從平巷位置向上打。抱著45千克的鑿巖機(jī),先用60厘米長(zhǎng)的鋼釬找眼,每掘進(jìn)20厘米后,換80厘米、1米、1.2米的鋼釬往里打。打到高處,要站在吊罐中打眼。天井較淺,打到10多米的時(shí)候,如果不能克服幽閉恐懼癥,就無(wú)法在這樣密閉的環(huán)境中堅(jiān)持。打眼有講究,要打出主眼、副眼、邊眼共16個(gè)眼。盡管戴著雙層口罩,依然擋不住石屑、粉塵的入侵。精疲力竭地下班后,到澡堂沖洗,還是能從臉上摳下一層帶著硬殼的灰泥。
還有一種更加困難的打天井方式就是打繃子。打繃子通常是在不適宜安裝罐籠的礦脈區(qū)域,在堅(jiān)硬的巖石天井左右兩邊打4個(gè)石窩,然后將2根欀木塞進(jìn)窩眼,打上楔子固定好,再搭上50厘米左右寬的木板,一個(gè)“支護(hù)”便算完成。天井的高度在18米到20米之間,相當(dāng)于6層樓的高度,通常要搭8個(gè)左右的支護(hù)層。
天井打到一定的高度,每上升3米左右,技術(shù)員就會(huì)將勘測(cè)好的打洞室的位置標(biāo)注好。這個(gè)時(shí)候,需要暫停向上掘進(jìn)的工作,打出幾個(gè)較淺的洞室。待天井打好之后,再將這些洞室擴(kuò)寬擴(kuò)深,將深孔機(jī)搬運(yùn)進(jìn)洞室,由深孔組的打裝填炸藥的洞眼。洞室有重要的作用,就是存放鑿巖機(jī)、鋼釬、麻繩、木板、欀木等工具。
打天井、打繃子一定是體力最好、最能吃苦耐勞的班組,青年突擊隊(duì)是首選。正是因?yàn)楹馁M(fèi)體力,工作強(qiáng)度大,需要打繃子掘進(jìn)的天井,一個(gè)班組通常需要5個(gè)人。2個(gè)人負(fù)責(zé)用鑿巖機(jī)打眼,2個(gè)人負(fù)責(zé)打繃子、維護(hù)修繕支護(hù),1個(gè)人打雜,維護(hù)電路、水路、高壓氣泵,同時(shí)負(fù)責(zé)背炸藥。炸藥在平巷的炸藥庫(kù),領(lǐng)取之后,裝在麻布制成的簡(jiǎn)易“褡褳”中,將“褡褳”放在肩上,炸藥放在胸前后背的“褡褳”中,小心帶進(jìn)天井,放進(jìn)最高層的洞室中,等待裝填進(jìn)洞眼爆破。
底部的繃子有簡(jiǎn)易木梯,到了高處,連木梯都沒有,只能像做“引體向上”一樣抓住繃子,用力拉上去。其間的辛苦,用語(yǔ)言實(shí)在無(wú)法形容。
高強(qiáng)度的勞作,加上吃飯時(shí)間不規(guī)律,雖然工作期間有頓勞保餐,但還是累出胃病,不時(shí)發(fā)生胃絞痛。而胃病,在礦山屬于常態(tài),只有在胃絞痛發(fā)作時(shí),才到醫(yī)務(wù)室打一針,回來(lái)繼續(xù)扛著鑿巖機(jī)打眼……
說到這里,楊紅昆停下話頭,神情凝重地說:“易門銅礦或者說云南冶金第三礦,因?yàn)橘Y源枯竭已經(jīng)完成其歷史使命。但是礦上這群新中國(guó)最勤奮的人當(dāng)中,我以曾經(jīng)是其中的一員而自豪,更自豪流淌的汗水跟銅有過最親密的交融。這種勤奮有遺傳基因,會(huì)一代代傳下去。事實(shí)上,這種精神正在延續(xù)。”
他寫的律詩(shī)《易門銅礦記》:“幾度綠汁木棉紅,日照鳳山走荒蕪。時(shí)光過盡容顏改,曉風(fēng)冷雨濕心頭。青春似火江渚上,英俊少年也風(fēng)流。銅礦歲月多少事,夢(mèng)里依稀向東流。”詩(shī)言志,讀之滿滿滄桑感。在新中國(guó)成立的幾十年時(shí)間里,從“40后”到“60后”,這群稱得上全球最勤奮的勞動(dòng)者,帶著“只爭(zhēng)朝夕”的信念,1天當(dāng)2天干,干出了改革開放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筑牢了中華民族復(fù)興的基石。這群最勤奮的勞動(dòng)者,遍布中華大地,他們有大格局大情懷,犧牲小我小家,不計(jì)個(gè)人得失,是新中國(guó)的隱性脊梁。他們大多與新中國(guó)同歲,已然斑白的頭發(fā)上,寫滿的是無(wú)怨無(wú)悔和老驥伏櫪的壯志豪情。

作者 官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