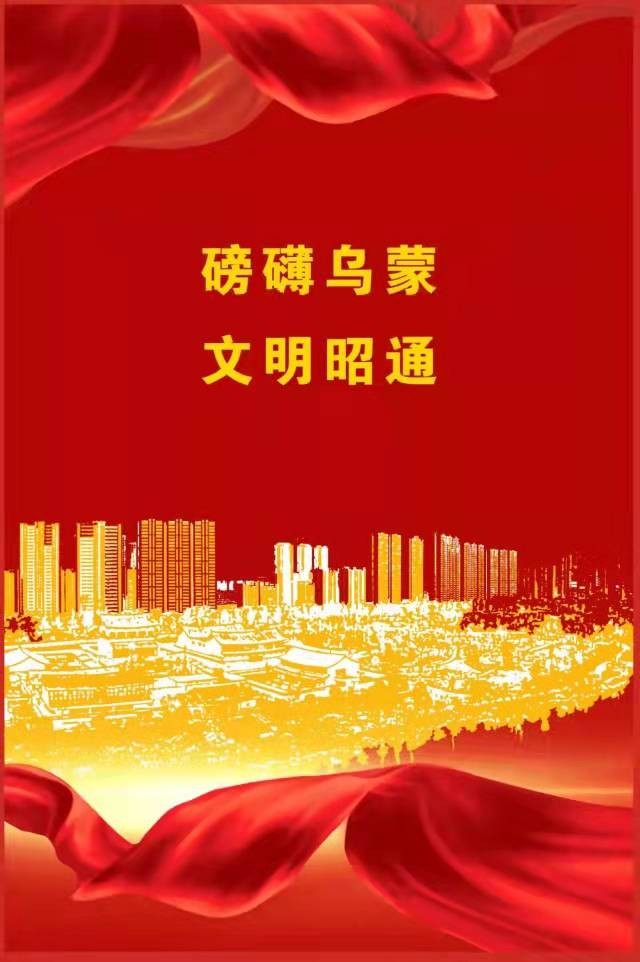2023-06-04 12:21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從鎮(zhèn)雄縣城往東走,穿過潑機古鎮(zhèn),翻過關(guān)門山埡口,站在瓜塢梁子朝東北方向望去,有一個被大山簇擁、被綠樹掩映的村莊,那便是尾嘴。它像一顆璀璨的綠寶石鑲嵌在大山的懷抱里,靜靜地躺在綠樹翠竹中。白云從羊耳山頂飄過來親吻它,沙坎河水彈響琴弦陪伴著它,花漁洞的濤聲撫慰著它,劉家山的松樹林凝望著它——
它叫尾嘴,是我的故鄉(xiāng)。
小時候常聽大人調(diào)侃,尾嘴從羊耳山下往下鋪開去,直到沙壩河邊,尖山像一把殺豬刀迎接著它,所以尾嘴是“群豬下壩”。站在羊耳山上,望著寬敞的尾嘴,我就想,它怎么就叫“群豬下壩”呢?
此時此刻,我站在尾嘴,確切地說是上尾嘴,更確切地說是站在上尾嘴的王家寨官方名叫上寨的老祖屋前,這是我童年時無比流連,少年時無比討厭的老屋,現(xiàn)在無比懷念的老家,留下我的多少情懷、多少夢……
尾嘴稱為壩子,叫尾嘴壩。有一首山歌是這么唱的:“尾嘴壩兒閃悠悠,有女不嫁小河溝,下雨又怕河水漲,天晴又怕沙子溜。”小河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山高坡陡河深谷沉,人居環(huán)境比較惡劣,那是一定的了。其實這首山歌無非是用對比的手法襯托出尾嘴的山美、水美、人美,并沒有貶低小河溝的意思。小時候的尾嘴有很多水田,站在尖山頂,踩著沙壩河的波濤往上看,層層梯田猶如一塊塊明鏡,映襯著山巒,倒映著藍天。艷陽下,鳥聲中,這些梯田你牽著我、我拖著你,隨著田間流淌的水聲,整個一幅水墨畫。插秧季節(jié),田里到處是攢動的人影,有的背秧苗,有的甩秧苗,一小捆一小捆的秧苗散落在水田,就像一個個處子在等待插秧人解開他心中的情懷,放飛他心中的夢想。大家站在田里,呈直線排成一道風景,然后彎著腰插秧。這種情景唐代詩人布袋和尚描寫為:“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布袋和尚說,低頭是做人的一種方式,只有低頭才能看見人性的光芒。家鄉(xiāng)父老一年四季都在田里勞作,背著藍天指點水田,其實他們是在釋放一種做人的態(tài)勢。通常插秧季節(jié)是春末初夏,那時還是微雨時節(jié),人們戴著斗笠、披著蓑衣,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個跳動的音符。在田埂上歇腳的時候,有大嫂就會唱:“大田栽秧行對行,一對鴛鴦來歇涼。悄悄話兒說不盡,月亮落后抱成雙。”她緋紅著臉,一往情深望著秧田的盡頭。山歌婉轉(zhuǎn)悠揚,在細雨中張揚著對美好生活的期望。有人說,人生最美的風景是看漁家小妹撒網(wǎng)、看農(nóng)家大嫂插秧。唱歌的大嫂緋紅的臉寫滿醉人的歌謠,青青秧苗便在她清亮的山歌聲中變成斜對斜、橫對橫、豎對豎都成線的一個個音階、一行行詩。待秧苗在田里立穩(wěn)、轉(zhuǎn)青、成長,長成一片沸騰的海,遠遠看就像一個大草甸,青青的秧苗在風中一起舞蹈,一起呼吸,一浪涌成千重浪,開成萬道波,令人想起:“稻谷千重浪”“麥浪滾滾”這些優(yōu)美的詩句。尾嘴雖然有大片大片的田,但尾嘴人是吃不上大米的,大米在那些年被上交公糧了。為了多填飽肚子,分到手里的一點稻谷,有的人家就拿去換成苞谷來吃,一斤稻谷可以換三四斤苞谷,在那個艱難的時代,吃飽肚子,有力氣干活才是硬道理。要吃上大米飯,除非過年,或者是來了貴客,或者是感冒了,將大米熬成稀飯,就著煳辣椒,再拌上三兩瓣大蒜,喝一碗下去,瞬間滿頭熱氣,大汗淋漓一通渾身有力氣了,感冒立馬就好了。老家出產(chǎn)一種“竹丫糯”的飯米特別香,還有點糯,蒸飯的時候整個寨子都溢滿清香,從寨子中間經(jīng)過,誰家飄出“竹丫糯”的香味,就知道誰家來了最親近的人。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看書,每到開學季發(fā)新書的時候,語文書一個星期就被我看完了,當然也不是囫圇吞棗過一遍,有的課文還是很認真地讀了。印象中有一篇《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的課文,道理很淺顯,文字很優(yōu)美:“四周黑洞洞的,還不容易碰壁嗎?”至今記憶猶新。還有一篇現(xiàn)代寓言詩《池子和河流》不知看過多少遍,大意是池子在嘲笑河流不停地奔流,河流勉勵池子,出來走走不要過于安閑,結(jié)果池子干涸了,河流仍在奔流,奔騰的浪花表達對藍天白云、青山綠水的喜愛。當時就明白,人要像河流一樣熱愛生活,熱情向往,不停地創(chuàng)造,不停地探索,也不停地享受。有一年湊了一角二分錢,請經(jīng)常去畢節(jié)的表叔買了小人書《看不見的戰(zhàn)線》,連續(xù)幾個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翻看。一盞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燈在夜幕降臨的時候亮起微弱的燈光,從門縫、窗縫里透出來,給靜謐的小山村平添了幾分生氣。當年借著煤油燈,我看完了《劍》《連心鎖》,還有《金光大道》《林海雪原》,特別喜歡《連心鎖》,雖然才十一二歲,但是中朝兩國人民的友誼還是理解的,“后面似乎還有很多兵,但由于青紗帳的遮掩看不清了”這樣的句子至今還記得。
書給了我童年的快樂。學校里有一年秋季學期,從東川轉(zhuǎn)來了一個學生,姓陳,其父是東川銅礦的工人,家里有很多小人書。有一天放學,他和一個同學邊走邊談小人書,談到高興處,還“啪”地立正敬禮:“報告長官,馬蹄哨放哨的小子叫我逮住了!”我好奇問他怎么回事,他說小人書上寫的。從此我黏上了他,叫他借書給我看。開始他很樂意借給我,后來見我沒有交換的小人書,漸漸疏遠了我,以至徹底斷供。有一天放學后我攔住他,想向他再借一次書,他不干,搖著頭跑了,我追上去,一腳踢在他的屁股上。那時是雨后,道路泥濘,他摔了個狗吃屎,哭著回家了。同學之間打架,摔個跤是常有的事,我沒當回事。晚上回家,父親一把抓住我的衣領(lǐng),一腳踢在我的屁股上,吼道:“你長力氣了,還叫人狗吃屎了,我也叫你狗吃屎一回!”但我沒有狗吃屎,我踉蹌了一下,忍著疼,忍著要沖出眼眶的眼淚說:“有本事你去買小人書給我看。”可憐的父親揚起的手掌也垂了下來。母親連忙勸阻道:“算了算了,他以后不敢了。”父親窮啊,他哪有錢給我買小人書,瓜兒、豆豆、洋芋能夠讓我們吃飽就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看著父親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哭了。父親很難,祖父在他兩歲的時候就去世了,祖母帶著他,窮困潦倒,沒有讀書上學。長大后自己偷學才能夠識點文字、算點工分,當了生產(chǎn)隊的會計,會讀點文件報紙,傳達上級會議精神。他深知讀書的艱難和重要,供我們讀書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那時候除了看書,最快樂的事就是看電影了。公社放映隊巡回到生產(chǎn)隊放電影,太陽沒有落山寨子里的孩子就早早把板凳抬來占座位,電影在各生產(chǎn)隊巡回放,我們就循環(huán)看,不管天多黑、路多遠,都要去看。那時放映影片大多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 》《奇襲》《偵察兵》,看的次數(shù)多了,我們連臺詞都全部記得。有次在劉家寨放《智取威虎山》,我跟著銀幕上的臺詞念:“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間,壯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淵。”旁邊一個大哥拍著我的肩膀說:“不錯,不錯,這些字都認得,以后定有出息。”他姓幸,在鎮(zhèn)雄氮肥廠當工人,拿工資吃飯,穿一身洗得發(fā)白的勞保服,比起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óng)民叫人羨慕不已。我謙虛地笑笑,沒有說話。第二天大人出工去了,我就帶著兩個弟弟迫不及待找來母親的圍腰,學著楊子榮的樣子亮個相:“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給我智慧給我膽,千難萬險只等閑……”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兩個弟弟笑得人仰馬翻。而國營黑樹硫磺廠的禮堂里放電影是沒有排班次的,領(lǐng)導(dǎo)想放就放,或者工人要求放就派車把電影機拉來就放,不像生產(chǎn)隊要派人去背。
我家離硫磺廠只有五六公里,一聽到消息,說硫磺廠要放電影,我們總是盼著太陽快下山,把肩上割豬草的背簍一甩,飯也不吃就朝硫磺廠跑。
尾嘴人歷來善良、誠實、堅韌且好客,母親就是其中的一位。母親不識字,只認得人民幣,受父親的影響,她也堅定地支持父親供我們讀書。她栽種的菜有大白菜、青菜、小白菜、瓢兒菜,不同季節(jié)栽不同的菜種。我的那本《新華字典》就是母親背了一籃子菜去硫磺廠賣了,用七角二分錢買來的。坐在教室里,雙手撫著藍色封面的字典,我滿臉都是喜悅,這本字典我用了好久,老師說字典是工具,它可以打通我們識字的通道,幫助我們走進文字的天堂,享受春花和秋月、朝露和晚霞,看山色晴嵐,聽潮汐唱歌。憑借著這本字典,我積累著詞匯,克服著閱讀障礙,語文功底慢慢扎實起來,我有篇作文《毛主席是我心中的紅太陽》還得到老師的表揚并張貼在學校《學習園地》的突出位置。
一根扁擔、一個針線盒,是母親的二寶。一根竹制的扁擔,兩肩沉重的風雨,一頭是全家人的生活,一頭是全家人的未來。大米飯是很難吃到的,苞谷飯有時也要斷頓,但洋芋是讓我們能夠吃飽的。洋芋是我們的主食,燒、蒸、煮、炸,我們都能吃飽,我的胃喜歡洋芋駐扎。那時她常說,衣服被子可以破但絕不能臟。母親幾乎天天都洗衣服,我們的衣服總是干干凈凈的。受母親的教誨,我很小就學會了洗衣服要先洗衣領(lǐng),再洗衣襟,洗袖子,最后洗背面。現(xiàn)在用上洗衣機了,我還喜歡聽洗衣機振動的聲音,喜歡看波輪攪起的水浪在水缸里旋轉(zhuǎn),每當這時,我仿佛就看到母親在太陽光下一下一下地揉搓著衣服,滿臉的微笑。撒谷種的時候,母親就擔著裝滿大糞的桶在田野里穿梭,兩只糞桶就像兩只蝴蝶,隨著她身子的擺動一下一下地飛舞,微風吹著她的頭發(fā),此時的她就像田野里一幅移動的畫。母親的針線盒里總是裝著針線、頂針和錐子,她總是不停地縫縫補補。她縫補我們的衣服也是在縫補艱難的生活,一針一線,日子在她綿長的針線里走過了一天又一天,我們也一天一天長大。母親納的千層底我們穿著很實在,母親縫的新書包我們背著很溫暖。每當我看書的時候,母親總是在煤油燈下,或是納鞋底,或是干著點零活陪伴著我,不管夜多深多沉,她都始終在我身邊。春天,母親就像一縷風,撫慰著我;冬夜,母親就像一堵墻,為我遮擋著寒冷。母親的慈祥善良和深明大義,是遠近聞名的。對弱者的同情伴隨著她的一生,就是叫花子從家門口過,她都要喊進屋里給他熱菜熱飯吃,走的時候還要撮一碗苞谷面給他帶上。有一次,一個鄰村的小伙子到寨子偷東西被抓住,幾個年輕人虎著臉要給他上繩子。母親連忙阻攔,問清小伙子是家里實在揭不開鍋蓋了,才不得不出來偷點吃的后,對大家說:“算了算了,不是生活艱難,他也不會做出這么丟人現(xiàn)眼的事。”小伙子望著母親,眼淚在眼眶里打轉(zhuǎn)。母親是文盲,她不知道她的這種行為被明代洪應(yīng)明創(chuàng)作的語錄體著作《菜根譚》早就說成至理名言:“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時,減三分請人嘗。”《增廣賢文》也有言:“馬險不揚鞭,人難不添言。”后來的一個母親節(jié),一個網(wǎng)友在微信里留言;“我以一聲媽媽為理由向她無盡索取,她以一聲媽媽為枷鎖,向我無限付出。媽媽這兩個字僅叫一叫,都很容易讓人哽咽。”感同身受。
寨子里有一口井叫陽和水井,一口冒沙井,水波粼粼,清澈純凈,它承載著一寨人的生活用水,也承載著一寨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井水冒出來,往下流,流成一條清涼的水溝。寨子里的大娘、大媽、姐姐、妹妹就在河邊洗衣服、洗鞋子,順便說點家長里短,激起一片歡樂的笑聲。其間,一位潘姓的小姐姐尤為顯眼。她長得精致,燦爛的臉上總是洋溢著笑容,一頭烏黑的頭發(fā)披在腦后,瀑布般光滑美麗。她喜歡在頭上插一朵豌豆花或是洋芋花、油菜花,不同的時節(jié),不同的花兒在她的頭上開放,蜻蜓一樣舞蹈,簡直美極了。我喜歡看她頭頂上飛舞的陽光,喜歡她玲瓏小巧的手在溫暖的水里上騰下躍,喜歡她微笑時露出的白白的牙。有時候我會對著冒熱氣的水井發(fā)呆,小姐姐是仙女下凡嗎?后來我走出尾嘴,再后來聽說小姐姐嫁到貴州畢節(jié)去了,后來每當聽起張也演唱的《小橋流水》“水做的浣衣女,她飄呀飄走了……春風把豌豆花貼在你的發(fā)梢……”不免一陣悵然,很久很久以來那朵豌豆花依然開在我心里,蜻蜓般舞蹈。
故鄉(xiāng)尾嘴,長居我心。

作者:王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