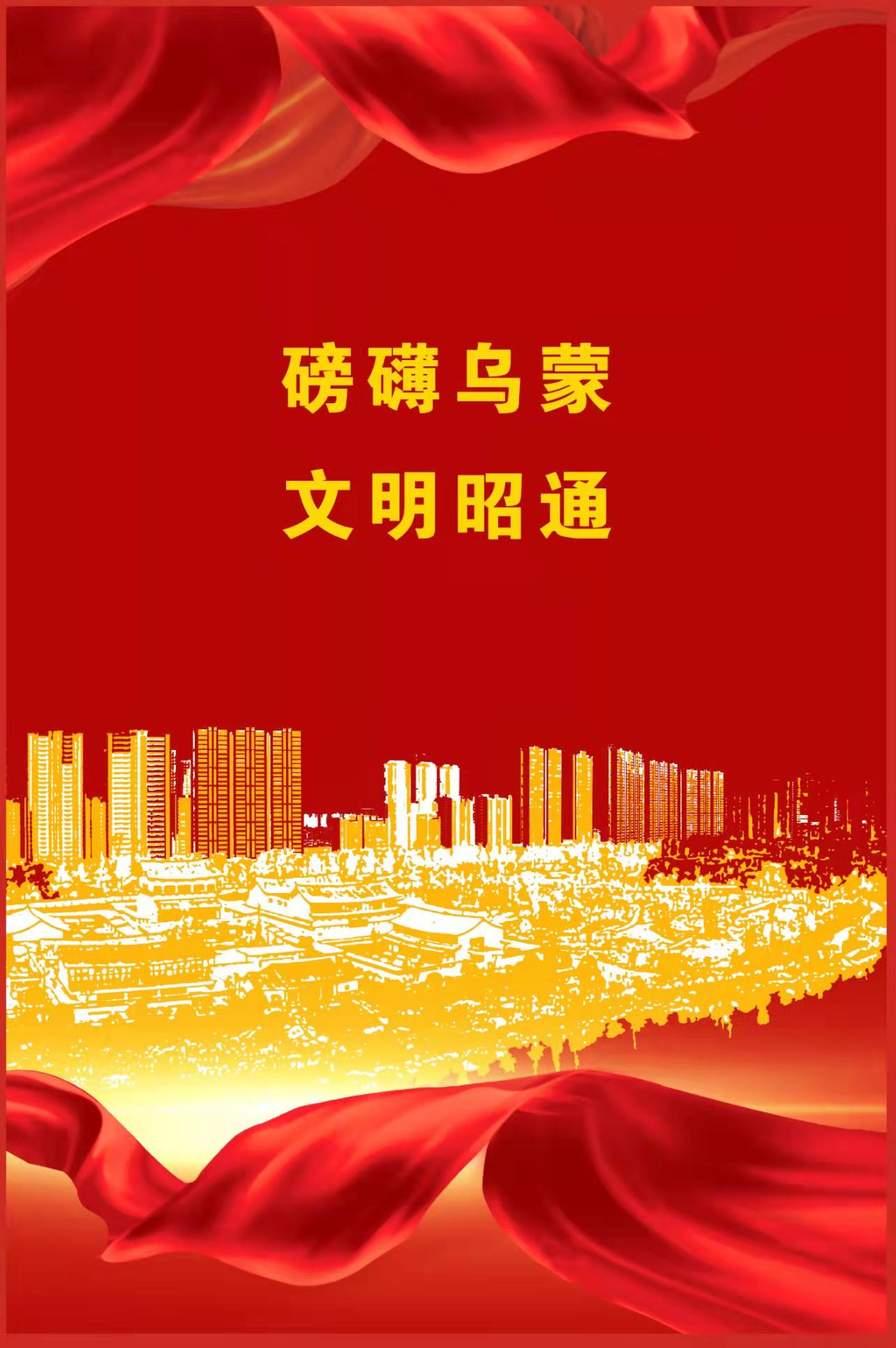2023-06-13 11:23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如果一棵樹枯萎了,如果只是樹冠枯萎,這只是因?yàn)楦貌粔蛏睢U麄€(gè)世界都是它的領(lǐng)地。
——(德)弗里德里希·黑貝爾
鄉(xiāng) 愁
當(dāng)我在故鄉(xiāng)想起并再三撫摸故鄉(xiāng)的疼痛時(shí),就像一個(gè)病人清醒地承受著自身病痛的折磨,憂郁地想著如何才能減輕和治愈這種病痛。然而,不為良方難尋,我渴望痊愈的心態(tài)亦不知該向誰訴說,一如我不知道該對(duì)誰傾訴我對(duì)故鄉(xiāng)之現(xiàn)狀與未來發(fā)展的深切憂慮。這也許就是現(xiàn)代人常說的鄉(xiāng)愁吧!
“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住慣的山坡不嫌陡”“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稻草窩”“在家千日好,出門時(shí)時(shí)難”……當(dāng)我打算開口指陳故鄉(xiāng)的諸多病癥時(shí),關(guān)于熱愛、贊美、歌頌和眷戀故鄉(xiāng)的各種諺語、俗語便如晨鐘暮鼓般回響在我耳畔。因此,我總是陷入憂傷、焦慮不安的深淵般的沉默中。回望歷史悠久的故鄉(xiāng),面對(duì)隱秘而龐大的民族、宗族和家族血脈譜系,面對(duì)古老神圣、莊嚴(yán)肅穆而時(shí)常令人心生溫情與敬畏的宗祠,哪怕滿懷憂思和令人窒息的壓抑感,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huì)輕易無端地抱怨自己的生養(yǎng)之地,盡管有些自以為識(shí)時(shí)務(wù)的人早已頭也不回地棄之而去。
詩人海男有著浪漫而深沉的小鎮(zhèn)情結(jié)。她在《論小鎮(zhèn)》里寫過:“小鎮(zhèn)很安靜,就幾條街巷,走著走著就走完了。云南的所有小鎮(zhèn)在我看來,都是有福報(bào)者居住的地方。”年輕時(shí)曾經(jīng)四處漫游的海男說道,人的居處是天注定的,“我相信宿命,并一直遵循天意生活著。”所以,她漫游歸來后一直安居在云嶺高原,在三迤大地山水間潛心行吟。
我出生于滇中嵩明縣城邊上的一個(gè)小鎮(zhèn),除了負(fù)笈昆明讀書幾年外,我一直生活在故鄉(xiāng)一座名為嵩陽的小鎮(zhèn)上。小鎮(zhèn)就是嵩明縣城駐地。縣城固然很小,但作為一個(gè)縣域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中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稱之為“帝都”。
“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鄧麗君溫婉動(dòng)人的歌曲,仿佛正為如是縣城譜寫。
導(dǎo)演賈樟柯頗具縣城情懷。他的《小山回家》《小武》《站臺(tái)》《任逍遙》《山河故人》等電影均以汾陽縣城為背景。他稱贊縣城生活非常有誘惑力,讓人有充裕的時(shí)間去感受生活的樂趣。在滿街熟人的城里隨意廝混,“這種生活是有美感的,人處在熱烈的人際關(guān)系里面,特別舒服。”他同時(shí)感慨,“但是如果每天都離不開這片土地,還是相當(dāng)枯燥。早上起來躺在床上,縫隙之間會(huì)有一種厭倦感。”但在作家張楚看來,縣城隨著人心之激變已越來越世俗勢(shì)利,人們?cè)絹碓轿镔|(zhì)化和機(jī)械化,他曾在《在縣城》一文中抱怨小城人:“談起話來,每個(gè)成年人的口頭都離不開房子、金錢、女人和權(quán)力,似乎只有談?wù)撨@些,才能讓他們身上的光芒更亮些。”張楚因此發(fā)現(xiàn)并寫下了許多有趣而悲傷的縣城故事。就我們自負(fù)的“滿街熟人”這種自豪感,評(píng)論家何平一語道破縣城生活的人際關(guān)系真相:“縣城是熟人社會(huì),熟可能更多是表象,相見不相識(shí)是本質(zhì)。”豈止縣城如是耶?實(shí)則整個(gè)人情社會(huì)皆如此。
像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很少離開里斯本一樣,無論感覺舒服抑或枯燥,我似乎也只能在作為故鄉(xiāng)的縣城生活一輩子了。這是我自己注定的。此前,在我青春得意陽光燦爛的時(shí)候,我曾有多次調(diào)離縣城到省城工作的機(jī)會(huì),但我都毫不猶豫地放棄了。
羅伯特·伍斯諾在其名著《小鎮(zhèn)美國(guó)》開篇說,小鎮(zhèn)是美國(guó)的恥辱,相對(duì)快速發(fā)展的城市顯得非常落后;小鎮(zhèn)是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的人們的避難所。他以浪漫而不屑的口吻反諷道,不幸的小鎮(zhèn)居民無事可做,只好看草長(zhǎng)鶯飛。
羅伯特真幽默。他豈能不知道,像奔波繁忙的都市人每天要為一日三餐操心,“無事可做”的小鎮(zhèn)居民同樣也要為一天早晚兩頓飯操勞。就基本的生存問題而言,人類面臨的處境沒什么區(qū)別。對(duì)生活于這一時(shí)代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止于溫飽層面上的活著也許不太難,難的是如何活得更好更滋潤(rùn)更為體面更有尊嚴(yán)。恕我冒犯——我向來討厭和蔑視那些逃離小城卻習(xí)慣于炫耀自己在大都市如何辛苦打拼的“成功人士”。面對(duì)堅(jiān)守故園的那些優(yōu)秀的兄弟姐妹,他們?cè)趺春靡馑紕?dòng)輒表功或像祥林嫂那樣叫苦呢?難道他們真的忘了,在他們心安理得遠(yuǎn)離故土甚至忘恩負(fù)義無情拋棄的故鄉(xiāng)小城和周邊農(nóng)村,還有很多熱愛故土家園的人在默默無聞、任勞任怨辛勤耕耘,他們?yōu)楣枢l(xiāng)發(fā)展付出的畢生心血和艱苦努力,也許永遠(yuǎn)都無法贏得鮮花掌聲和某些人僅用一點(diǎn)浮財(cái)捐資就能輕易獲得的贊賞與榮譽(yù),他們終生只能過著衣錦還鄉(xiāng)的淺薄者所蔑視的平庸平淡平凡的生活。有時(shí)候說來讓人辛酸而費(fèi)解:有些才洗腳進(jìn)城的人,身上的泥渣和土味都沒來得及抖落干凈,轉(zhuǎn)身就背叛了祖宗和土地。
作為資深的中國(guó)小鎮(zhèn)居民,我與終生居住在里斯本的費(fèi)爾南多·佩索阿性情和經(jīng)歷頗相似:我們都在平凡的崗位上做著枯燥而平淡的工作,除了短暫的外出旅游也很少離開生養(yǎng)之地。正如佩索阿習(xí)慣于經(jīng)常性地站在辦公室的窗口看著里斯本那條喧囂的大街,開始漫長(zhǎng)憂傷而無邊無際的頭腦旅行一樣,這并不妨礙我在安身立命的小城里,泰然自若地想象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布宜諾斯、吉隆坡、巴黎、紐約的生活情景。與全球大多數(shù)小鎮(zhèn)居民相同,我也深受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生態(tài)和道德諸多問題的困擾,我也有復(fù)雜多變的思想,也要認(rèn)真或天真地思考短暫的世俗人生價(jià)值和人生不朽的偉大意義。
我們不能選擇生身父母,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地。盡管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生活在別處”,但不管生活在哪里,無論小鎮(zhèn)居民還是都市貴族,我們都要承受命運(yùn)的恩賜和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輕或重——這是每個(gè)有夢(mèng)想的地球人必然面對(duì)的人生境遇。
在故鄉(xiāng)失去故鄉(xiāng)
我的故鄉(xiāng)嵩明原是一個(gè)山清水秀的大壩子,嵩明壩面積414.6平方千米,是著名的高原明珠,素有“滇中糧倉”“魚米之鄉(xiāng)”諸多美譽(yù)。青春年少時(shí),我經(jīng)常為它遼闊無垠的田野景象所震撼,為它四季鮮明而變幻無窮的景色所陶醉,為那些星羅棋布如詩如畫的寧靜村莊而縱情放歌。我曾贊美它:阡陌縱橫的田園就是絕色的天然國(guó)畫,明凈空靈的山水就是最美的人間詩歌;那是陶淵明、唐伯虎所描繪的世外桃源,那是謝靈運(yùn)、柳宗元謳歌的自然山水。那時(shí)我天真地以為,群山環(huán)抱的嵩明壩子就是一個(gè)獨(dú)立自由的理想國(guó)。它分明是失落人間的伊甸園,是如假包換的塵世天堂。
彈指間,人到中年,我所看到的故鄉(xiāng)早已不是昔日我在詩文里反復(fù)謳歌禮贊的那個(gè)魂?duì)繅?mèng)縈的人間仙境。意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說:“沒有離開過故鄉(xiāng)的人充滿了偏見。”背離故鄉(xiāng)的人何嘗不是如此。無論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的“偏見”,除去愛恨恩怨,或許都只是一種深刻的誤會(huì)。
喬治·斯坦納在其回憶錄中感嘆:“在我太過喧囂的生活里,我一直偏好收藏寂靜,但這是愈來愈難尋了。”他抱怨道:“在我的存在之中充滿了太多喧囂的城市、機(jī)場(chǎng),以及過多的言說。”他將平生浪跡之地及其行蹤視為“全是觀光”,唯有在“地靈”的重新導(dǎo)引下回到那個(gè)遺世獨(dú)立的“再無從覓得如此完美的境地”——他的寂靜卻生機(jī)蓬勃的故鄉(xiāng)N 地,他才能“聽見寂靜中的寂靜”,他也才會(huì)欣慰而平靜地說:“在N地,是一輩子的事。”我很羨慕斯坦納,他無論走得多遠(yuǎn),走得多久,最后總能“誤打誤撞地找到歸鄉(xiāng)”。
周曉楓在《有如候鳥》這篇散文中斷言,沒有哪個(gè)故鄉(xiāng)能與天堂媲美,否則我們就不曾遠(yuǎn)離;也許故鄉(xiāng)與天堂的相似之處在于,只有遠(yuǎn)離才能發(fā)現(xiàn)它的美,就像站在大地上才能仰望云層。她感嘆,在快速的城市化浪潮沖擊下,一個(gè)延續(xù)幾千年的鄉(xiāng)土中國(guó),漸行漸遠(yuǎn)。故鄉(xiāng),這個(gè)含情脈脈的詞語,內(nèi)涵被改變,甚至從地圖上被抹除標(biāo)記。“母親喂養(yǎng)我們年少的胃,故鄉(xiāng)的山河喂養(yǎng)我們的往事。我們?cè)褷I(yíng)養(yǎng)不良的土壤當(dāng)作貧瘠的故鄉(xiāng)來熱愛,可現(xiàn)在,我們難以找到整體的故鄉(xiāng),只剩破碎的土粒。家族、環(huán)境、習(xí)慣、風(fēng)俗和傳統(tǒng),靠一代代人來存儲(chǔ)和延續(xù);當(dāng)記憶遭到撕裂和洗除,出現(xiàn)難以逾越的代溝和斷崖,某種秘密的遺傳密碼被篡改了。”
正是由于遺傳密碼被野蠻篡改或遺忘,包括方言的消失和鄉(xiāng)音的變化,不僅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失去了故鄉(xiāng),悲哀的是,當(dāng)身在故鄉(xiāng)的我說起故鄉(xiāng)時(shí),面對(duì)老城和古老的村莊,眼看著生機(jī)盎然的田園一天天被鋼筋水泥的森林蠶食,我發(fā)現(xiàn)我已失去或正在失去故鄉(xiāng)。這是一個(gè)令人眩暈而尷尬的悖論:因?yàn)槲乙恢笔刂枢l(xiāng),我此生已注定不會(huì)離開故土。我早已將自己深深地植根于滇中這片豐美肥沃的紅土地上。我目睹著它一天天被人為地改變,我無法阻止。這是故鄉(xiāng)的命運(yùn),也是我的宿命。
馬修·阿諾德坦言,我們所有人都喜歡走自己的路,而不愿意被趕出大多數(shù)人習(xí)以為常的陳詞濫調(diào)的世界,“那把我們聯(lián)系在一起的紐帶”。我承認(rèn),我一直固執(zhí)地拒絕庸俗并獨(dú)自走著一條荊棘密布的寂寞之路,但我有時(shí)也難免“庸俗”地省思:也許改變才有活路或他們所說的出路,才會(huì)有眾人所向往的美好未來。我確實(shí)已無法融入鄉(xiāng)村社會(huì),以前為它做的那些小事不足掛齒,現(xiàn)在能為它做的事情也實(shí)在不多。
幾千年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不都是這樣存活下來的嗎?無論戰(zhàn)爭(zhēng)、貧困或任何令人畏懼的災(zāi)難,哪怕十室九空,都未能將它徹底毀滅。隱秘而清潔的電力悄然而熱情地改變了鄉(xiāng)村的生活方式,電燈代替了油燈和蠟燭,家用智能電器消滅了詩意氤氳的浪漫炊煙,聲色華麗且變化多端的電影、電視或KTV豐富、引領(lǐng)和導(dǎo)演著夜晚的娛樂生活……不得不承認(rèn),比大自然的閃電溫馨而實(shí)用的電力,讓鄉(xiāng)村的夜晚變得明亮而溫暖。不論多么懷舊戀舊,畢竟很少有人愿意在寒冷的風(fēng)雪之夜獨(dú)坐于微弱、飄搖不定的油燈下?lián)碇粋€(gè)行將熄滅的小火爐迎接黎明吧!
改變和激蕩鄉(xiāng)土生活方式的,還有從聚族而居漸變?yōu)椤靶?guó)寡民”式的居住模式,由傳統(tǒng)土木結(jié)構(gòu)演變?yōu)殇摻罨炷两Y(jié)構(gòu)的建筑以及時(shí)尚多元的鄉(xiāng)村建筑風(fēng)格,以牛馬驢騾為主的畜力車進(jìn)化為自行車摩托車轎車等各種先進(jìn)的交通工具……隨著物質(zhì)條件的改變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我們有意無意地注視著鄉(xiāng)土文明悄然而快速劇烈的嬗變。沒有人能阻止,也沒有誰——至少現(xiàn)在還沒有學(xué)者能從理論上為我們認(rèn)清并揭示這種文明嬗變的必然性及由此可能帶來的深刻影響。田野調(diào)查的文本結(jié)論很難讓人信服,但有一點(diǎn)卻毋庸置疑,那就是,身處這一時(shí)代的我們——無論農(nóng)民還是已然離開農(nóng)村的無論何種身份的曾經(jīng)的鄉(xiāng)下人,現(xiàn)在都無心或無暇來真正研究這種文明變遷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作為旁觀者或參與者,我們只會(huì)在某天突然面對(duì)物是人非的農(nóng)村社會(huì)時(shí),發(fā)出一種五味雜陳卻意味深長(zhǎng)的莫名驚嘆:一切都變了!是的,一切都勢(shì)不可擋、出乎意料地變了。
畢生深具俄狄浦斯情結(jié)的法國(guó)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主將羅蘭·巴特,在看到查理·克利福德拍攝的《阿蘭布拉》之后感慨,認(rèn)為并確信風(fēng)景的實(shí)質(zhì)就是使“母親”在他身上復(fù)蘇:“故鄉(xiāng)這東西喚起了我心中的母親。”在巴特這里,“故鄉(xiāng)”與“母親”這兩個(gè)符號(hào)自然地合而為一,成為他對(duì)母親和母愛的最佳理解與注釋。難怪,但凡喜歡以游子自況的人,都將故鄉(xiāng)視為精神上的母親。
“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之嘆,常讓我想到博爾赫斯關(guān)于故鄉(xiāng)悲情纏綿的解讀。阿爾維托·曼古埃爾曾講述過博爾赫斯關(guān)于故鄉(xiāng)的孤獨(dú)感受:“我最后一次見到博爾赫斯是在1985年,在巴黎洛泰爾酒店的地下餐廳。他很憂傷地談到阿根廷,說即使有人說那是他的土地,是他生活過的地方,但實(shí)際指的也不是具體的場(chǎng)所,而是一種歸屬感,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朋友們的陪伴。”
坦誠(chéng)說來,故鄉(xiāng)于我們,其實(shí)并非傳說中的伊甸園,它原來只是一個(gè)我們最為熟悉的地方,譬如靈魂之于肉身,它顯然只是一種文化心理上的歸屬感,倘若沒有親友的陪伴,沒有赤誠(chéng)的情感慰藉,那地理和空間意義上的故鄉(xiāng)于我們便失去了精神的寄托。故鄉(xiāng),這個(gè)給予我們生命、童年和夢(mèng)想的地方,最后變成了我們的埋骨之地,成了寂寞而永恒的歸宿。
土 地
說到土地,我就想起凌越《帶著貧窮和星辰》這首詩中的第一節(jié):
帶著貧窮和星辰,
天空收回豐饒的土地。
不再為哭泣動(dòng)容的故鄉(xiāng),
有誰在人群里心懷不安?
“有誰在人群里心懷不安?”我是否有資格算得上其中一個(gè)?
從前,村里的老人們常念叨:土地啊,是我們的衣胞,是祖宗留下的肋骨,是一代留給一代最好的財(cái)富,永遠(yuǎn)都不可拋荒,更不能丟棄。如今,常說這話的老人們一個(gè)個(gè)都走了。“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是縣自然資源部門早年寫在某村一面斷壁上的大紅標(biāo)語。它在風(fēng)雨中日漸漫漶和剝蝕,現(xiàn)在已隨著那面殘?jiān)珡氐紫Я耍〈氖且淮爆F(xiàn)代氣息濃郁的摩天大廈。我知道這個(gè)村的土地管理向來混亂,村民時(shí)常侵占公家的土地亂建房屋,膽大的村民不僅互相調(diào)換土地,甚至還將承包經(jīng)營(yíng)的土地賣給城里人蓋別墅。如今,這個(gè)村已成為一個(gè)危房林立的“空心村”,它周邊原來的綠色田野已被若干高檔樓盤覆蓋。
現(xiàn)代的農(nóng)村人都知道土地的金貴,但熱愛土地的人們卻無法守住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遺產(chǎn)。有人說,單純的種植業(yè)只能解決溫飽,土里刨食、靠天吃飯永遠(yuǎn)實(shí)現(xiàn)不了小康目標(biāo),虧本的生意無人做,讓土地變?yōu)橹靛X的商品房才有希望。沒有人會(huì)拒絕擺在眼前的真金白銀,何況那些長(zhǎng)年為錢所困而急于過上富足生活的人們。
也許是意識(shí)到了土地問題的嚴(yán)重性,如今,國(guó)家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戰(zhàn)略層面上又提出了實(shí)施“兩區(qū)”保護(hù)的政策,即對(duì)糧食生產(chǎn)功能區(qū)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區(qū)進(jìn)行重點(diǎn)保護(hù)。
駱一禾在《生為弱者》一詩中如是謙遜地表白:“我的心是樸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后人將它作為詩人的墓志銘,我倒覺得這詩句應(yīng)該作為警示語,刻在那些破碎的、傷痕累累的大地上。
童年與河流
童年是人生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shí)代。因其天真爛漫,哪怕偶然也有一閃而逝的邪念,但它也一樣出于無知的純真考量。童年的記憶是我們一生的追求。羅蘭·巴特在《西南方向的光亮》一文結(jié)尾寫道:“童年是我們認(rèn)識(shí)一個(gè)地區(qū)的最佳途徑。實(shí)際上,只有童年才談得上家鄉(xiāng)。”我們畢生尋找的不是伊甸園,而是那個(gè)叫作“童年”的故鄉(xiāng)。許多寫作者都將在紙上找到還鄉(xiāng)、返回童年的途徑當(dāng)作隱秘的動(dòng)力。張煒將“童年”作為“文學(xué)的8個(gè)關(guān)鍵詞之一”列在首位,他說:“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潛藏著一個(gè)人終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開和放大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長(zhǎng)度。”他甚至斷言,具有特殊力量的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難怪富有四海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心心念念思?xì)w故里。“故鄉(xiāng)不僅是他的病,更是他的藥”,李修文在《偷路回故鄉(xiāng)》中寫道:“唯有回到故鄉(xiāng),人君才重新做回了人子。”
令人不安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丟掉童年之前就丟失了故鄉(xiāng)——即使他們像唐哀帝時(shí)丙寅科狀元裴說那樣“亂中偷路回故鄉(xiāng)”,恐怕也只能與張信哲悲傷的吟唱相似:我們?cè)僖不夭蝗チ耍瑢?duì)不對(duì)?
簡(jiǎn)媜說:“浪漫地想,每個(gè)人的童年都應(yīng)該在河邊長(zhǎng)大才對(duì),如果沒有,不是河拋棄我們,就是我們背叛河。一塊土地,從農(nóng)耕開發(fā)成都市,首先鏟除的必然是山丘與河川,不懂得保留大自然的城市,丑得驚人。”
作為長(zhǎng)江和黃河邊孕育的民族,我們確實(shí)應(yīng)當(dāng)在河畔長(zhǎng)大和生活,哪怕只是一條無名之河。我擔(dān)任縣水務(wù)局局長(zhǎng)的那幾年,正趕上國(guó)家治理江河的大好政策。我們縣境內(nèi)的“一江八河”,因?yàn)橛懈骷?jí)政府的資金支持,全部都進(jìn)行了有效治理。而在治理過程中,修復(fù)重建那些業(yè)已被農(nóng)村建房侵占的河堤,落實(shí)退田還湖、退耕還林和水源保護(hù)區(qū)禁用農(nóng)藥化肥、禁養(yǎng)殖等重大措施,確實(shí)花費(fèi)了頗多資金和心血。但這種付出是值得的,教訓(xùn)尤其應(yīng)該汲取。亡羊補(bǔ)牢,為時(shí)未晚,盡管江河恢復(fù)生機(jī)與靈氣還需要時(shí)間和持續(xù)的保護(hù),但逐步建立健全的河長(zhǎng)制等水政已初見成效。

凌之鶴 本名張凌,詩人、評(píng)論家。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昆明市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協(xié)會(huì)理事,純文學(xué)民刊《滇中文學(xué)》主編,大益文學(xué)院簽約評(píng)論家,16歲發(fā)表處女作。常用筆名有荊棘鳥、安蘭、凌之鶴、小李伊人、西門吹酒、林潔冰。著有《醉千年:與古人對(duì)飲》《獨(dú)鶴與飛》《為文學(xué)祭春風(fēng)》。

作者: 凌之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