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9 09:34 來源:昭通日?qǐng)?bà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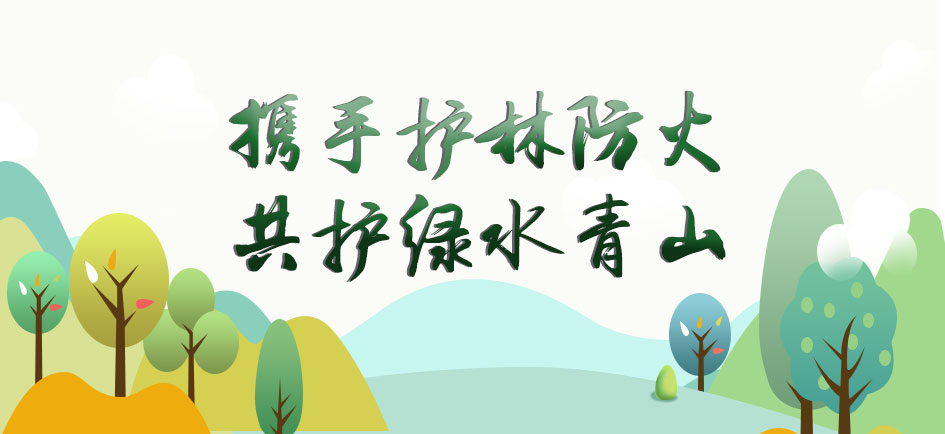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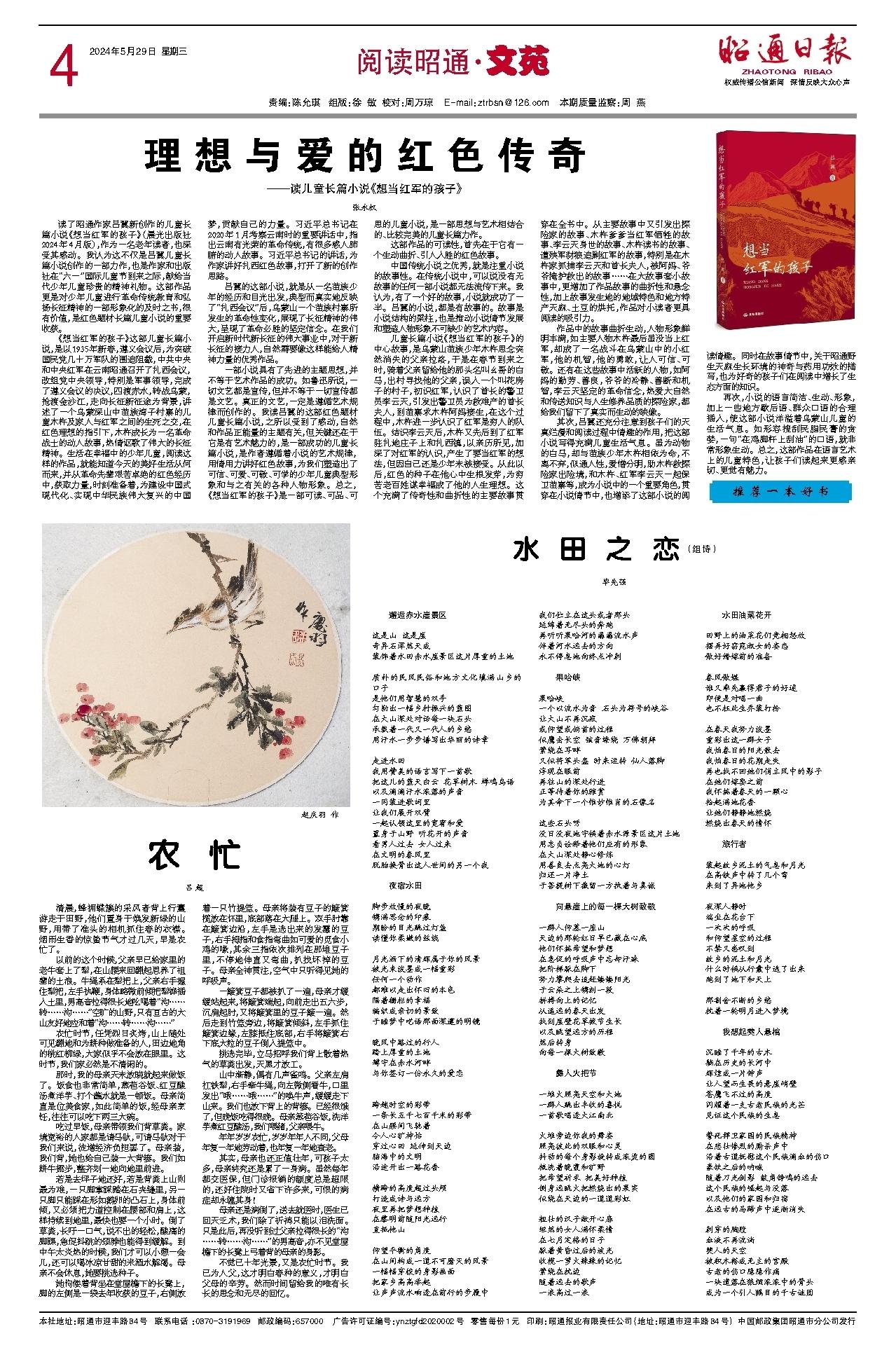
讀了昭通作家呂翼新創(chuàng)作的兒童長(zhǎng)篇小說《想當(dāng)紅軍的孩子》(晨光出版社2024年4月版),作為一名老年讀者,也深受其感動(dòng)。我認(rèn)為這不僅是呂翼兒童長(zhǎng)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部力作,也是作家和出版社在“六一”國(guó)際兒童節(jié)到來之際,獻(xiàn)給當(dāng)代少年兒童珍貴的精神禮物。這部作品更是對(duì)少年兒童進(jìn)行革命傳統(tǒng)教育和弘揚(yáng)長(zhǎng)征精神的一部形象化的及時(shí)之書,很有價(jià)值,是紅色題材長(zhǎng)篇兒童小說的重要收獲。
《想當(dāng)紅軍的孩子》這部?jī)和L(zhǎng)篇小說,是以1935年新春,遵義會(huì)議后,為突破國(guó)民黨幾十萬軍隊(duì)的圍追阻截,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云南昭通召開了扎西會(huì)議,改組黨中央領(lǐng)導(dǎo),特別是軍事領(lǐng)導(dǎo),完成了遵義會(huì)議的決議,四渡赤水,轉(zhuǎn)戰(zhàn)烏蒙,搶渡金沙江,走向長(zhǎng)征新征途為背景,講述了一個(gè)烏蒙深山中苗族灣子村寨的兒童木杵及家人與紅軍之間的生死之交,在紅色理想的指引下,木杵成長(zhǎng)為一名革命戰(zhàn)士的動(dòng)人故事,熱情謳歌了偉大的長(zhǎng)征精神。生活在幸福中的少年兒童,閱讀這樣的作品,就能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從何而來,并從革命先輩艱苦卓絕的紅色經(jīng)歷中,獲取力量,時(shí)刻準(zhǔn)備著,為建設(shè)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貢獻(xiàn)自己的力量。習(xí)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月考察云南時(shí)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云南有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動(dòng)人故事。習(xí)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作家講好扎西紅色故事,打開了新的創(chuàng)作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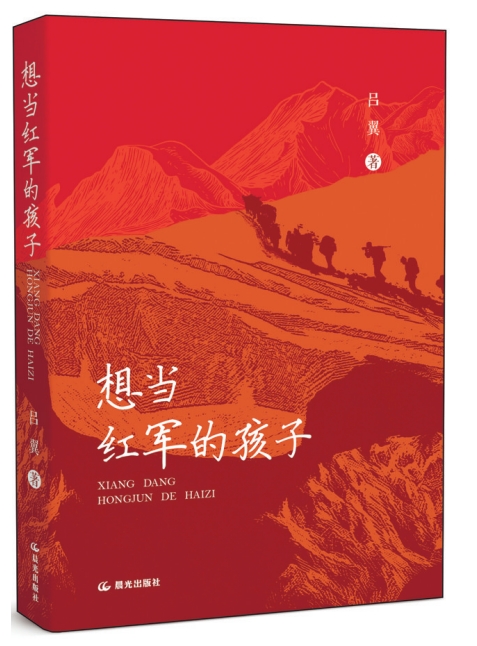
呂翼的這部小說,就是從一名苗族少年的經(jīng)歷和目光出發(fā),典型而真實(shí)地反映了“扎西會(huì)議”后,烏蒙山一個(gè)苗族村寨所發(fā)生的革命性變化,展現(xiàn)了長(zhǎng)征精神的偉大,呈現(xiàn)了革命必勝的堅(jiān)定信念。在我們開啟新時(shí)代新長(zhǎng)征的偉大事業(yè)中,對(duì)于新長(zhǎng)征的接力人,自然需要像這樣能給人精神力量的優(yōu)秀作品。
一部小說具有了先進(jìn)的主題思想,并不等于藝術(shù)作品的成功。如魯迅所說,一切文藝都是宣傳,但并不等于一切宣傳都是文藝。真正的文藝,一定是遵循藝術(shù)規(guī)律而創(chuàng)作的。我讀呂翼的這部紅色題材兒童長(zhǎng)篇小說,之所以受到了感動(dòng),自然和作品正能量的主題有關(guān),但關(guān)鍵還在于它是有藝術(shù)魅力的,是一部成功的兒童長(zhǎng)篇小說,是作者遵循著小說的藝術(shù)規(guī)律,用情用力講好紅色故事,為我們塑造出了可信、可愛、可敬、可學(xué)的少年兒童典型形象和與之有關(guān)的各種人物形象。總之,《想當(dāng)紅軍的孩子》是一部可讀、可品、可思的兒童小說,是一部思想與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比較完美的兒童長(zhǎng)篇力作。
這部作品的可讀性,首先在于它有一個(gè)生動(dòng)曲折、引人入勝的紅色故事。
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說之優(yōu)秀,就是注重小說的故事性。在傳統(tǒng)小說中,可以說沒有無故事的任何一部小說都無法流傳下來。我認(rèn)為,有了一個(gè)好的故事,小說就成功了一半。呂翼的小說,都是有故事的。故事是小說結(jié)構(gòu)的梁柱,也是推動(dòng)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和塑造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藝術(shù)內(nèi)容。
兒童長(zhǎng)篇小說《想當(dāng)紅軍的孩子》的中心故事,是烏蒙山苗族少年木杵思念突然消失的父親拉洛,于是在春節(jié)到來之時(shí),騎著父親留給他的那頭名叫ㄠ哥的白馬,出村尋找他的父親,誤入一個(gè)叫花房子的村子,初識(shí)紅軍,認(rèn)識(shí)了首長(zhǎng)的警衛(wèi)員李云天,引發(fā)出警衛(wèi)員為救難產(chǎn)的首長(zhǎng)夫人,到苗寨求木杵阿媽接生,在這個(gè)過程中,木杵進(jìn)一步認(rèn)識(shí)了紅軍是窮人的隊(duì)伍。結(jié)識(shí)李云天后,木杵又先后到了紅軍駐扎地莊子上和扎西鎮(zhèn),以親歷所見,加深了對(duì)紅軍的認(rèn)識(shí),產(chǎn)生了要當(dāng)紅軍的想法,但因自己還是少年未被接受。從此以后,紅色的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fā)芽,為窮苦老百姓謀幸福成了他的人生理想。這個(gè)充滿了傳奇性和曲折性的主要故事貫穿在全書中。從主要故事中又引發(fā)出探險(xiǎn)家的故事、木杵爹爹當(dāng)紅軍犧牲的故事、李云天身世的故事、木杵讀書的故事、遭殃軍豺狼追剿紅軍的故事,特別是在木杵家抓捕李云天和首長(zhǎng)夫人,被阿媽、爺爺掩護(hù)救出的故事……在大故事套小故事中,更增加了作品故事的曲折性和懸念性,加上故事發(fā)生地的地域特色和地方特產(chǎn)天麻、土豆的烘托,作品對(duì)小讀者更具閱讀的吸引力。
作品中的故事曲折生動(dòng),人物形象鮮明豐滿,如主要人物木杵最后雖沒當(dāng)上紅軍,卻成了一名戰(zhàn)斗在烏蒙山中的小紅軍,他的機(jī)智,他的勇敢,讓人可信、可敬。還有在這些故事中活躍的人物,如阿媽的勤勞、善良,爺爺?shù)睦潇o、善斷和機(jī)智,李云天堅(jiān)定的革命信念,熱愛大自然和傳送知識(shí)與人生修養(yǎng)品質(zhì)的探險(xiǎn)家,都給我們留下了真實(shí)而生動(dòng)的映像。
其次,呂翼還充分注意到孩子們的天真爛漫和閱讀過程中情趣的作用,把這部小說寫得充滿兒童生活氣息。雖為動(dòng)物的白馬,卻與苗族少年木杵相依為命,不離不棄,似通人性,愛憎分明,助木杵救探險(xiǎn)家出險(xiǎn)境,和木杵、紅軍李云天一起保衛(wèi)苗寨等,成為小說中的一個(gè)重要角色,貫穿在小說情節(jié)中,也增添了這部小說的閱讀情趣。同時(shí)在故事情節(jié)中,關(guān)于昭通野生天麻生長(zhǎng)環(huán)境的神奇與藥用功效的描寫,也為好奇的孩子們?cè)陂喿x中增長(zhǎng)了生態(tài)方面的知識(shí)。
再次,小說的語言簡(jiǎn)潔、生動(dòng)、形象,加上一些地方歇后語、群眾口語的合理插入,使這部小說洋溢著烏蒙山兒童的生活氣息。如形容搜刮民脂民膏的貪婪,一句“在雞腳桿上刮油”的口語,就非常形象生動(dòng)。總之,這部作品在語言藝術(shù)上的兒童特色,讓孩子們讀起來更感親切、更覺有魅力。

作者:張永權(q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