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2 09:00 來源:昭通日報(bà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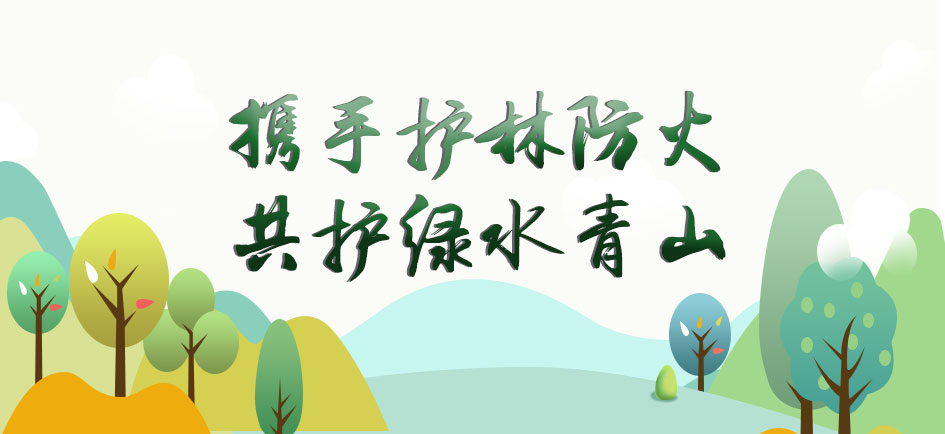

起伏的山勢,決定了道路的曲折。
從昭陽城區(qū)到蘇甲鄉(xiāng),之前只有一條橫穿舊圃、灑漁兩個(gè)鎮(zhèn)的主道。2017年,從城區(qū)到大山包的一級公路通車后,去蘇甲可以借道而行。一個(gè)多小時(shí)的車程,高速飛馳和坡陡彎急無縫銜接,是一種奇妙的感受。對藏在大山里的蘇甲來說,多了一條路,就有了更多的選擇。
可以確定,蘇甲,這是個(gè)正在被時(shí)代打開的山區(qū)鄉(xiāng)。
為夢想培土
暮春的早上,海拔2000多米的蘇甲依然有涼意。春天不像秋冬那般枯寂。大地上的生機(jī)聞風(fēng)而動(dòng),蓄勢待發(fā)。這次我們要采訪的對象是一位種糧人。一個(gè)長于土地、外出打過工、經(jīng)過商,最后又回歸土地的蘇甲人。今年48歲的王開華應(yīng)約從地里趕到鄉(xiāng)政府,他的太陽帽上,有陽光和汗水交織的味道。這種味道,直截了當(dāng)?shù)刈尨蠹腋惺艿搅舜喝胀恋厣戏泵Φ臍庀ⅰ?/span>
20世紀(jì)90年代,王開華因家庭困難,初二沒讀完就輟學(xué)回家。那個(gè)時(shí)代,對很多如王開華一樣的農(nóng)村娃來說,求學(xué)是一種奢侈的夢想。作為家里的老大,王開華自然而然把求學(xué)機(jī)會(huì)讓給了弟弟、妹妹。對于念過書,眼界越過大山的王開華,已經(jīng)沒有安心閑賦在家的可能了。當(dāng)年農(nóng)村多數(shù)沒上過學(xué)的男孩,到了20歲左右,順理成章娶妻生子,承襲父輩的生活方式。腦子里有點(diǎn)墨水,精神世界不再是炊煙裊裊、雞鳴狗叫的王開華,起伏的大山和箐溝里的水,已經(jīng)留不住這個(gè)毅然想走出去的人了。
長時(shí)間被一個(gè)小地方捆綁的人,一旦掙脫了這種束縛,就會(huì)誤認(rèn)為全世界都和自己有關(guān)系。北京、三亞、廣州這些大都市是王開華的首選之地,但沒有生存技能,沒有明確的目標(biāo),全憑骨子里那股空蕩蕩的豪氣,注定只能到處漂泊。為了生存,賣苦力干累活成了生存下去的方式。“漫無目的的日子,每天睜開眼就很迷茫。”王開華回憶說。
2000年,在河北一家塑料廠,王開華終于停下步伐,心也安定下來了。老實(shí)本分、勤學(xué)苦干的他很快就被塑料廠老板重用,從一名基層工人搖身一變成為管理者,待遇很快就和工友們區(qū)別開來。人為什么要拼命,為什么要改變,說到底,就是為了和以前的自己與周圍的人區(qū)別開來。
“2002年,我?guī)е鴥扇f七千多元回村里。”王開華的眼里有酸楚、艱辛和驕傲,更多的是美好的憧憬。
“有點(diǎn)錢了,肯定不會(huì)待在老家,想大干一場。”王開華的話語里有豪氣,但很快,就被他臉上的苦笑替代了。筆者與他作為同齡人,明白這種情緒變化,背后一定有更曲折的人生故事。
戴著村里第一個(gè)萬元戶的頭銜,王開華又出發(fā)了,和上次截然不同的是,第一次出門是迷茫的,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撞到什么算什么,這次目標(biāo)清晰,他決定到昭通火車站開館子,當(dāng)老板。2004年,王開華說干就干,租房子、購餐具,餐館在火車站很快開張。
火車站就是個(gè)大容器,不同腔調(diào)、不同經(jīng)歷、不同目的、不同故事的人,都會(huì)在這里匯集。王開華看中的就是人流量,人氣就是最大的流量。當(dāng)然,人越多越復(fù)雜。館子的生意如王開華期待的那樣,每天食客來來往往,空著肚子來,留下鈔票走。
“錢確實(shí)好掙,那時(shí)一年有10多萬元收入,但是開銷太大了。”王開華說。他為人仗義,蘇甲老鄉(xiāng)只要到火車站坐車,都會(huì)去他餐館里坐坐。他是村里率先出來當(dāng)老板的,鄉(xiāng)鄰來了不可能不吃飯,遇上趕不上火車班列的就留宿家里。“每天都有六七個(gè)老鄉(xiāng)來餐館里吃飯。”王開華又是苦笑,“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給錢也不能收,大家都不容易。”
王開華的餐館自然而然成了鄉(xiāng)鄰的臨時(shí)驛站。家鄉(xiāng)人到這里的開支雖大,這是以鄉(xiāng)情為前提的,某種意義上,是情誼的儲存。“表面上熱熱鬧鬧,生意興隆,其實(shí),反而欠賬。”王開華笑著說。
一地荊棘的現(xiàn)實(shí)在不斷磨損著王開華創(chuàng)業(yè)的激情。城市這個(gè)看似到處都充滿機(jī)會(huì)的地方,實(shí)則,很難成為一個(gè)兩手空空的農(nóng)村孩子的夢里水鄉(xiāng)。王開華曾經(jīng)憧憬的美麗花園到底在哪?落敗回鄉(xiāng),王開華是無法接受的,至少還沒到只有回家的單項(xiàng)選擇。
后來,王開華借助積累的人脈,承攬修溝筑坎、房屋建設(shè)等基礎(chǔ)性小工程,繼續(xù)繪制著自己追夢的藍(lán)圖。幾年打拼,積累了70多萬元,王開華又有了新想法。
大地的色彩
被春風(fēng)喚醒的大地,散發(fā)出一種特殊的氣味。這種混合著泥土、山風(fēng)、勃發(fā)的味道,讓王開華頓感久違的親切。當(dāng)然,對于一個(gè)用30年在不同城市、不同領(lǐng)域摸爬滾打才醒悟的人而言,這種氣味不單是氣體那么輕飄,更像一種不可抗的召喚——回鄉(xiāng)。
每個(gè)年齡段對成功的定義不大相同,40歲前,發(fā)家致富是最高理想。到了知命之年,王開華突然領(lǐng)悟到,成功已不再是個(gè)人有多少錢的個(gè)體行為,而是讓一群有關(guān)系的人都能過上好日子。要實(shí)現(xiàn)這個(gè)想法,回家種地就是最好的選項(xiàng)。
蘇甲鄉(xiāng)海拔2070米,境內(nèi)山巒起伏,溝壑交錯(cuò),地勢西高東低,立體氣候特征突出,主產(chǎn)玉米、馬鈴薯、蕎、麥等傳統(tǒng)農(nóng)作物。近年來,在當(dāng)?shù)攸h委、政府的引領(lǐng)下,少數(shù)敢于率先“吃螃蟹”的人在這里種植冷涼蔬菜獲得成功。晝夜溫差大,養(yǎng)分沉積度高的蔬菜是蘇甲獨(dú)有的自然稟賦,這種得天獨(dú)厚的資源優(yōu)勢讓王開華決心回鄉(xiāng)種植蔬菜。
“我不是盲目地干,我去過很多地方考察過,如何種植,田間管理和銷售我都反復(fù)斟酌了,去年試種成功后,我今年決定大干一場。”說這話時(shí),王開華的拳頭緊緊握住,篤定的表情和語氣,讓筆者看到了他深思熟慮的決心。2024年,他流轉(zhuǎn)了280畝土地,熱火朝天地干起來。
這片曾經(jīng)讓王開華千方百計(jì)逃離的土地,如今,卻將成為他夢想的舞臺。
“我只種紫芥蘭,從育苗、移栽到采收只要2個(gè)月左右,只要種出來,銷路一點(diǎn)不愁……”
從王開華充滿干勁的眼神里,筆者似乎看到,勤勞善良的蘇甲人民正在把色彩斑斕的希望根植在黃色大地上,然后,結(jié)出夢想的碩果。

通訊員:嚴(yán)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