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8 14:41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老叔放下斧頭,抬起手臂用衣袖擦了擦額頭的汗水,笑著對我說:“房子蓋好了,老房子剩下的柱子和架模板沒地方用,就把它們劈了當(dāng)柴堆著。”看著堆得整整齊齊、刀口清晰平整的柴垛,我由衷稱贊:“老叔,幾十年沒上山砍柴了,這劈柴的刀法功力還是沒退步啊!”老叔笑道: “自從用上電、液化氣,都不燒柴了,就當(dāng)作練練手。”
老叔的話勾起了我的回憶。鄉(xiāng)村的生活,總有那么多的記憶叫人難忘,比如這柴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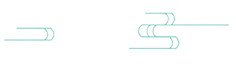

從我記事起,父母親每天的生活程序中,除了耕田種地、采茶煮飯、喂養(yǎng)家禽外就是砍柴。那時村里剛通了電,電是從十多公里外的一座小水電站提供的。小河水流量小,限制了電站發(fā)電量。電的主要用途是照明,家里20瓦的電燈泡,常常忽閃忽閃的。村里做飯只能靠柴火,柴火進(jìn)灶,炊煙裊裊,煙火味就是家的味道。于是,村里家家戶戶都要砍柴,相互間還在默默地攀比,哪家的柴圓滑、長短一致,哪家的柴垛堆得比山高比河長,哪家就最富有,最受鄰居尊敬。
每年初冬,全村人抓住農(nóng)閑時節(jié),奔赴十多公里外自家產(chǎn)權(quán)林準(zhǔn)備一年的柴了。雞叫頭遍,村民們就起床出發(fā)。根據(jù)約定俗成的分工,我們這些小孩子上午放學(xué)后,要負(fù)責(zé)燒火做飯,并去半路上給大人送午飯。沿途,大人們背著大捆大捆的柴回來,遇到孩子接過盛著午飯的餐具,往路邊草地上隨便一坐,一家人開始了幸福的吃飯時光。那時家里下飯吃的,是自家腌制的腌菜、蘿卜,最好的伙食則是雞蛋炒飯,雖然簡單,但一家人吃得不亦樂乎。我記得,有一天父親腰疼的老毛病發(fā)作了,母親獨自去砍柴。中午送飯的路上,我沒有看見母親的身影。我加快腳步往山里走,終于看到了母親。母親背著的柴比往常多了很多,重重地壓在母親身上,母親緩慢地移動著腳步。看到我,母親順著路邊小土坎,艱難地放下柴,長長地呼吸了一下,雙手使勁捶著腰。吃飯的時候,母親總是瞄著不遠(yuǎn)處的幾棵松樹發(fā)呆。吃完最后一口飯,母親提起砍刀,就跑進(jìn)松樹林里去。松樹林里,“乒乒乓乓”的砍樹聲還沒維持多久,就響起一陣“抓偷柴賊”的叫罵聲。母親慌慌張張地沖出松樹林,拉上我就跑。為了多砍點柴,母親慌忙中丟下了砍的柴和砍柴用的砍刀,還背了“偷柴賊”的名聲,母親為此懊惱了好長一段時間。我知道,那天母親想“偷”的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柴,而是一家人一年燒火、做飯的“責(zé)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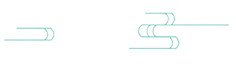

樹成了柴,柴點燃火,火燒了飯,飯喂養(yǎng)了我們。炊煙裊裊,日子如梭。而今,沼氣、電飯鍋、電磁爐、燃?xì)庠睢颁佁焐w地”,快遞公司、外賣召之即來,柴垛的“光輝歷程”早已悄悄躲進(jìn)了記憶深處。不少地方打出“柴火雞”的招牌,借著柴火燒菜的名頭,其實用的是現(xiàn)代技術(shù)壓制出的機制炭,人們卻依然趨之若鶩。其實,大家都知道,砍柴做飯的年代早已遠(yuǎn)去,“柴火雞”帶給我們的是回憶,是一代人對“家”的解讀和堅守。
來源:楊永平(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xié)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