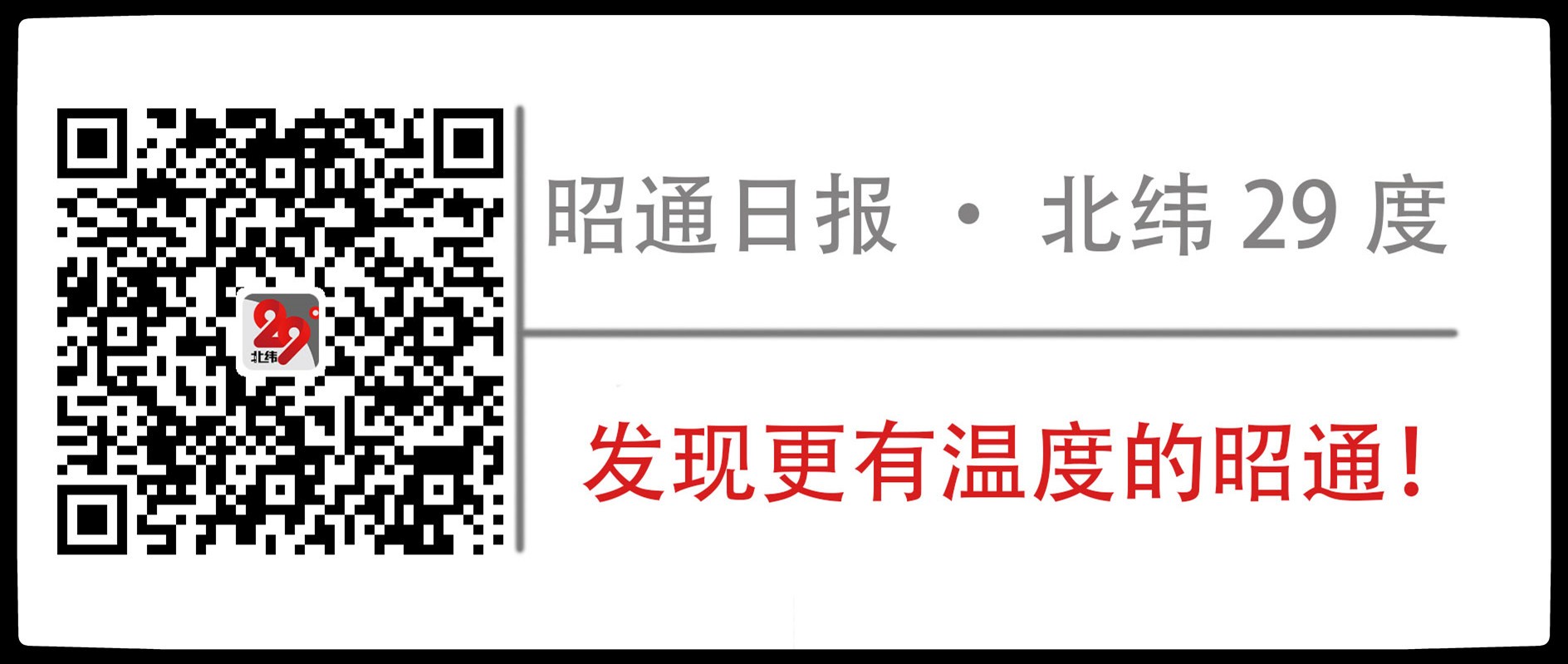2019-12-03 15:21 來源:昭通創(chuàng)作
胡永堅? ? ?70后,生于云南昭通。種過地,當過鄉(xiāng)村教師,現供職于昭通文學藝術家創(chuàng)作中心,市委下派到巧家縣藥山鎮(zhèn)大村村擔任脫貧摘帽督導員。喜用文字和鏡頭記錄生活的點點滴滴。
對于巧家藥山的大村村來說,今年是干旱之年。聽說大村村三鍋樁社、煤炭灣社沒有水喝了,原來接通的水管滴水未有,村民們不得不到三四公里之外的山溝里背水吃。這涉及到兩個社60余戶人家的飲水問題,刻不容緩。村支書楊忠發(fā)在會上與大伙商量,決定去水源地看個究竟。
一大早,村支書楊忠發(fā)、村委委員劉啟榮、扶貧工作隊員張懋劍和我一行4人,坐著村委委員劉委員私人的微型車,上山了。一進土路,路面到處坑坑洼洼,大石頭、小石頭鑲嵌在泥土路,微型車一路顛簸,發(fā)出吱吱嘎嘎聲響,漫天的塵土像一條土龍,緊緊咬住車尾不放。劉委員熟練的把控著方向盤,面包車左彎右拐的避讓著路面的坑塘或凸起的石頭。我們緊緊的抓住扶手,但時不時人還是會被騰空離開座位,被顛簸得暈頭轉向的。村支書笑著說道,走這條路,就像在跳迪斯科。被他這么一說,我們都笑了,暫時忘卻了暈車的惡心。
微型車跳了一個多小時的迪斯科,不知繞了多少彎,不知過了多少坎,在一個陡坡前停了下來,我們下車,與煤炭灣的社長李順安、村民李國忠等3人匯合,開始往山上攀爬。路越來越窄,也越來越陡,到處是荊棘。村民李國忠經驗豐富,手持一把砍刀,在前面劈荊斬刺,為我們開道。不管怎么防范,那些帶刺兒的枝條或葉子,總是會穿透我的牛仔褲或衣袖里,扎得皮膚生疼生疼的。到了正午,我們走到哪,火辣辣的太陽就追到哪,不肯離去。原先還輕快的步伐,漸漸地也變得沉重了,呼吸也越來越急促了。一行人中,楊支書已經五十五歲了,頭發(fā)半百,額頭布滿了歲月的溝壑,高一腳,矮一腳踏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山路沒爬多久,就開始氣喘吁吁的了,臉上滲出細細的汗珠慢慢長大,從臉上滾落在脖頸里,背心也漸漸濕透了。一不小心,他還跌了一跤。沒等攙扶,他爬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土,笑呵呵的說道,歲月不饒人,還是不如當年了!
蓄水池就在眼前。我們幾人合力撬開了蓄水池沉重的水泥蓋。一看,蓄水池基本沒有水,進水管道的水也只有麻線粗細。難怪呀,村民們哪會有水喝?這水進水小,又加上出水口滲水,滴滴噠噠往外漏,當然就沒有水了。我們只有采取土辦法,取些草餅放在池內出水口周圍,壓實,將流走的水引入水池。然后查看蓄水池上方的水源,水慢慢地從泥土里滲出,淌入管子里的水非常的少。我們又重新找了一處從石縫了滲出來的水源,很干凈。我掬了一捧水喝,清涼,甘甜,還行。于是我們決定從這兒再引一條水淌到蓄水池。
費了半天勁,重新排好水管,接了水源,水就順著管道緩緩地流進蓄水池。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疲憊地躺在草甸上。時間過得真快,已經是中午兩點半鐘了。等了一個小時,水終于蓄到了四分一處。可又有意外出現,不見水位再往上漲了,出水管也不見有水。一檢查,才發(fā)現水池四周都在滲水。原來這是個漏水池!咋個辦呢?現在唯一的辦法,就只有直接把水源處的管子和蓄水池出口的管子直接接在起來,不經過蓄水池,暫時先把水引到半山的另一個水池里,先解決吃水問題,下一步再重新維修漏水池。
回到村上,已經夕陽西下。掬水洗臉,我才感覺火辣辣的痛。鏡子里的我,滿臉通紅。盡管之前作了充分的準備,戴了帽子和墨鏡,但仍擋不住紫外線的照射。第二天一大早醒來,我就打電話問了一下李社長飲水的情況。當告知村子的水管已經有水流出來,村民已經吃上水了,一股甘泉也緩緩流進了我的心田。那水是那么的清澈、甘甜,洗去了昨日的疲憊和疼痛,我們踏實了。過了半個月,我的臉和裸露的手臂才恢復過來。雖然痛,但我是值得的。

來源:昭通創(chuàng)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