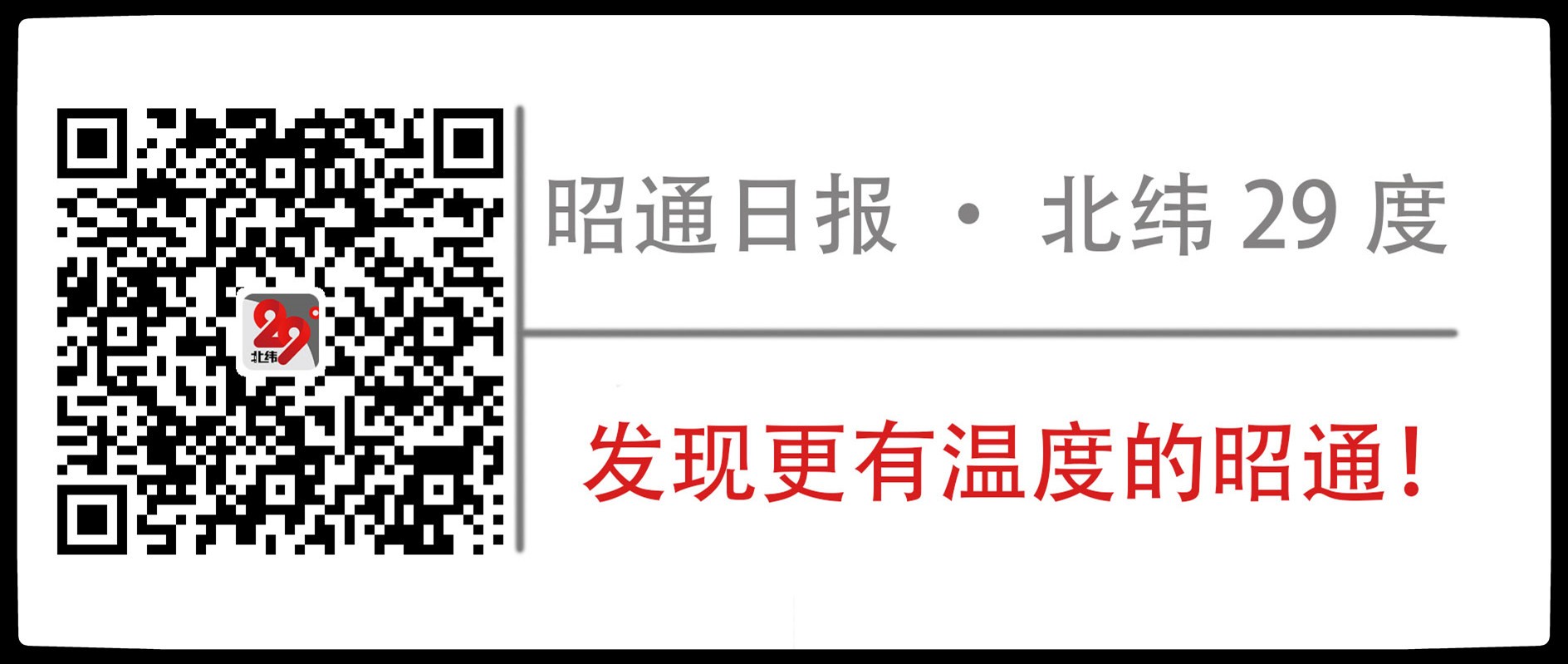2020-04-02 16:36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看到母雞時(shí)我吃了一驚,母雞也愣了一下,然后“咯噠!咯噠!咯咯噠!”地叫著試圖躲開我。它腳上拴著的繩子,被錯(cuò)落交織地現(xiàn)出地面的樹根攔了一下,母雞使勁向前掙,繩子拉成三角形,它也不知道繞回來,一門心思往前跑。我停住,避免其越掙越緊。它終于把攔住繩子的那根細(xì)枝拽斷,繼續(xù)繞著樹跑。大榕樹的根須形成一個(gè)直徑約五六米的圓盤,拴著雞的繩子不夠拉一圈呀。綠葉和枯葉在母雞的腳下翻騰,紅雞冠和黃羽毛閃爍著鮮艷的光芒,證明這是一只“年輕”的母雞。在這個(gè)繁華的大都市里,隱藏著一個(gè)陳舊的社區(qū)。這只拴在樹下的母雞,仿佛被奠定了一個(gè)基調(diào):“我塵封于此,但我依然向前走。”
看到母雞時(shí)我吃了一驚,母雞也愣了一下,然后“咯噠!咯噠!咯咯噠!”地叫著試圖躲開我。它腳上拴著的繩子,被錯(cuò)落交織地現(xiàn)出地面的樹根攔了一下,母雞使勁向前掙,繩子拉成三角形,它也不知道繞回來,一門心思往前跑。我停住,避免其越掙越緊。它終于把攔住繩子的那根細(xì)枝拽斷,繼續(xù)繞著樹跑。大榕樹的根須形成一個(gè)直徑約五六米的圓盤,拴著雞的繩子不夠拉一圈呀。綠葉和枯葉在母雞的腳下翻騰,紅雞冠和黃羽毛閃爍著鮮艷的光芒,證明這是一只“年輕”的母雞。在這個(gè)繁華的大都市里,隱藏著一個(gè)陳舊的社區(qū)。這只拴在樹下的母雞,仿佛被奠定了一個(gè)基調(diào):“我塵封于此,但我依然向前走。”
不確定母雞的主人是誰。坐在不遠(yuǎn)處的那幾個(gè)老人誰都可以站起來說:“這是我的雞。”靈芝造型的亭子,紅褐色,葉片為蓋,遮擋出一片陰涼。老人們?cè)诖驌淇恕K麄兟刈ヅ疲匕l(fā)牌,像是慢鏡頭,沒有任何聲音。廝殺喊叫了多年,如今已到沉寂之時(shí)。
一幢幢墻體斑駁的樓房,露出衰敗之象。業(yè)主為搶占空間,紛紛從陽臺(tái)上“伸出”的鐵護(hù)欄,均已生銹、扭曲,被多年雨水“揉搓”得變了模樣,不再平整。花盆里的鮮花,從鐵欄桿縫隙里“擠”出來,風(fēng)一吹,好似在向人“招手”。
跟其他地方那些動(dòng)輒幾十萬上百萬平方米的小區(qū)比起來,靈芝新村狹窄而簡陋,像“螺螄殼里做道場” 。當(dāng)然,和深圳其他社區(qū)相比,靈芝新村又成了“巨無霸”,就看跟哪兒比。深圳的小區(qū)太小了,有時(shí)一棟樓即一個(gè)小區(qū),若多出個(gè)空中花園,簡直算意外之喜。有人說:“深圳人的腳踏不到地,他們多數(shù)在天上。地面比天空值錢。”
這個(gè)小區(qū)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建成,是深圳最早的小區(qū)之一。那時(shí)寶安區(qū)還叫寶安縣,被排除在特區(qū)之外。一道長長的鐵絲網(wǎng)將潮熱的土地一分為二,網(wǎng)內(nèi)是特區(qū),稱為“關(guān)內(nèi)”,鐵絲網(wǎng)外稱為“關(guān)外”。關(guān)外的人想進(jìn)去,關(guān)內(nèi)的人不想出來。工業(yè)社會(huì)可不管什么鐵絲網(wǎng)內(nèi)和鐵絲網(wǎng)外的,從遠(yuǎn)方“滾滾”襲來。水稻在田地里一年一茬,收割后大地一片干凈。轉(zhuǎn)眼之間,樓群從“關(guān)內(nèi)”蔓延到“關(guān)外”,長出來,沒人“收割”它們。它們“賴著”不再走,和“關(guān)內(nèi)”的樓房遙遙相望,大家都一個(gè)模樣,分不清彼此。
我進(jìn)入靈芝新村,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在時(shí)光博物館里,歲月“雕刻”的事物一一展現(xiàn)在我的面前。一部分已“雕刻”完畢,一部分正在“雕刻”中,哪里有什么完畢?
一位老年婦女坐在二樓的露臺(tái)上,俯視著我,光線打在她毫無表情的臉上,皺紋“鐵水澆鑄”一般,讓她的“無表情”顯得很是堅(jiān)定。除了我,她見過了太多的人,心里也許默默在計(jì)數(shù),也許熟視無睹?從她腳下走過的人再也沒有回來。我只瞟了她一眼,不再看第二眼。萬一她忽然笑起來呢!我相信“萬物有靈”,所有沉寂的事物被打量的時(shí)間長了,都會(huì)“靈性復(fù)活”的。
一個(gè)穿著制服的清潔工人,是個(gè)瘦高的男人。他左手握掃帚,右手持手機(jī),貼在耳邊。我遠(yuǎn)遠(yuǎn)看著他的那個(gè)姿勢(shì),從他身邊走過去,回頭望,還是那個(gè)姿勢(shì),一點(diǎn)沒變。他貌似什么都沒說。說什么都和沒說一樣。一個(gè)騎著共享單車的年輕人,直愣愣迎面而來,兩條腿像走路一樣地蹬著。從他的眼神里面我看到了自己。好奇怪,莫非他是我的一個(gè)“分身”?
每棟樓一樓的窗戶上幾乎都會(huì)拉出一條繩子,拴在大樹上,上面晾著衣服。遙望一大片,近看一條線。從衣物可以判斷出這家有老有少。有的衣服圖案是小熊維尼,有的是中山裝,在風(fēng)中擺來擺去,好像人還在衣服里面一樣。向陽的一面,特別光亮,背陰的一面又特別黑。
樹下一個(gè)中年人斜臥在躺椅上,光著腳,翹著二郎腿,手機(jī)放在腿上。他眼睛正對(duì)著屏幕,似乎睡著了,斑駁的光線從樹葉中間滲漏下來,把他“切割”得黑白分明。這一天,我看到的始終是光線下的事物。光線勾勒了它們,凸顯了它們。沒有了光線,事物便進(jìn)入黑夜,全部消失。
石桌零落地?cái)[布在大榕樹下,走一會(huì)兒看見一張。我像是巡視的官員,剛才已經(jīng)跟我們“握過手”的那張石桌,從另一條路上“快步繞到”前面,“假裝”是另外一張石桌,擺出同樣的姿勢(shì)“迎檢”。桌面有一點(diǎn)臟,永遠(yuǎn)擦不干凈的那種臟。我掏出一張手紙,使勁兒去蹭,沒用。紙沒臟,桌也沒凈。桌子一角已掉落,可以劃破不小心的人。石凳也如此,坑坑洼洼的,似麻子的臉。人坐在上面如同延后二十年,“身體瞬間變衰老”。
共約一百棟樓房,被綠色植物包圍著。綠色植物本應(yīng)每年都是新的,但一年四季不停歇地“綠下來”,這種“綠”也顯得“舊”了。樹木有年輪,綠色也有年輪。“蒼老的綠”,一般人看不出來。我能,我甚至看到了綠色植物的“驚喜和哭泣”。
一座巨大的雕塑,女性,奔跑的姿勢(shì),黑色的漆零零星星地掉落。它丟失了手掌,空空的手臂向前擺動(dòng),像殘疾運(yùn)動(dòng)員,身體前傾,仿佛要逃離這片叢林。榕樹太高大了,十幾棵便塑造出叢林一樣的荒涼。不知雕像材質(zhì)如何,塑料的或是鐵石的?我不敢走近去摸。還是擔(dān)心“靈性復(fù)活”。最初它就在這里嗎,還是被遺棄至此?
這么傷心的事,不問也罷。
一棵樹干上寫著“趙春國”三個(gè)字,中間那字也許是“秦”字。我猜測是若干年前,淘氣的孩子刻上去的,已變形。“趙春國”本人在長大,他的名字在樹皮上亦隨之長高、變粗。也許某一天,“趙春國”經(jīng)過這里,一抬頭,發(fā)現(xiàn)名字超過了自己。再想刮下來,已經(jīng)夠不著了。
臺(tái)風(fēng)剛過,小區(qū)里還殘存著“浩劫”的痕跡。一棵巨大的榕樹,樹根完全露出來了,有兩人高,像是巨大的圓盤。新鮮的濕土尚未干透,偶爾掉落下來,土渣上“馱著”螞蟻。樹葉和鋸斷的樹枝已被清理過,整整齊齊排布在地上。另一處,三棵古樹連帶貼著瓷磚的花壇,一起翻到路邊。方方正正的瓷磚上,裂著一條黑色的細(xì)縫兒,像誰用針縫過似的。從倒掉的樹下鉆出一只小貓,白色但臟兮兮的,被風(fēng)一吹,細(xì)毛柔軟地倒向一邊。樹“站著”的時(shí)候,它可以爬上爬下,那是它的“家”。樹倒了,它仍依戀它。莫非,樹倒之后它才來到這里,將其當(dāng)作自己的“家”?就像我,在靈芝新村嶄新的時(shí)候無緣到此,在它“變老”以后卻見到了它。這都是誰的安排呀?
同樣的社區(qū),同樣一座樓挨著一座樓,卻不像其他地方那樣橫平豎直,一眼望到底。它們有時(shí)連成片,有時(shí)相互之間錯(cuò)落開。有三層的,五層的,還有更高的。樓之間或者是樹(樹又千姿百態(tài)),或者是石凳,并沒規(guī)律。街道雖直但不清潔。街道充滿了“情緒”和不確定性,“隱藏著”多種可能。初來者若是膽小的,內(nèi)心定會(huì)產(chǎn)生不安全感。
多年前,我曾一個(gè)人汗流滿面在這個(gè)小區(qū)的幾條街道之間走過,仰著頭,汗水倒灌進(jìn)嘴里。臨街的飯店一個(gè)挨一個(gè),以客家菜為主,由此斷定附近居民客家人居多。作為廣東三大民系之一(其他兩個(gè)為潮汕和廣府),客家人本來就是古代的中原移民,一度受制于土著,如今終有了“反客為主”的根基。悶熱的夏天,我差點(diǎn)迷路。一個(gè)新客家人在找房子。那時(shí)這里就“以舊著稱,每平方米七八千元錢”,是這塊區(qū)域最便宜的房子。今天再走過的時(shí)候,得知“最便宜的已超過五萬元錢一平方米了”。這在我懷舊的情緒上“當(dāng)頭潑了一瓢涼水”。
一個(gè)理發(fā)店里面,模模糊糊地坐著幾個(gè)等待理發(fā)的中老年人。理發(fā)師禿頂,板著臉。看見我,眼睛直直地盯著,仿佛在問:“有什么事嗎?”他不張嘴,我便不好回答,也不能問。他的神情是拒絕問話的。他對(duì)陌生人還有著天然的警惕。那幾個(gè)坐著的,應(yīng)該是常客了,隨著店主的目光,眼睛也直直地盯著我。整個(gè)世界都寂靜,我徘徊了幾分鐘,像個(gè)陌生人一樣落荒而逃。那盯人的目光有點(diǎn)讓人驚悚。
理發(fā)店門口有一鐵籠子,籠中一只黑色的大鳥,大聲地叫著,“吱吱!”“吱吱!”,尖利,單調(diào),顯示著它是這里真正的“主人”,拒絕一切外人。叫聲好難聽呀!
在一個(gè)“來了就是深圳人”的都市,“陌生感”比其他城市更常態(tài)化,不會(huì)成為撐開彼此距離的竹竿。熙來攘往的街道上,沒有一個(gè)熟悉的面孔,誰都神態(tài)自若。熟悉即陌生,陌生即熟悉。這多好,多舒服,沒人打聽你的隱私,穿一件古怪的衣服也沒人側(cè)目,只有穩(wěn)固、封閉的熟人社會(huì),才會(huì)有那樣的眼神。
或許,拒人千里之外的疏離中,含有自以為是的“高貴成分”?
存在這種可能性。當(dāng)年這個(gè)鶴立雞群的小區(qū)矗立于一片片稻田中,照耀在這里的陽光都顯得比其他地方多。居民打開窗戶,可以看到外面嘈雜的街道和逐漸增多的、散亂的工廠。他們是最先“安逸”的一群人。他們一手端水缸,一手拿牙刷,俯視著四面八方匆匆趕來的淘金者沉重的包裹和蛇皮袋子扛在肩上、背在背上的身影。
很快,更新更高的樓蓋起來了,更寬闊的馬路修起來了。更高大的樹木被從鄉(xiāng)下連根拔起,直接“插進(jìn)”樓群中間的空地上。最初的繁華被掩蓋,顯得落落寡歡。而最初入住的那些人,皮膚還沒隨著這種“覆蓋”迅速“發(fā)皺”,他們的自豪仍在。這種自豪,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熠熠發(fā)出光亮。后來者超越他們的只是外在。他們內(nèi)心的“高貴”越來越堅(jiān)實(shí),并沒有變老。
深圳的天空真藍(lán),常年如此。被“扣在”同一個(gè)藍(lán)天下,被稱為新村的地方成了舊村。它背離了這個(gè)城市的大趨勢(shì)。整個(gè)城市朝前走,它停下來。陳舊的一個(gè)社區(qū),不過三四十年,真是滄海一粟,而它是這個(gè)嶄新城市難得的“古董”。住在這里的一部分人,還生活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們是懈怠還是堅(jiān)守?姑且視為堅(jiān)守吧,因?yàn)樗麄兊膱?jiān)守成了這個(gè)城市豐富性的一面,讓二十世紀(jì)和二十一世紀(jì)同時(shí)呈現(xiàn)在外人的面前。這么快的城市建設(shè),不能總是加速。遲早有一天節(jié)奏會(huì)放緩。在他們身后,堅(jiān)守的人會(huì)越來越多。
一個(gè)城市,一個(gè)社區(qū),最重要的是人。摩肩接踵的人、偶爾出現(xiàn)的人是色彩,變幻涂抹著街衢。但在靈芝新村,即使沒有“人氣”,這些古舊的建筑也散發(fā)出一種“態(tài)度”。去外地旅游,見到身形巨大的山,咆哮的大海,它們不需要人類來畫蛇添足,它們的身體就是表情。靈芝新村亦然。時(shí)光仿佛在這里“雕刻出酸甜苦辣”,把每一天每一刻的感受“濃縮在刀片里”,隨著刀刃進(jìn)入物體內(nèi)部。它們每天都在變化,像一個(gè)人偶爾皺眉、咳嗽、打哈欠,它們不是呆板的物體。這些可以忽略了人的建筑,已經(jīng)“動(dòng)起來,成了精”。
小區(qū)的背面有一條河,名新圳河,河寬不過二十米,之前肯定像所有河流一樣,時(shí)枯時(shí)豐,干凈而寧靜,千百年來鮮被打擾。工業(yè)大發(fā)展時(shí)期則變成了臭水溝。經(jīng)過多年治理,今復(fù)干凈。河水不是以前的河水,卻可以“扮演原來的模樣”。河水特別淺,在晨光照射下,一汪一汪地反射著白光。水的腥氣翻騰上來,熏、蒸著岸邊的樹。水中的石塊很干凈,不是天然的石塊,是樓房拆遷后的建筑垃圾,經(jīng)水流常年沖洗后變干凈了,但棱角還在,可以“冒充天然”石塊。時(shí)間一久,是否“天然”便沒人能分辨得清。一群又一群的蜻蜓上上下下、飛來飛去,透明的翅膀反射著太陽的光。河底芳草稀疏,若滿目盈綠,尚需假以時(shí)日。人氣“逼壓”植物氣,它們荒涼不起來。對(duì)于草來說,荒涼即旺盛。
岸邊一座小廟,“蹲”在一棵大樹下。緊挨著的是一垃圾回收站。這種回收站多由來自鄉(xiāng)下的夫妻兩人維護(hù),既當(dāng)清潔工,也能撿一點(diǎn)值錢的東西來賣。回收站相當(dāng)干凈,有的房頂上種上了鮮艷的簕杜鵑,常年“爆炸”出一片粉紅。所謂廟,門面很小,一人多高,循環(huán)播放著低回的歌曲。佛龕上擺著長短粗細(xì)各不相等的香燭、紙錢,盤子里是香蕉、蘋果、石榴等應(yīng)季水果。大紅的桌布鋪展下來,繡著招財(cái)進(jìn)寶觀音、送子老壽星等圖畫,門兩邊貼著極不對(duì)稱的對(duì)聯(lián)。上聯(lián):誠心求保,國泰民安風(fēng)調(diào)雨順;下聯(lián):世界和平,民心安樂。樸素而又可愛的訴求。一個(gè)老年婦女跪在蒲團(tuán)上用粵語說著什么,一句都聽不懂。神佛無所不通,應(yīng)照單全收。若調(diào)皮,開口回應(yīng)她一句亦無不可。她雙手擎著香火,頻繁地叩首。站起來回身看到我,問了一句。我以普通話回之:“沒事,就是好奇,隨便看看。”她以蹩腳的普通話說:“這土地廟已經(jīng)有十九年了,很靈的。”
有河,城市就“活”了。我懷疑“河”以前讀“活”。或許,兩個(gè)字是一個(gè)字。有廟,可安放俗人的心靈。我們都是俗人。
靈芝新村附近還有兩個(gè)公園。一曰新安公園,一曰靈芝公園,可給居民帶來福氣,使其進(jìn)可攻退可守。公園和小區(qū)一樣,由樹木構(gòu)成。人的身體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公園里百分之七十都是樹和寶玉般的水塘。水與水不同,樹與樹又不同。每個(gè)組合都排列出不一樣的姿勢(shì)。新安公園九曲回腸,會(huì)時(shí)不時(shí)地修整一下。趕巧了,兩次去,兩次都在大修。想起小時(shí)候常聽家長教訓(xùn):“你能不能消停一會(huì)兒?安靜即美。”靈芝公園當(dāng)年設(shè)有很多兒童游樂設(shè)施:摩天輪、魔鬼屋之類。“我喜歡那里的叢林小火車和旋轉(zhuǎn)木馬,這兩樣讓人一玩就想微笑”,一位已經(jīng)過了三十歲、依然葆有少女心的女性如是說。她和另一些人,已經(jīng)是成熟的“深(圳)二代”,比上一代更自信,更有屬地感、歸屬感。他們的童年記憶與曾經(jīng)的玩樂設(shè)施緊緊連在一起。他們加入這個(gè)城市后,回身還能看到來路,這是不同于前輩的地方。前輩回身是茫茫的泥濘,他們則看到“一個(gè)旋轉(zhuǎn)的摩天輪”。
靈芝兩字,懷疑是粵語發(fā)音,但我沒問過任何人。心里存著懷疑,不想揭開謎底,像深湖一樣。本地的主政者似乎愿意據(jù)此敷衍故事,于是有了傳說:某一年,靈芝新村里發(fā)現(xiàn)了靈芝,居民還制作了一個(gè)靈芝模型供人參觀。竊以為,這種有靈性的事物只能在偏遠(yuǎn)地方長大,白娘子用它救許仙,要從浙江跑到四川峨眉山。人聲鼎沸的地方,靈芝舒展不開。不過這種敷衍讓人容易接受,我寧愿相信這故事是真的。人心總往好處走,抬頭望天。
我從小區(qū)的正門走進(jìn)去,從側(cè)門走出來,走過三十多年,感覺自己又“迷了”一次路。 作 者??王國華
作 者??王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