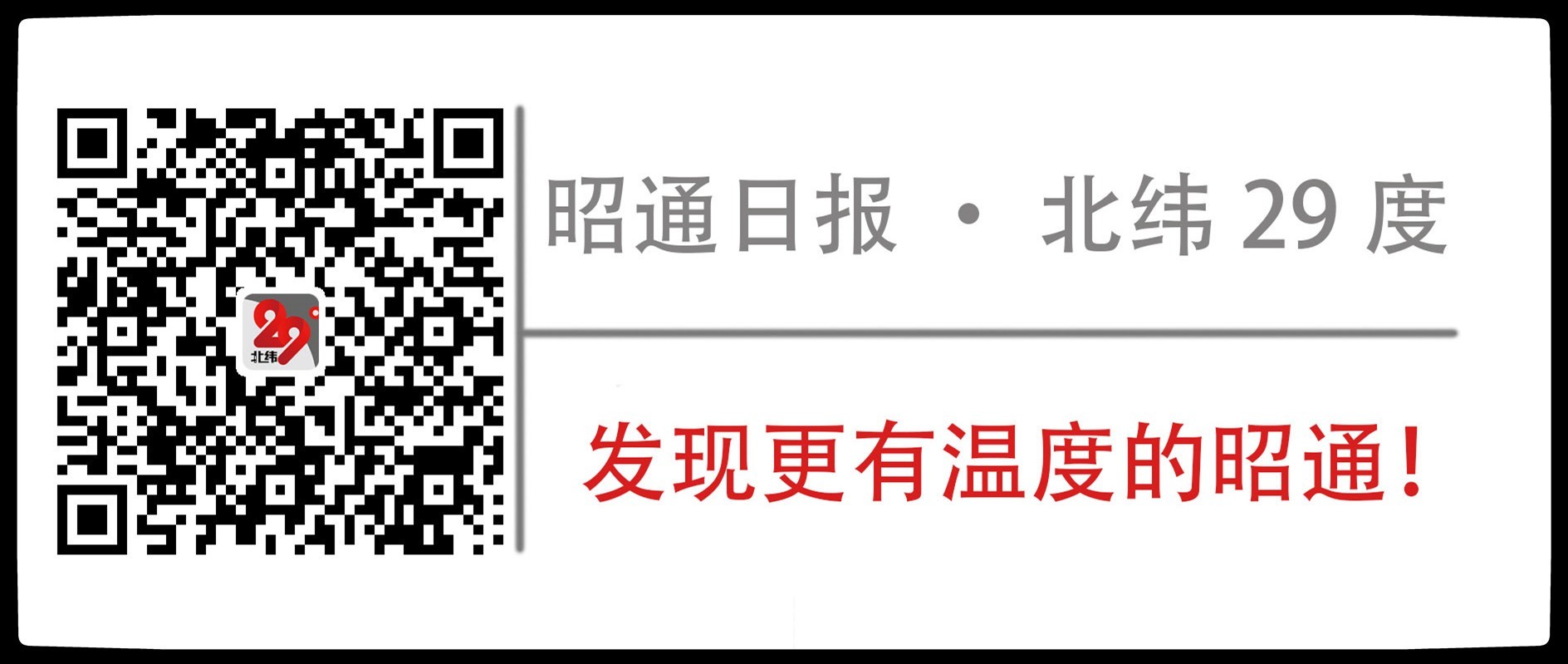2020-04-14 15:26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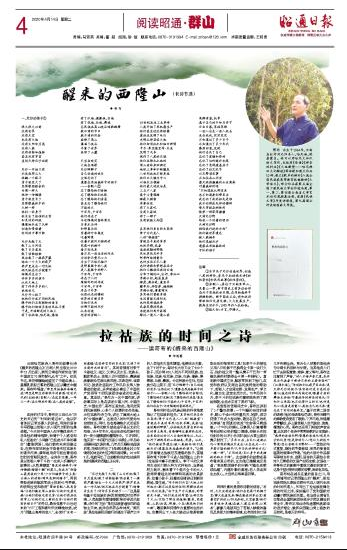
云南哈尼族詩人哥布的敘事長詩《醒來的西隆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榮列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xiàn)禮叢書”之中。初見書名,我仿佛朦朧地望見了中越邊境上、蓋著乳漿般云霧的西隆山正從曦光中醒來。哥布吟唱道:“那里原始森林浩瀚無邊/那里是野生動物快樂的家園/世世代代的(拉祜族)苦聰人/在這里隱藏,一年又一年/在文明的外圍/在人類的邊緣”。
一
在詩的《引》中,哥布定義自己為“歷史的書記員”“時間的筆記本”。他以聽者身份記錄當(dāng)事人的講述,用詩的語言書寫西隆山苦聰人步入現(xiàn)代文明的滄桑進(jìn)程。“今天的中國詩人似乎整體喪失了總體性的精神視野,鐘情于個人感受和私人經(jīng)驗的‘小詞癖’已經(jīng)成為不爭的事實”(霍俊明語),他們朝向未來回避過去,但哥布卻站到金平縣者米拉祜族鄉(xiāng)的者米河岸,謙卑地用詩句回應(yīng)著滔滔汩汩的苦聰民族史。全詩共12章,哥布是以苦聰人李干斗的一生來入手建構(gòu)大敘事的:從芭蕉棚里“獸皮的襁褓中/伸伸懶腰/蹬蹬小腿”的嬰兒,到成為“西隆山最英俊的少男/少女們睡夢中的主角/讓滿山的動物/聞風(fēng)喪膽的獵手”,再到幫助迷路的解放軍戰(zhàn)士找到42號界碑,積極響應(yīng)黨和政府“幫助苦聰人脫離苦海/讓他們搬出深山老林/讓他們定居定耕/讓他們有飯吃有衣穿/讓他們有房住有學(xué)上/讓他們過上新的生活/讓他們擁有幸福日子”的號召,最后受惠于20世紀(jì)末的“155”工程和新時代的精準(zhǔn)扶貧,成為“西隆山高壽的老人”,去世時“沒有一絲遺憾/在臨終空茫的目光里/充滿了對當(dāng)前時光的留戀”。其間穿插有對李干斗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女巫、老族長、解放軍戰(zhàn)士、苦聰人訪問團(tuán)團(tuán)長、彝族瑤族傣族哈尼族壯族同胞、漢語老師、省委書記、脫貧攻堅駐村工作隊隊長等人物事跡的敘述,多聲部地合奏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民族團(tuán)結(jié)奮進(jìn)的壯美樂章。莫言說:“我作為一名中國作家,講故事實際上是在講述中國人民、中國歷史、中國生活”,哥布正是如此,他用宏觀的民族視野、心系個人故事的生命體驗,為拉祜族作詩立傳,講出了滇南大地上的“中國故事”。這是詩人的時代使命與自覺擔(dān)當(dāng),同時,也有海德格爾式的返鄉(xiāng)宿命。哥布的家鄉(xiāng)就在金平縣以北的元陽縣,1964年冬天,他出生在哈尼族村莊的一所火塘燠暖的蘑菇房中。17歲那年,他買到一本《現(xiàn)代漢語小詞典》,3年后命運賜給他漢語的筆,幾年后又賜給他母語的筆,陸續(xù)創(chuàng)作出了《母語》《遺址》《少年情思》《神圣的村莊》等雙語詩集。2019年9月,他就寫出了這部獻(xiàn)給他的拉祜族同胞的《醒來的西隆山》長詩。
二
“厄沙先做了天/做了山川河流/做了日月星辰/做了動物植物/然后栽了一棵葫蘆藤/結(jié)出一個大大的葫蘆/葫蘆里走出一對兄妹/倆兄妹在厄沙授意下/結(jié)婚并生出了/許許多多的孩子……”這是哥布基于拉祜族史詩《牡帕密帕》對世界開端、人類起源和愛情婚配等的神話式敘事,詩中的“厄沙”是拉祜族普遍信仰的造物主天神,統(tǒng)帥自然界各種神靈,“倆兄妹”是拉祜族民間盛行的誕生于葫蘆之中的人類祖先扎笛和娜笛,他倆結(jié)為夫妻,生下9對子女,每對長大后又生了900個孩子,厄沙將900人劃為不同的民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漢族、白族、傣族、傈僳族、壯族、彝族。分完民族分住處,拉祜族分在山梁子,但“厄沙陶醉于/自己創(chuàng)造的歡樂/全然忘記了/遺落在原始森林中的孩子/——苦聰人/忘了賜給他們食物/忘了賜給他們衣物/忘了賜給他們房屋/甚至忘了賜給他們/萬能的火/千百年,千百年/他們存在于/與世隔絕的密林深處。”
哥布同時也從民族遷徙的科學(xué)角度指認(rèn)了拉祜族的祖先:“其實他們來自西北高原/源于古代羌人/人稱‘鍋搓蠻’/曾經(jīng)在豐美的草原/放牧羊群,或者/追逐狡黠的野狼”,拉祜族先民曾在西北地區(qū)的黃土高原、青海湖畔過著游牧生活,后來南遷過四川入云南的瀾滄江、元江、紅河下游兩岸的山林棲息、寄居。從此,“他們被世界遺忘/被人類拋棄/他們是被厄沙/遺落在原始森林的孩子。”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被厄莎遺落的孩子,緊隨哥布筆下的李干斗進(jìn)入他西隆山上的卡(拉祜語中寨子的意思)。李干斗的父親用古老的刀耕火種方式種包谷,當(dāng)耕地肥力耗盡,意味著下個春天全卡的大人就將背著祖先的神牌和簡易的農(nóng)具家具、拉著小孩子、趕著老母豬游遷到新的耕地、居住地,“對于他們而言/大地上任何地方/都不過是臨時住所/那顆流浪的心/無處安居。”由于生產(chǎn)方式落后,時常家無斗糧,“他們把生的希望/全部交給了大山/交給了野生動植物/蕨菜、芭蕉根、山藥/松鼠、野豬、小鳥/都是他們的口糧”,靠采集和狩獵作為重要的生活補充,也靠同山下人在大路邊以物易物換取生活的物資和工具(如李干斗的曾祖父用八只松鼠干巴換得全卡第一塊打火石,他的祖父用一整頭麂子干巴和一背簍名貴藥材換得全卡第一桿獵槍)。直到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軍找到了他們,在黨和政府以及周邊各民族同胞的幫助下,苦聰人才定居定耕、發(fā)展生產(chǎn)、學(xué)文化、搞衛(wèi)生、改變生活方式。70年后的今天,李干斗的拉祜族村寨徹底告別了原始面貌,生活水平有了質(zhì)的飛躍。
在悠悠的苦聰簡史中,哥布還講到了3個警世故事:一個叫簸的自信的獵手,醉心于設(shè)計和布置機關(guān)、陷阱,成功狩獵了許多大型動物,最后在自己的機關(guān)旁被“有預(yù)謀的老虎”咬食得只剩殘軀;一個叫扎的獵長,召集男人們拿著毒弩到動物必經(jīng)的隘口圍獵,卻被頭次擔(dān)任射手的20歲小伙瓦叭誤認(rèn)為草叢里的麂子射死了;“多年以后,當(dāng)瓦叭逐漸從內(nèi)心深深的愧疚中走出/正在成為一個/聲譽日隆的獵手/幾乎與扎的辭世方式/一模一樣”,“不同的是/瓦叭身中的是獵槍的獨頭子彈”。這些獵手的劫數(shù)在哥布看來是必然的,正如他已清醒地反思道:“我在歌頌獵手的時候/可能也在歌頌血腥”,內(nèi)蘊樸素的真理:若人類丟棄生態(tài)良心,大自然必將奉呈罰罪。
三
同樣樸素的是哥布詩歌的語言。“有時,幾天沒有進(jìn)食/他們在芭蕉葉的棚子里/烤火或者發(fā)呆/躺在路邊的草叢里/看著空曠的遠(yuǎn)山/陽光燦爛,天空湛藍(lán)/他們的身體和靈魂/在被人遺忘的深山/煎熬”,寥寥幾筆就寫出了苦聰人缺糧的窘?jīng)r及其更大的精神困境,此類簡潔的口語幾乎布滿全詩。更為令人欣喜的是他詩句中綿長的回味與甘甜。當(dāng)其他詩人們忙于去馴服意象、修辭、意義等時,哥布還注意到了聲音,“詩人不諳聲音之道,或許是當(dāng)代讀者于新詩不親的主要原因吧”(江弱水語)。“傳說他們從葫蘆里出來/是天神厄沙的孩子/其實他們是古羌的后裔/從遙遠(yuǎn)的西北向南遷徙/操著古老的彝語支話語/守著祖?zhèn)鞯纳袷サ男帐?不知什么原因/也不記得什么時日/也許是無心/或者是有意/人類把自己的兄弟/遺忘在了茫茫的森林里。”基于對第二語言的語感(他的母語是哈尼語),哥布用精巧的腳韻使詩更有了歌韻,“i”聲不絕,伴隨著聲帶顫動,多么像苦聰人世代跌宕、流離、漫漶的心靈。哥布還運用了其他的聲音設(shè)置,比如那個在詩中常常揚歌的女巫莫奔:“慈祥的老族長啊/智慧的老族長/您是厄沙的化身/您是神的仆人/您讓大樹枝葉繁茂/您讓苦聰子孫繁衍……”顯性的句式重復(fù),隱性的節(jié)奏縈回,神靈的使者在溫美的旋律中抒情。“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寫得相當(dāng)樸實、透明,語言的無蔽性令我對久已熟悉的漢語產(chǎn)生陌生感,漢語在一種哥布式的新鮮中重現(xiàn)它最初的面目”,這是于堅對哥布詩歌的夸贊,我深有共鳴。
哥布站在誠實莊重的語言之川,用心用情用功記錄西隆山的“醒來”,做拉祜族同胞從原始農(nóng)耕時代邁入現(xiàn)代生活的時間代筆人,書寫出了拉祜族波瀾壯闊的時間之詩,深刻揭示了黨和國家對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關(guān)愛。在當(dāng)前云南省扎實推進(jìn)全國民族團(tuán)結(jié)進(jìn)步示范區(qū)建設(shè)的偉業(yè)中,哥布正用此詩傳遞著民族團(tuán)結(jié)的進(jìn)步理念,像那朵西隆山崗上盛放的玉荷花,是春天的符號。
 作者:師國騫
作者:師國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