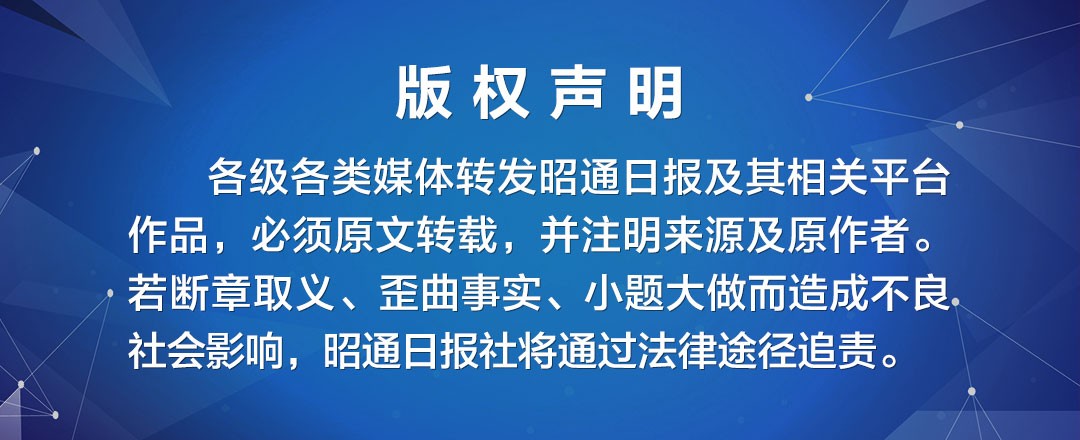2020-07-22 10:27 來源:昭通日報

灑漁素有魚米之鄉(xiāng)的美名,曾經(jīng)作為貢米上呈皇宮。特別是木瓜林的米最為有名,木瓜林的米,煮熟了米粒是豎立的,吃起來異常的香甜。我不想去探究灑漁米香甜可口的原因,我只想去追憶那萬頃秧苗的碧綠,一望無際香稻的金黃,以及栽秧、捉鯽魚、逮鱔魚、抓泥鰍的快樂。
灑漁的夏天屬于萬頃的碧綠。萬頃碧綠把我從一個無憂無慮的孩童托送到意氣風發(fā)的初中時代,初中的我正是豪情萬丈的年紀。有那么一段時期,我時而激情澎湃,時而憂愁郁悶,父母和哥哥們懷疑我患了精神病,因為我激情澎湃時表現(xiàn)的就是狂躁癥的癥狀,而憂愁郁悶時就是典型的郁抑癥。狂躁癥發(fā)作的時候,我會跑到背后的山上高呼,望著萬頃碧綠盡情放歌,高頌岳飛的《滿江紅》:“怒發(fā)沖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抑郁癥發(fā)作的時候,我就躺在屋前池塘的柳樹枝編織的柳床上呆呆地望著房屋北邊的稻田,低吟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我在狂躁與抑郁中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當然在這段時間里,我也沒有落下學業(yè),這也是我反駁父母和哥哥們懷疑我患精神病的有力證據(jù)。在這段時期,我依然是從家門出發(fā),然后經(jīng)過碧綠的稻田,走在稻田間的田埂上,直到學校的大門。放學后,我又從學校大門出發(fā),從熟悉的田埂回家。每天來來回回三趟,已經(jīng)熟悉到可以閉上眼睛從家到學校的程度。
學校的四周都是稻田,稻田的碧綠包裹住學校。然而,當夜幕降臨或烏云密布的漆黑夜晚,包裹學校的就不再是碧綠,而是使人透不過氣的黑暗。在漆黑的夜晚,學校里點著煤油燈學習的學子們在孜孜不倦的苦讀,從學校窗戶里傳出的微弱的一點點燈光,成了整個漆黑的灑漁壩子一點希望,也成了人們辨別方向的燈塔。可是,學校為了規(guī)范校園管理,要求十一點統(tǒng)一關(guān)燈。關(guān)燈后,不準學子們在教室里點煤油燈看書,于是,滅燈后的整個灑漁壩子完全被黑暗緊緊包裹,市九中也因此從全市升學率最高的學校下降為極為糟糕的學校。從一所名校降為一所末流學校,這盡管不是所有畢業(yè)于市九中學子的哀傷,但卻是我的哀傷,我相信有著這種哀傷的學子并非只有我一個;我也相信,凡是具有榮辱情懷的學子,看著自己母校的淪喪,無不深感切膚之痛;我還相信,學子們學習的激情像剛點燃的火焰正要熊熊燃燒,卻被規(guī)范校園管理的冷水撲滅,這不止對于學子們的學習激情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對學校也是一個消淪的舉措。
晚自習下課,我的心情異常的郁悶。走出學校,放眼望去,都是綠色的一片,月光朦朧,朦朧中的碧綠望不到邊。我信步走在田埂上,慢慢蹲下來,輕輕地愛撫著秧苗的葉面。秧苗還沒出穗,每一株秧苗都筆直地挺立在水中,這時的秧苗和我們中學的學子及其相仿,她們也像我們一樣渴望成長。相對于她們的一生,這是他們的青年時期,這是她們的授粉時期,這是她們成長的最關(guān)鍵時期,如果這個時期天陰沉沉,烏云密布,陰雨綿綿,水稻就揚不了花、授不了粉,那水稻生命的意義就此了結(jié),盡管它一樣可以生長到秋季,這有點像植物人一樣。我輕輕地撫摸著水稻的葉面,希望她也有思維,這樣我就可以和她述說我心中的郁悶。可是我知道她和我的本質(zhì)區(qū)別就是我有思維,她沒有。帕斯卡爾說過“人是一棵能思維的蘆葦。”也就是說,給一棵蘆葦加上思維,她就和人一樣了。我希望給手中的這棵水稻加上思維,這樣她就能感受到我青春期的狂躁與抑郁。我拉住水稻的嫩葉,就當她有思維,低聲向她述說我的苦悶與無奈。這是一個霪雨霏霏的年份,陰風濕雨已一月有余,日月的光芒被層層烏云包裹,水稻揚不了花、授不了粉,因此郁郁蔥蔥生長的秧苗也成了一具沒有稻米的空草。我同情地握緊水稻的葉面,同情她的遭遇,我深深地感受到與她有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站在六個石包山頂上,望著綠油油一片萬頃水稻,但卻知道這已是一片荒蕪的雜草,這是怎樣的一種諷刺,這是怎樣的一種傷痛。
至若豐收之年,奔來眼底的碧綠蘊含著沉甸甸金黃黃的稻谷。深秋之際,站在六個石包之巔,整個灑漁壩子盡收眼底,這時最美的風景是灑漁煙柳,但最激動人心、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風景確是隨風浮沉的一浪接一浪的萬頃香稻。晴空萬里,金黃黃的香稻在燦爛陽光的照射下,猶如黃金閃閃;微風中一浪接一浪的香稻與浪與浪之間隙銀白的水波相連,宛若漂金蕩銀。漫步在田埂,我被金黃的稻穗深深地震撼,蹲下身子,把頭置于與稻穗一樣高,放眼望去,是一望無際的金黃。倘若一陣風吹來,稻浪滾滾而來,會有一種排山倒海之感。站在金黃色的浪濤滾滾之間,就像指揮著千軍萬馬向敵軍勇往直前沖鋒,我的思緒隨著洶涌澎湃的浪濤高漲,似乎升到一望無際的、廣袤的天空,眼前一碧萬頃、晴空萬里。正當心曠神怡、雄心勃勃、壯志凌云、長風破浪之時,天庭突然暴怒,天空頃刻烏云密布、電閃雷鳴、陰風怒號、日星隱耀、狂風暴雨,我的思緒從蔚藍的碧空一下掉入臭泥塘,無髓之軀只能在臭泥塘里茍延殘喘。殘喘之余,望望身旁碧綠茁壯的沒有稻穗的稻草,只能再次感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同殘喘之余,一同回憶從前的往事,也可以稍稍沖淡臭泥塘的臭味。
小時候沒有栽秧的資格,只有在田埂上拋秧把的份,那時總盼著能像大人一樣栽秧。這一天總算等到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鞋子,擼起褲腳和袖子,站在大人的中間,開始栽秧。結(jié)果別人栽了二十多棵秧苗,我還沒栽好五棵,而且東倒西歪,還有兩棵沒栽穩(wěn),漂了起來。
于是,我被哥哥弄出栽秧的列隊。他找了一小塊田角,先教我怎么栽秧,叫練習熟了再進入列隊。他教我用左手拿著秧苗,用拇指和食指把手掌中的秧苗分出來,而且一次只能分出一棵,然后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接住左手分出的那棵秧苗,拇指輕輕一按,就把秧苗按在食指和中指之間,接著拇指、無名指、小指同時卷起,秧苗順著食指和中指插入泥里。通過哥哥的講解,我才知道我剛才栽的是五爪秧,也就是五個手指都插如泥里,五爪秧是很難成活的。我在這塊田角栽了拔,拔了又栽,反反復(fù)復(fù)練習了很多遍,直到下午才勉勉強強把秧苗插穩(wěn)。看了無數(shù)次栽秧,總認為很簡單、很好玩,可是實際操作起來并不是想象中那樣簡單。一天下來,手指辣乎乎的痛,整個腰像斷了似的。人們對自己不熟知的領(lǐng)域總是心存浪漫和好奇,等嘗試之后才知道事實與想象并不一樣。
初中的夏季學期的一大樂事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邀約一大批同學集體去栽秧。那時基本都是在學校吃了中午飯,然后集合,騎著自行車出發(fā)。那時自行車相對匱乏,并不是每個同學都擁有一輛,所以組織者就會安排載人。這樣磨磨蹭蹭到主人家的田邊,差不多一點過,這個時候也正是開始栽秧的時刻。因為早上是拔秧苗和耙田,這兩個活都是專業(yè)人士干的,不是我們這些毛手毛腳的學生娃娃能干的事。特別是耙田這個活,專業(yè)耙田人站在木耙上,一般是左腳站在木耙的前枋,右腳站在木耙的后枋。耙田人用鞭子驅(qū)使著兩頭并排拉木耙的牛,來來回回十遍左右,大的土塊已弄碎。這時,耙田人用右腳往后木枋橫桿一鉤,后面木枋一下翻了過來,齊排排、鋒利的十把尖刀瞬間翻到上面,讓人毛骨悚然、驚恐萬分。原來前后木枋的下面各有十把鋒利的尖刀,目的就是把大土塊弄碎,弄碎后就要把田土耙平,耙田人把后面的木枋翻過來,目的就是耙平田土。田土耙平一個小時后,田水下面就會沉淀一層薄薄的漿泥。秧苗插入漿泥,既穩(wěn)沉,又容易成活。開始的年頭,栽得快的會把栽得慢的圍在田中央。后來為了每一行整齊,就讓兩個人在田埂的兩端,用繩子一拉,栽秧的人順著繩子栽下去,這樣就非常的整齊。拉繩子的人按大行小行交替進行,大行五寸小行三寸,栽秧慢的人一般會被分配去拉繩子或者去拋秧苗。這種寬窄行稻田種植法從樂居開始,逐步推廣到全市。
我們栽秧的速度和質(zhì)量與專業(yè)種田人士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所以我們名義上是去栽秧,實際上玩耍的成分更多,大家在田里嘻嘻哈哈鬧個不停。父母們責備我們荒廢學業(yè),我們總是用知青下鄉(xiāng)來反駁。從1955年開始的中國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āng)持續(xù)了二十多年,那時“農(nóng)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成為積極的口號,在這二十多年中,據(jù)說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大約1800萬人。我因為出生晚了一點,所以沒能親身經(jīng)歷這場驚心動魄的運動。如果不是父親1995年胃出血住院的話,我對知青下鄉(xiāng)的體味也不會太深刻。父親因為退行性膝關(guān)節(jié)炎被當?shù)氐泥l(xiāng)村醫(yī)生用了大量激素藥物,導(dǎo)致胃出血,送入市一醫(yī)院救治。我聽說后馬上從昆明趕回昭通,那時我還是一名醫(yī)學院的學生。父親的病非常危重,可是在病床上躺著卻無人問津,醫(yī)生根本就不把患者的死活當回事,正當家人束手無策的時候,突然一個年長的護士帶著兩個年輕護士急匆匆闖入病房,核對父親的身份信息,核對無誤后,年長的護士突然摘下口罩,激動地看著父親,問道:“黃叔叔!你看看我,你還記得我嗎?我是小童呀!”父親仔仔細細地端詳了好一會兒,才輕輕點頭說:“啊!你是小童呀!”她緊緊握住父親的手,淚流滿面,無語凝噎,一個勁地點頭。過了好一會兒,她帶著兩個年輕護士出了病房。接下來,我父親得到了精心的醫(yī)療照護,因為小童是內(nèi)一科的護士長。小童就是1971年下鄉(xiāng)到樂居的知識青年,當時就是一個17歲的小姑娘,我父親堅持不讓小童和其他幾個一起下鄉(xiāng)的青年干苦活,只安排記記公分之類的事,并叮囑他們要多看書多學習。為了他們的安全,我父親把他們分別安排在幾家可靠的人家住下,小童就住在我們家,父母對待小童就像自己的子女。在父母的關(guān)心愛護下,小童沒有經(jīng)受什么苦難,后來也順利返回城市,成為一名醫(yī)務(wù)工作者。在父親住院期間,得到了小童的精心照護,父親很快就康復(fù)了。知青下鄉(xiāng)活動持續(xù)20年左右,于1980年宣布結(jié)束。知青下鄉(xiāng)活動雖然結(jié)束了,但這種思想和行動依然延續(xù)著,時不時又來一場變種的風暴。這種下鄉(xiāng)活動制度一直延續(xù)從未中斷的典型應(yīng)該是醫(yī)療行業(yè)。醫(yī)療行業(yè)的職稱晉升有明確的規(guī)定,從初職晉升到中職、從中職晉升到高職必須下鄉(xiāng)指導(dǎo)工作一年或者半年,也就是省市三級醫(yī)院的醫(yī)生要想晉升職稱就得下到縣區(qū)二級醫(yī)院,而縣區(qū)二級醫(yī)院的醫(yī)生要想晉升職稱就得下到鄉(xiāng)鎮(zhèn)一級醫(yī)院。事實上,省市三級醫(yī)院分科很細,下派到縣區(qū)級醫(yī)院沒有用武之地,譬如省級核醫(yī)學科的醫(yī)生下派到縣區(qū)級醫(yī)院,除了一天找不到事干之外他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很多科室的醫(yī)生都面臨沒事可干的尷尬,回去是不行的,呆在下鄉(xiāng)單位又沒事可干,在這一年中成了喪家的無所事事的孤魂野鬼。而縣區(qū)級的醫(yī)生下到鄉(xiāng)鎮(zhèn)就更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縣區(qū)級的醫(yī)生基本都是專科醫(yī)生,而鄉(xiāng)鎮(zhèn)級基本是全科,專科醫(yī)生也只能無奈地裝神弄鬼一番,盡快把下鄉(xiāng)證明弄到手。我不知道這種下鄉(xiāng)活動在其他地方的效果如何,就我所知道的醫(yī)療機構(gòu),除了勞民傷財、浪費資源、消耗人力之外,再沒其他任何效果。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gòu)如此,其他行業(yè)也好不在哪里。父母指責我們?nèi)ピ匝硎腔膹U學業(yè),其實我們自己非常明白所用的反駁材料是多么的荒唐,只不過那時具有極強的反叛意識,其實也就是一種青春期的躁狂罷了。不過不管所舉的實例如何荒謬、如何荒誕、如何荒唐,父輩們也沒法駁斥,因為他們就是這些荒誕離奇事件的踐行者和見證者。
水稻即將成熟時,也是鯽魚、鱔魚、泥鰍肥美之時。從水稻掛穗時,哥哥就隨時帶我們?nèi)プ紧~。哥哥先把魚籠安置在水溝的下端,用鐵環(huán)耙在水里上下攪動弄出聲響,慢慢移向魚籠,一到魚籠口邊,就立即提起魚籠頭,然后提起整個魚籠,再把魚籠尾對著魚盆,拔開塞子,魚籠里的魚就淌入魚盆,我主要負責把魚盆里的魚一條一條撿進魚桶。用魚籠捉到的主要是鯽魚,偶爾也有泥鰍。用魚籠是不能逮到鱔魚的,鱔魚基本是隱藏在相對比較柔軟的田埂里,哥哥逮鱔魚比較有經(jīng)驗,他首先找到比較松軟的田埂,再尋找非常光滑的小洞。找到洞后,他就先用手把洞口弄大,然后把手輕輕伸入洞穴探尋洞的走向,如果洞的走向與田埂的夾角大于四十五度的話,那么洞的出口基本是在田埂的對面,如果小于四十五度的話,洞的出口基本在同側(cè)。他弄好洞口之后,就把一只腳放進洞口,慢慢地用腳在洞口抽動,然后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出口,等鱔魚的頭鉆出洞口,他就用中指環(huán)一下掐住鱔魚的七寸,接著用鐵線串起來,遞給我提著。
在那個缺衣少食的年代,魚類是改善伙食的一種有效補充。因為要讀書,所以每周只有一次逮魚的機會,那時總是盼望周末的到來。周末一到,就迫不及待央求哥哥帶我去逮魚,一是因為好玩,主要還是想吃到美味可口的魚肉。鱔魚和泥鰍基本是紅燒,而鯽魚則是紅燒、清蒸、清湯、糖醋換著吃。在我十二歲那年,我二哥從咸陽回來,他那時在咸陽工作,一年回來一次。我記得我和四哥逮了好多的鯽魚,二哥說他做糖醋鯽魚給我們吃。只見他拿起一條鯽魚,用刀輕輕拍拍魚頭,快速把魚鱗剔除,然后破開魚腹,去除內(nèi)臟,從他一系列的動作來看,他宰魚的動作非常的嫻熟。等到吃晚飯時,我首先看到的是桌子上那一大盆糖醋鯽魚,我迫不及待地夾了一條放進嘴里,味道之鮮美,至今還記憶猶新。后來也吃過很多次糖醋鯉魚,可是再沒有那次的鮮美之味。再后來呀,稻田里的鯉魚越來越少。現(xiàn)在呢,稻田里再也找不到一條鯉魚,當然泥鰍、鱔魚也隨之消聲覓跡。這一切的功勞全歸于農(nóng)藥的使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以前,人們很少使用農(nóng)藥殺蟲劑,那時的農(nóng)作物可以稱之為天然無公害農(nóng)產(chǎn)品。可是從本世紀初開始,人們普遍使用農(nóng)藥殺蟲劑,用量越來越大,農(nóng)藥所過之處,害蟲尸骨無存,益蟲也片甲不留,鯽魚、泥鰍、鱔魚隨之灰飛煙滅。現(xiàn)在農(nóng)藥的使用已經(jīng)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農(nóng)藥噴灑之處,不要說是所有昆蟲魚類瞬間冰消瓦解,就連秧苗周圍的雜草也一下煙消云散。譬如百草枯就是一種讓昆蟲魚類和雜草瞬間消失的農(nóng)藥,有了百草枯,農(nóng)民種植稻田方便之極,用了百草枯,農(nóng)民就可以逍遙自在的去玩耍,不用去稻田驅(qū)趕害蟲,更不用下田去拔雜草。可是用百草枯殺除雜草種出來的稻米他們是不會自己留著吃的,他們把稻米運到市場賣掉,再去買外地的大米自己吃,殊不知外地的大米也是用百草枯農(nóng)藥種植出來的。現(xiàn)在的飲食業(yè)有一個潛規(guī)則:自己不吃自己種植的糧食、自己不吃自己種植的蔬菜、自己不吃自己種植的水果;自己不吃自己喂養(yǎng)的牲畜家禽;自己不吃自己加工的食品,因為自己種植的糧食、蔬菜、水果的農(nóng)藥超標得讓自己害怕,自己喂養(yǎng)的牲畜家禽所用的抗生素、激素、飼料讓自己不敢吃,自己加工食品所用的地溝油、蘇丹紅、三聚氰胺、食品添加劑怕毒死自己。現(xiàn)在去農(nóng)村轉(zhuǎn)轉(zhuǎn),農(nóng)民喂豬都分為兩種喂法,喂了自己吃的,就用糧食和蔬菜喂養(yǎng),生長周期一般是一至兩年,這樣喂養(yǎng)出來的豬肉,就是貨真價實的豬肉;喂了去賣的,就添加大量的飼料和激素,生長周期一般是半年,這樣喂養(yǎng)出來的豬肉,吃起來沒有一點豬肉的味道,至于豬肉里會不會殘留激素,或者說豬肉里殘留的激素會不會影響人的健康,我想應(yīng)該會有一定的影響吧!當然具體的影響要通過相關(guān)的調(diào)查研究才能確定。可是,這些事關(guān)人民健康的事,在某些權(quán)勢看來是多么的無足輕重,他們關(guān)心的是自己的前程,人們的健康對于他們而言根本不值一提。有一次,一個朋友說,他可以從魚肉的味道分辨出魚是在池塘喂養(yǎng)還是在江水生長的,大家對他的味覺贊嘆不已,他說:“江水生長的魚有一種甘甜之味,而池塘喂養(yǎng)的魚有一股泥巴味。”事實上他并不知道事情的本源。我們小時候吃的魚也是生長在小溝和池塘里的,那時的鯽魚非常的甜美。同樣都是池塘里喂養(yǎng)的魚,為什么以前味道鮮美,而現(xiàn)在有股泥巴味呢?原因主要是給魚喂了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不知道我們吃了這些喂了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對身體有什么危害,也不知道我們吃了用百草枯種出來的稻米會不會像喝了百草枯一樣。在基層醫(yī)院的急診科隨時能遇見喝農(nóng)藥的患者,在這些喝農(nóng)藥的患者中,最讓人揪心的應(yīng)該算是喝百草枯的患者,因為喝百草枯的患者,給了你后悔的時間,卻不給你活著的機會。每每想起喝百草枯患者將要死亡時的眼神,我總是全身驚悚、不寒而栗。每當我跟侄兒們講起小時候我們逮魚的趣事時,他們首先的反應(yīng)是看看日歷,會不會是愚人節(jié),他們根本不相信稻田里會有泥鰍,也不相信有鱔魚,更不相信會有鯽魚。因為現(xiàn)在的稻田里,除了秧苗之外,什么都沒有了,雜草沒了、泥鰍沒了、鱔魚沒了、鯽魚沒了,就連啄稻谷的麻雀也沒了,除了水稻、機器和人之外,好像一切都沒了,蛙聲一片也成了一種過去的永恒,這里除了一片死寂,找不到任何生機盎然的景象。
秋天是收割稻谷的季節(jié),當?shù)靥魱|西一般都用扁擔,但挑稻谷要用纖擔,纖擔要比扁擔長三分之一左右,兩頭是尖的。人們把水稻捆系在纖擔上,從稻田里挑起,就一直要到稻谷場才能放下,中間不能歇氣,否則稻子會掉落在歇氣的地方。水稻放在稻谷場曬幾天后,就可以扳谷子了。扳谷子就是支好一塊石板,用夾子夾住水稻尾,把水稻頭用力扳在石板上,這樣谷子就落下來。后來用上稻谷脫粒機,兩個人把水稻抱到脫粒機的兩旁,另外兩個人用腳蹬脫粒機,同時用手拿起水稻,把水稻放在脫粒機上,很快谷粒就脫離了。剛剛有稻谷脫粒機時,我們很好奇,總喜歡去蹬脫粒機,但最難受的是穗稻的毛絨掉到脖子里,特別出太陽,脖子里流著汗,那種難受的滋味至今想起還感覺毛骨悚然。再后來,電動稻谷脫粒機普及后,人們就此高傲地自詡進入的現(xiàn)代化,這些沒見過世面的井底之蛙們高炫凱歌:“我們超英趕美了!”
我記得當時很多的稻谷要交給國家,叫做交公糧和余糧。那時我還太小,總覺得父母很奇怪,我們家自己都還不夠吃,為什么還要交公余糧呢?特別是好不容易喂養(yǎng)大一個豬,宰好后也要交一半給國家,而且還要交有豬尾巴那半大的,當時就是想不通父母的行為,我們家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吃一頓豬肉,自己辛辛苦苦喂養(yǎng)的豬為什么要上交?后來漸漸明白了,我們所種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國家的,土地下戶其實是土地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家庭就是承包土地來種,既然土地不是自己,是承包來的,理所當然要交承包費,承包費就變成了公糧,其實就是農(nóng)業(yè)稅。土地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制實施后,農(nóng)民對承包的土地有了使用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但沒有買賣權(quán)。后來公余糧免了,土地依然不能私自買賣,只能國家收購或流轉(zhuǎn)。
遇到風調(diào)雨順之年,水稻每畝能產(chǎn)四五百公斤;一旦遇到天災(zāi)就會減產(chǎn),甚至毫無收成,譬如我讀初中二年級那年就顆粒無收;當然攤上人禍也會兇年饑歲,譬如大躍進之年,那時的水稻被浮夸風吹詡到每畝能產(chǎn)萬斤,但人們卻餓的面黃肌瘦。在大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虛報風浮夸風盛行,在農(nóng)業(yè)上,提出“以糧為綱”,不斷宣傳“高產(chǎn)衛(wèi)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于是水稻被虛吹到能畝產(chǎn)萬斤。1958年7月,各媒體先后刊登湖北省長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早稻畝產(chǎn)15361斤,放了一個大大的“衛(wèi)星”。榜樣既出,各地紛紛效仿,畝產(chǎn)萬斤的報道接踵而來、比比皆是。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報》報道,天津市的東郊區(qū)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chǎn)12萬斤,并稱在田間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接著《天津日報》10月8日和10日又分別報道天津市雙林農(nóng)場“試驗田”畝產(chǎn)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時轟動全國,吹詡的神功可謂獨領(lǐng)風騷。當時我的父輩們對此事深信不疑,因為偉大的領(lǐng)袖親自視察過天津市新立村的“試驗田”,所以他們絕對相信水稻能畝產(chǎn)12萬斤。父輩們有時無意談起這些事,我總會插嘴評論一番,父輩們也不跟我較真,基本都是嘿嘿一笑而過,那時我總以為父輩們都很愚蠢、都很愚昧、都很無知。慢慢地,我也經(jīng)歷了很多很多事情,才明白父輩們的無奈與悲催,我總以為自己聰明、精明、能干,漸漸的我也明白,自己和父輩們沒有兩樣,都是被抬高到人模人樣的一群黑毛豬,或者說都是被塑造為一群披著人皮的快樂豬。
對于水稻的育種及種植,有一位雜交水稻育種專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專研著、耕耘著,他就是舉世聞名的袁隆平老人,他被譽為“世界雜交水稻之父”。2016年袁隆平團隊選育的超級雜交稻品種“湘兩優(yōu)900(超優(yōu)千號)”平均畝產(chǎn)1149.02公斤,創(chuàng)造了世界水稻單產(chǎn)的最新、最高紀錄。這項最新、最高紀錄是世界公認的,而天津市雙林農(nóng)場“試驗田”畝產(chǎn)稻谷126339斤是1958年10月8日和10日由《天津日報》報道的,在實際與報道之間的距離就像從三維空間進入四維空間無法丈量。無法丈量的還有袁隆平雜交水稻對人類的貢獻。可是不論他的貢獻如何大,也換不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一張遮羞布。盡管在1995年時,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也無法掩蓋科學和科研評選制度的丑陋,科學本來是最純真、最公平的,可是制度把最純真、最公平的科學變得無比丑陋、無比的邪惡、無比的黯淡。多次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他,2006年卻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這對中國科學不知是諷刺還是警示?“袁隆平先生發(fā)明的雜交水稻技術(shù)。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貢獻,增產(chǎn)的糧食每年為世界解決了7000萬人的吃飯問題。”這就是世界著名科學家、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美國科學院院長西瑟羅納先生在新當選院士就職典禮上介紹袁隆平院士的當選理由。而我們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做客人民網(wǎng)強國論壇面對網(wǎng)友提問是怎么說的呢?他說:“我個人認為,袁隆平完全有資格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未能當選,這只不過是一個歷史上的誤會。”美國科學院院長西瑟羅納先生宣布袁隆平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的理由非常明確,而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回答網(wǎng)友卻非常的含糊,什么歷史上的誤會?作為中國科學院的院長都羞于或者不敢說出袁隆平未能當選的真正原因,只能用一句“這只不過是一個歷史上的誤會。”敷衍過去,這于科學本身而言,是何等的悲哀。
袁隆平先生發(fā)明的雜交水稻技術(shù),為糧食增產(chǎn)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可是曾經(jīng)的魚米之鄉(xiāng)的灑漁卻用不上這項技術(shù)了,因為現(xiàn)在的年輕人要么去城鎮(zhèn)工作,要么去大城市打工,沒有人愿意留在農(nóng)村種水稻。偌大的一個灑漁壩子,以前是一片金黃的水稻。現(xiàn)在什么都種,蘋果、梨、葡萄、櫻桃、玉米、洋芋、小麥等等,零零星星的也種著幾塊水稻,顯得七零八落。秋高氣爽之日,登上山頂,放眼望去,萬頃香稻已然逝去,收入眼底那幾塊亂七八糟的奄黃的穗稻,宛如風塵女子身上飄拂的幾許襤褸彩衣。

來源丨@昭通日報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