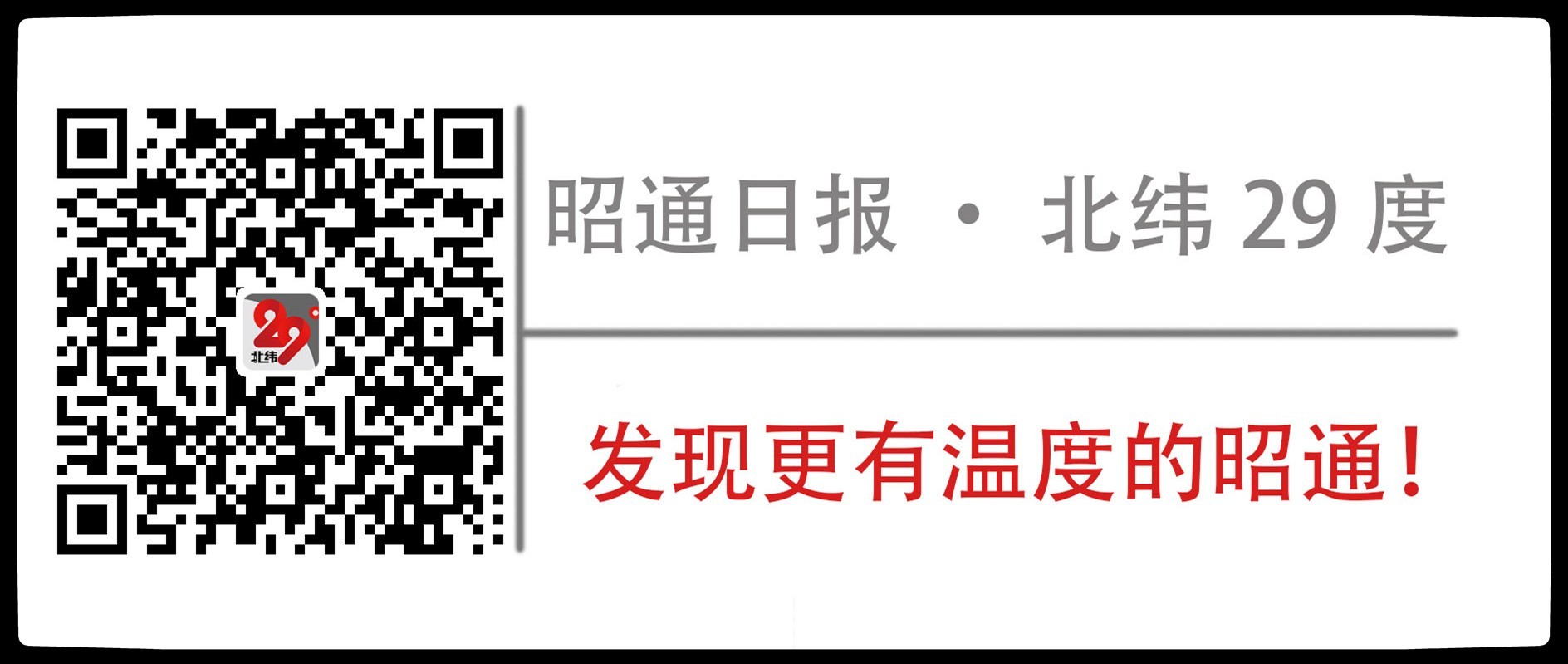2020-08-25 15:51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初秋,上午10點的陽光已經(jīng)有些熾烈了。在經(jīng)歷了整個長夏的繁密雨水之后,“拐過秋天的埡口”,“雨腳”漸漸收住,陽光猛然間“熱辣”起來,進入了“催熟”莊稼的“曬黃天”。鄉(xiāng)間有民諺說:“七月‘辣’太陽,啞巴喊曬死。”這里的7月,指的是農(nóng)歷七月間。在這時的大太陽下,已經(jīng)灌漿成熟的莊稼一天天悄無聲息地暈染開秋色,直至將人們又一歲的勞作與汗水,點染成這大地明亮的詩章。
在這秋天上午的晴朗陽光下,沘江,一如它過去的千萬年那樣,在兩岸群山巍峨的峽谷間潺潺流淌,尚未褪去雨季“洪顏”的水面,在陽光下泛著微微的波光。沘,電腦的五筆字庫里沒有這個字,新華字典注其音為bǐ,“沘源,河南省唐河縣的舊稱。”而在山高水長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龍縣縣境,在與云龍相鄰的沘江的發(fā)源地蘭坪縣(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以及附近的永平縣(屬大理白族自治州轄區(qū)),乃至在所有認識這條河流的整個滇西,人們都把這條河流叫作pī江。這是這條古老的河流獨屬于這片土地的見證。我甚至有些主觀地這樣想著:“所有從外面來到這片土地、見到這條河流的人,當他們在見過了這條河流流淌的樣子之后,便會喜歡上這個名字,然后,像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那樣,將它親切地叫作pī江。”
有著兩百多年歷史的古道木橋——通京橋就安靜地跨在沘江之上。在西面橋亭腳的側(cè)壁上,嵌著一塊白色的大理石碑,上面的刻文介紹了這座橋的稱謂、歷史以及構(gòu)造:“通京橋,原名大波浪橋,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橫跨沘江,東西走向,為懸臂式單孔木梁風雨橋。全長40米,孔凈跨29米,距水面12.5米,橋身采用木枋交錯架疊,從兩岸橋頭層層向河心挑出,在相距9米處,用5根粗壯的橫梁銜接,上鋪木板。橋面寬4米,上建抬梁式木結(jié)構(gòu)橋屋,兩側(cè)設(shè)護欄,兩端建亭。”之所以在這里較完整地引用了橋碑上的介紹,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講清這座古老木橋的獨特構(gòu)造。這種全部以木承重的古橋梁,是云龍縣境內(nèi)獨有的木橋構(gòu)造形式。在這段介紹中的“懸臂式”,有些資料中又稱為“伸臂式”。“大波浪橋”又稱為“大波羅橋”,因其所在地為“大波羅村”(還稱“大包羅村”的),屬云龍縣長新鄉(xiāng),古橋所在地距離云龍縣城38公里。湊巧的是2016年,離1776年建橋時,剛好是240年。
走上古橋,發(fā)現(xiàn)上面一如許多古橋那樣,在橫鋪的木板橋面上,正中縱向又鋪一道由兩塊厚木板拼起的寬約兩尺的木板,上面每隔約一臂的距離橫向釘一道厚木條。不難看出,中間縱鋪的這道厚木板,除了能更好地固定橋面,更主要的作用是給騾馬走的道,人們趕著負重的騾馬從橋上走過時,馬走中間,人走兩側(cè),騾馬負重后蹄腳重,若沒有中間這道加厚的騾馬行道,橋面便很容易被踏壞。釘在縱道上的橫向木條,除了固定住兩塊木板,同時還起到了防止騾馬蹄腳打滑的作用。在安靜的橋面上,有著幾攤牛馬的糞便,有的已經(jīng)半干,有的還很新鮮,這可能是早上才從橋上走過的牛馬留下的“新鮮痕跡”。
站在橋上,倚著橋廊望橋下的沘江,江水北來南去,恍惚間,似是千萬年的時光滔滔涌流至前,穿過腳下這道經(jīng)風歷雨的古老木橋,依依向著來日緩緩而去。在這江的兩岸,是逐漸向上打開的巍峨高山,深青色的玉米地大片大片地鋪展在從山腳至山腰的坡地上,村莊一簇一簇生長在茂密的玉米地間,而在緊鄰河岸的山腳地帶,一丘一丘彎彎的稻田間,已悄悄暈染開最初的秋黃。
我這樣想著:一條河流,它所能給人的最好的惠顧,便是年復(fù)一年地澆灌著兩岸的田野莊稼。人們世世代代依傍著它,將兩岸的稻田插滿秧苗,將兩岸的山坡種滿玉米、大豆和蕎麥,將兩岸開滿野花的大地,釀成人們世代棲居的祥和故土。雨水從屋瓦落下,雞鳴在黎明升起,炊煙年復(fù)一年匯入山頭的云朵。生活在兩岸村莊里的人們,早晨從橋上出去,夜晚從橋上回家。群山與河流組成的大地,召喚離家的人們聞著花香從遠方歸來。
在云龍縣大地上,我注意到,當人們在說著沘江的時候,就像是在說著自己的母親。志書上載:公元前109年,漢朝征服滇國設(shè)置的益州郡,將勢力伸入哀牢國東部(今云龍縣),設(shè)置“比蘇縣”。據(jù)說,“比”,在白語里的意思是鹽。云龍古境,最早便是一片因鹽而始的治地。從比蘇縣起始,在兩千多年的時光里,這片滇西秘境的名字,與鹽一起走遍各地。“比”與“沘”( pī),這樣兩個音形相類的字,使我想到這條河流名字的由來,“沘”,我猜想它應(yīng)該同樣與鹽有關(guān)。或者,“比”,在古時候同樣是被讀作pī的。這片蘊藏著無盡鹵水的古地,地被命之為“比”,河被名之為“沘”。云龍縣境的地勢,東西高而中部低,在地圖上,沘江從最北面的白石鎮(zhèn)進入云龍,以幾乎居中的位置,一路由北向南流經(jīng)全境。這條發(fā)源于北面蘭坪縣境、全長169.5千米的河流,在云龍境內(nèi)整整流淌了123千米,從北到南流經(jīng)了云龍的白石、長新、諾鄧、寶豐等鄉(xiāng)鎮(zhèn)村社,最后在南面的功果注入瀾滄江。對于云龍,對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這是一條真正意義上的母親河。人謂“云龍歸來不看橋”。因云龍境內(nèi)各種類型的古橋梁之多、保存之完整,所以云龍被稱為“古橋梁藝術(shù)博物館”。而這些以藤、木、鐵、石為材,浮、梁、吊、拱為構(gòu),日月久遠、修筑精致的古橋梁,大多數(shù)都是集中在沘江及其支流之上的,銜其進,渡其出,在漫長的時光里,連通兩岸人們的往來,讓其繁衍后代子孫。在位于白石鄉(xiāng)水城村的沘江之上,至今仍完整地保留著一座古藤橋。藤橋架設(shè)在江兩岸對生的老栗樹上,用當?shù)厮a(chǎn)的山葡萄藤編織而成,以兩根藤子扭編成的直徑約5厘米的長繩作為橋的左右兩臂,整座橋的造型,恰若一段長長的V形網(wǎng)兜,網(wǎng)兜底部鋪著寬不足一尺的木板作為行走的橋面,木板用鐵絲固定在藤網(wǎng)上,同時,在整座藤橋上,以每隔約一臂的距離用鐵絲對橋藤進行加固,以確保安全及增加橋的承重力。出了橋兩端用圓木搭成的簡易橋門,是同樣用圓木鋪成的短短的下橋坡。橋上陽光明媚,橋下流水泱泱。橋的東岸是稻田和玉米地,橋的西岸是臨岸人家的后花園一角,園里安靜地開著黃色和白色的菊花。
位于諾鄧鎮(zhèn)的云龍縣城亦在沘江的一側(cè)。一路往北而來的沘江到了城北1千米處,因形就勢,繞出一個大大的S型,彎成一個巨大的天然太極圖。后來在離開云龍的時候,殷勤的主人們給每位客人贈送了一幅鑲在支腳玻璃相框里的“云龍?zhí)珮O”圖(這是一組太極四季圖)。我得到的這一幅,上面是“云龍?zhí)珮O之春”(這名字多么好啊!)。在上面,春日上午的陽光,將沘江以西的山坡上尚未耕作的紅土地照出一片柔和的暗紅色,北面那個叫莊坪的村莊在晨光里顯得極為安靜,村莊腳下那片平整的田野里,油菜花開得一片金黃,從花塊的形狀上,看得出這片田疇間大多橫平豎直的線條。田疇之下,轉(zhuǎn)彎處的沘江水在陽光下反射出明亮的光。S彎的中部左側(cè),以及漸近尾端處的兩片大多長方形的田疇間,亦零星穿插著幾片菜花。在整個太極圖的東面,群山交錯層疊,有如絲如帶的潔白云霧緩緩飄移其間,直到將群山連綿送向遠方……繞著這個大大的太極圖,而今修建有一條沿河的行道,晚飯后的清涼時光里,一路上有許多人在上面散步和鍛煉,有人在路旁賣著黃瓜、水果和燒包谷。河岸上開著蘆葦花,路旁的田疇里,黃瓜藤和豆角相互纏繞著爬上了支架。云龍當?shù)厝嗽疲骸疤珮O圖上走一走,活到九十九。”是自然,亦是天意,大地上的萬千河流,唯有這條名叫沘江的水,最深切地領(lǐng)會了天地自然生息輪回的深情與奧妙。過了太極圖,便是云龍縣城,城中的文化廣場上,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有許多人在這里跳云龍獨有的民間舞蹈“力格高”。“氣!氣!齊齊氣恰氣!”踢腳、繞手、轉(zhuǎn)身、進退,這種以模仿動物的動作起始、節(jié)奏歡快熱烈的舞蹈,反映了人們與自然萬物的和諧相融。
時近中午,陽光熱辣了許多。過了大波羅村,一路沿著沘江逆流而上,從長新到白石,從大波羅村到順蕩村,從通京橋到彩鳳橋,一樣的沘江,一樣的古橋,舊舊的瓦頂,封閉式的橋廊,橋上兩側(cè)有供人坐著休息的橫木凳。稍有不同的是,彩鳳橋的西橋亭上修有閣樓,名曰“童子閣”,不像通京橋是直進的,而是從南向進亭。兩匹馱了空心磚的大騾子從亭口進來,在亭內(nèi)窄窄的空間里熟練地打個直角彎后,“嘎吱嘎吱”響著地上了木橋。趕騾子的人一邊小心輕扶著馬馱子,一邊一路喊著“當心”,“嘟嘟嘟”地過橋去了。有人用風順著河谷而下,輕輕穿過橋廊與橋屋。在北面橋廊正中一段的板壁高處,有白粉筆寫著大大的“人民”兩個字,南面橋廊正中一段板壁的近下腳處,畫了一個小小的可愛頭像(已有些模糊了)。我猜:字及圖畫,可能是孩子們在放學回家時的“涂鴉”。
論年齡,彩鳳橋比通京橋要久。彩鳳橋始建于明代,初為石板橋,后改建為木梁橋。將西橋亭改建為閣樓,是清光緒年間的事。順蕩古有鹽井,順蕩井是云龍古代“八大鹽井”之一。因鹽業(yè)的發(fā)展,古代在順蕩,建有大量的橋梁、驛站、店鋪、廟宇。順蕩古村現(xiàn)存的古民居,多為清代建筑。村下沘江上的彩鳳橋,是云龍通往蘭坪、劍川、鶴慶、麗江的古渡要津,是順蕩鹽運往外界的要道。
彩鳳橋、通京橋、青云橋、惠民橋,所有這些跨在沘江上的古渡古橋,除了連通兩岸人們的生活,在漫長的時光里,更是云龍食鹽外運的重要通道。一匹馬走過去了,一個人走過去了,一隊馬幫走過去了,一群趕馬的漢子走過去了,云龍的無數(shù)食鹽“走”過去了,2000年的冉冉光陰“走”過去了……
在順蕩,除了彩鳳橋,還有順蕩大慈寺古火葬墓群。順蕩火葬墓群是元末至明代中期白族的墓地,墓群現(xiàn)存火葬墓近1000冢,已發(fā)掘出的梵文碑85塊,梵文經(jīng)幢7座。所有墓碑皆為無冢碑,碑的正面(又稱為陽面)刻漢文,簡道死者生平,正面碑頭及兩側(cè)刻觀音、童子、魚、傘、寶瓶、海螺等“佛八寶”圖案;背面(又稱陰面)刻梵文。碑額均為半圓形,經(jīng)幢為正方形或六角形。墓地中最早出現(xiàn)的梵文碑為明永樂六年(1408年),最晚出現(xiàn)的碑為明萬歷元年(1573年),中間時間縱跨165年。墓碑所刻死者多為楊、張、高、趙姓,當中以張姓最多。
火葬墓群,再加上梵文碑,這讓順蕩古村以及古境云龍又多了一重神秘的面紗。梵文為印度雅利安語的早期名稱。資料稱,印度教經(jīng)典《吠陀經(jīng)》即用梵文寫成,其語法和發(fā)音均被當作一種宗教禮儀而分毫不差地保存了下來。云龍境內(nèi)的主體民族為白族,世居云龍古境的白族為何會在那樣一個時期內(nèi)在逝者的墓碑上刻寫梵文?再者,云龍縣境自古道教文化興盛,諾鄧古村有玉皇閣古建筑群,位于縣城南面的虎頭山有道教古建筑群,據(jù)說云龍?zhí)珮O圖東面山中正對著諾鄧玉皇閣,南面山中則正對著虎頭山三清殿,天然太極圖和境內(nèi)兩大道教文化建筑群神秘對應(yīng)在了一起。就是在順蕩,亦有著名的道教古建筑玄天閣。雖則在整個縣境之內(nèi),道、儒、佛三教交融,當中還交錯著白族本主崇拜,而為何獨獨在順蕩,出現(xiàn)了這樣一片火葬墓梵文碑?這使我聯(lián)想到通京橋所在的長新鄉(xiāng)大波羅村,其“波羅”之名,是否與佛教在這片地域的傳播有著神秘的關(guān)聯(lián)?“波羅”一詞原為佛教用語,有寫作波羅蜜,是梵文Paramim的音和意翻譯的結(jié)合,指到達彼岸。佛教源于古印度,于西漢末、東漢初傳入我國,經(jīng)過長期傳播發(fā)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在百度關(guān)于中國佛教史以及梵文的相關(guān)介紹里,沒有任何細節(jié)可以為起始于600年前、深藏于滇西秘境的順蕩古火葬墓群提供具體的解釋。這一神秘的梵文碑古墓群唯有讓人猜度,在明朝中期的那樣一段似乎并不特別的歷史時期,佛教,曾在這片因鹽而興的邊遠之地,有過隆重(這人世所能加于一個人的儀典,還能有比將他的一生埋葬并且銘記更隆重的么?)而深刻的影響。
“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從縣境最南邊的功果橋,一路溯瀾滄江西北而上至苗尾,再從苗尾過瀾滄江,一路沿盤山而上的苗(尾)諾(鄧)公路翻越五寶山回到縣城,又從縣城溯沘江一路北上到縣境最北的白石,在云龍的大地上,1000多年前“昭君出塞”的傷別辭,在相同的字面里,有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表達。群山壯闊,大河泱泱,山的高拔,水的綿遠,若父之偉岸、母之厚慈,孕育了這片土地久遠的文明、多彩的史詩。波浪滔滔的瀾滄江,滋養(yǎng)出史逾千載、遐邇聞名的古舊州,綿遠流淌的沘江見證了古村諾鄧2000多年因鹽繁華的煌煌歷史和古鎮(zhèn)寶豐300多年因鹽興盛的冉冉日月。沘江匯入瀾滄江,瀾滄江出云龍縣境,滔滔流經(jīng)保山、臨滄、普洱、版納,流出國境,流成一條長比日月的滔滔長河。而古云龍的眾多鹽井出產(chǎn)的白鹽,過了沘江和瀾滄江上的悠悠古橋,翻越過云龍大地上眾多的峨峨高山,沿著迢遙古道,走向山外,走向廣闊大地之上一座座車馬喧喧的城池、炊煙裊裊的村莊。
在地圖上看云龍,以沘江為縱軸,中間低、兩側(cè)高的地形,幾近于一本打開的書。可以確定,古境云龍,它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書——假若,我有一雙能夠讀懂這片大地的眼睛。比如瀾滄江畔的古治舊州,比如沘江岸上的寶豐古鎮(zhèn),比如沘江之上的眾多古橋,比如諾鄧古村的鹽上時光,比如太極圖上的晴明春色,比如高山天池的靜寧秋光。又或者,在傍晚的時候,坐在縣城文化廣場前的石階上,看人們在上面跳古老的舞蹈“力格高”,看夜色從兩側(cè)的山間緩緩落下,待燈火從四面點點升起。這當中的每一頁,都是云龍這片大地的獨有見證,而作為這本書的中線,沘江在這里從北向南亙古流淌,一歲又一歲,流過這大地上的春、夏、秋、冬。
而若是讓我非要選一個季節(jié)再回到?jīng)a江,我想,我依然要選擇這樣雨水收住、陽光晴明的初秋:山坡上大片大片的玉米地依然深青墨綠,中間有彎曲的道路通向那墨綠處寧靜的村莊;河岸上的稻田無聲暈染開最初的秋色;臨岸人家的菜園里,青綠的辣椒葉間掛出第一個鮮艷的紅辣椒;籬下的菊花開得一片爛漫,白的白,黃的黃;遠行的人從遙迢的遠方歸來,在風雨橋上抖落長路的汗水和塵埃;在沘江的兩岸,微風里布滿金銀花淡淡的清芬,迎接離人回到這溫暖的故土。
 作者:左中美
作者:左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