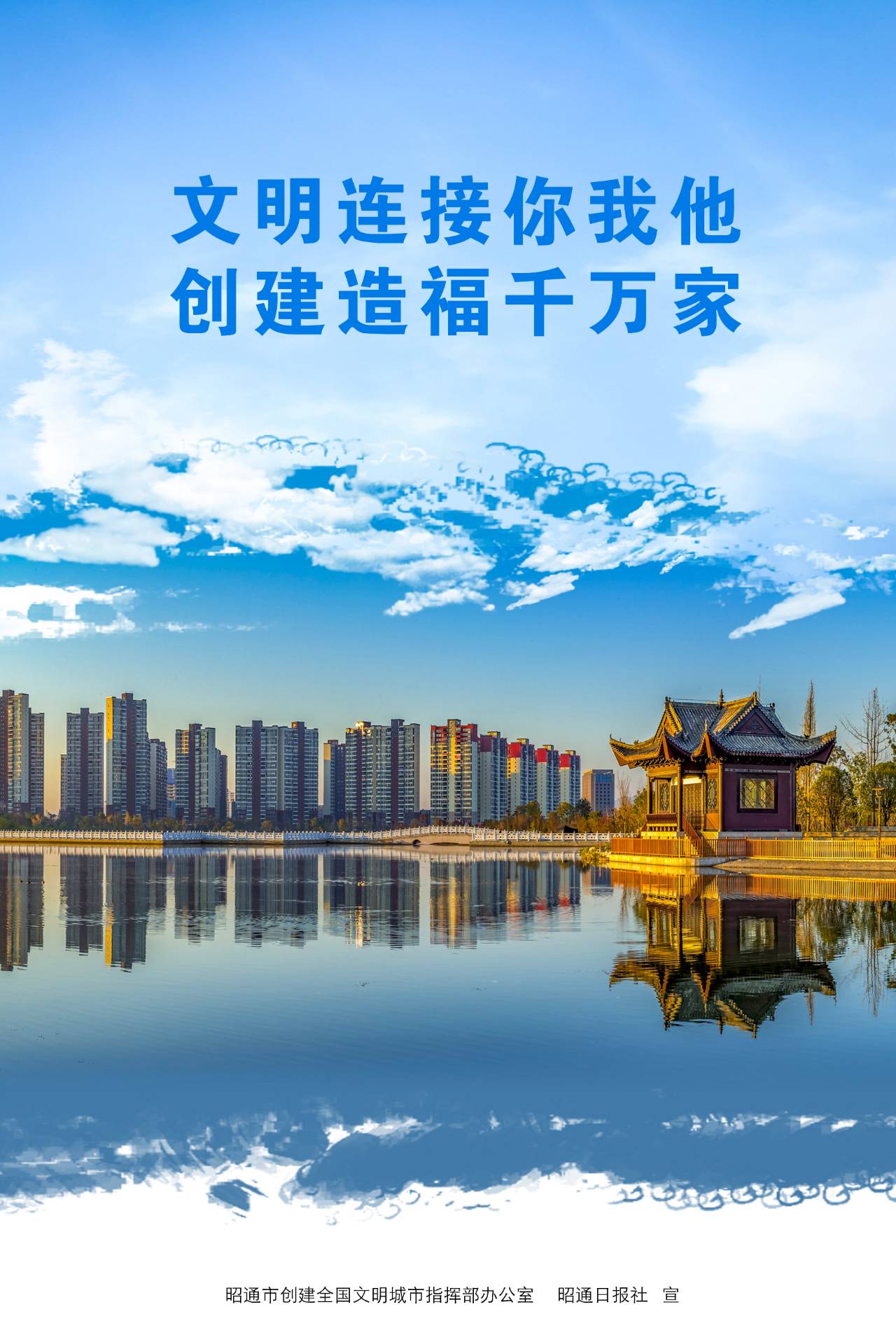2021-06-22 10:44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竇紅宇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魯迅文學(xué)院第29屆高研班學(xué)員。他曾有多部長篇小說發(fā)表于《十月》《大家》等文學(xué)期刊,并被改編成影視劇,還有多部中短篇小說散見于《人民文學(xué)》《十月》《小說選刊》《小說月報(bào)》《中篇小說選刊》《青年文學(xué)》《作品與爭鳴》《江南》《山花》《萌芽》《芳草》《滇池》《安徽文學(xué)》等刊物,大約有200多萬字。他現(xiàn)在是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委員會副主任,首屆云南大學(xué)滇池學(xué)院駐校作家。
老 趙
有一種情感,是一輩子都說不清楚的,比如我和老趙之間。
老趙叫趙正云,是壯族,已71歲,作家。他真實(shí)的身份,是云南省曲靖市師宗縣龍慶鄉(xiāng)黑爾壯族村的一位農(nóng)民。在那個(gè)小村里,他當(dāng)了大半輩子的民辦教師,同時(shí)也寫了大半輩子的小說,被很多人稱為“農(nóng)民作家”。我不知道“農(nóng)民作家”和“城里作家”有何區(qū)別,但在我眼里,老趙就像威廉·福克納(美國作家)一樣——一輩子守著“郵票大小的土地”、一輩子都在寫這個(gè)地方的人。老趙守在他的那個(gè)美麗的壯族村寨,教書、做木匠、寫小說,在省市級刊物上發(fā)表作品40多萬字。他說,他從未離開過黑爾,也從未離開過寫作。
我和老趙的認(rèn)識,就緣于寫作。每次他到曲靖來開筆會,我總要和他說幾句話,總要到他住的房間里坐坐,同他聊聊寫作,聽他講講黑爾。老趙是那種在人群中從不張揚(yáng)和多言的人,所以經(jīng)常聊著聊著,他就被“擠到”了邊角,像消失了一樣。但心里總想跟他說點(diǎn)什么,他也想跟我說點(diǎn)什么,可是,總是沒有說出來。兩個(gè)寫小說的人,竟然在20多年里,有一種“表達(dá)不清”的感覺。
今天,老趙71歲了,我也不再年少輕狂。老趙去師宗縣城,我就到師宗縣城去,見到他的時(shí)候,突然就想起來了,原來,我這20多年想對他說的話,就是想到他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寫了一輩子小說的地方去看看。
去就去了,我怕再不去,老趙就“老得寫不動(dòng)字、走不動(dòng)路了”。
從師宗縣城開車出發(fā),兩個(gè)小時(shí)之后就到了黑爾。那天,我總感覺黑爾的路是在老趙的敘述中鋪展開的,是在老趙所有的小說和故事中蜿蜒攀升的,所以,一路上我看見的人,趕羊的、趕街的、背背籮的和在高高低低的田野上不聲不響忙碌著的,我都覺得,他們都是老趙“筆下的人物”。
看得見黑爾的時(shí)候,車在山頂上停了下來。老趙從前面的車?yán)锾鰜恚衔遥驹诠愤叄h(yuǎn)遠(yuǎn)指著山下的黑爾說:“你看,黑爾!”我其實(shí)早就看見了,黑爾就在我的腳下,美得讓人驚嘆——大塊大塊的水田被大塊大塊的陽光分割得五彩斑斕,像大自然描繪的一幅無法超越的油畫,畫中炊煙裊裊。老趙指著他的家,笑得像個(gè)孩子。
看見這樣的笑,我好像明白了,原來老趙這20多年里想說的,就是要我到他寫過和正在寫著的黑爾來看看。我剛讀過他的一篇小說,其中的文字是“剛下過春雨,陽光下的石頭冒著熱氣,旮旯里的地也冒著熱氣,溫潤而暖和……”“這天,夕陽銜山,紫紅色的余暉把磨盤山涂抹得灼眼的輝煌……”老趙這輩子的寫作就是這樣,他一直指著山下的黑爾,對這個(gè)世界喋喋不休。
吃飯的時(shí)候,村子里來了很多的人,大塊吃肉、大碗喝酒;黑亮帥氣的小伙和白凈漂亮的姑娘來了一大群,他們都稱老趙為爺爺或公公,都說是老趙帶大的壯族學(xué)生。這個(gè)時(shí)候,老趙緊挨著我,不吃不喝,一個(gè)勁地只顧著笑,一個(gè)勁朝我碗里夾菜。喝著喝著,小伙子們就唱起來了。他們唱壯族小調(diào),他們唱壯族最動(dòng)聽的情歌,他們抬著酒碗盯著我,讓我知道了我是他們爺爺或公公最盼望的客人。我不知所措,朝老趙望了望,老趙突然不茍言笑,這個(gè)時(shí)候,我“看見了他在這塊土地上的尊嚴(yán)”。
來了,自然要到村子周圍轉(zhuǎn)轉(zhuǎn)。黑爾真的很美,美得讓喝醉酒的我不愿醒來,栽秧的人、犁田的牛、清澈見底的小溪和小溪邊洗衣服的女人、玩耍的孩子,還有,遠(yuǎn)處的山,從山上吹來的風(fēng)以及隨風(fēng)搖擺的大榕樹。這一切,讓我想到了“棲居”這個(gè)詞,接著,我想到了幸福和滿足,我朝老趙看去,他真的就在這片風(fēng)景中,幸福和滿足著。
走的時(shí)候,老趙又變得不說話了。我搖下車窗,看見老趙眼角濕濕的,他使勁兒抹了一把,才抬起手,沖我搖搖頭。突然之間,我在想,其實(shí),我想跟他說的話和他想跟我說的話,依然沒有說清楚,我在想,也許我和他,一輩子都說不清楚了。
“那么,老趙,黑爾,我還要來的……”
王啟國志
我最幸運(yùn)的,不是作品的發(fā)表,而是在作品發(fā)表后,總是在曲靖這個(gè)小地方,要么遇上當(dāng)頭棒喝的打擊、嘲諷和咬牙切齒的嫉妒,要么遇上輕言細(xì)語的善意提醒或盼望著我再寫出好作品的那種希望。王啟國,就屬于后者。
如今,回頭看看,那些嘲諷、打擊和嫉妒的人,早就不知去向。歷史是無情的,大浪淘沙,歷史永遠(yuǎn)不會給那些心高氣傲的、心智不全的,甚至心懷鬼胎的人留一條底氣十足的“退路”,到最后,他們永遠(yuǎn)只會落得個(gè)心有余而力不足和懷才不遇的落魄結(jié)局。而我和王啟國則不同,我們的每一次相聚都是愉快的,都是碩果累累和沉甸甸的。有時(shí),在飯桌上,我們兩人就開始交換起互相的作品來,書是一本又一本,雜志是一期又一期。我們總會相視一笑,大塊地吃肉,大口地抽煙,嘴上還在油膩膩時(shí),就開始談北京的制片人、云南的歷史大家或者某一段鮮為人知、發(fā)人深省的歷史,總是說,要拍一部有關(guān)曲靖歷史文化的電視劇……我們說起這些來,都是很認(rèn)真的,因?yàn)椋覀儾皇悄欠N只說“大話”不做實(shí)事的人,我們都明白,我們說了的,就一定會去實(shí)現(xiàn)。“我們是笑到最后的人。”他說。
不記得是什么時(shí)候認(rèn)識王啟國的了。大約10年前吧。那時(shí),我的長篇小說《斑銅》剛剛在《十月》雜志上發(fā)表,我有點(diǎn)得意,總想找點(diǎn)“借口”來夸夸自己。那天真巧,一群朋友約著去一個(gè)叫越州的小鎮(zhèn)去找王啟國,我也去了。見到他,他也夸《斑銅》,夸著夸著,他說,他最近還看到了一部長篇小說,是貴州一個(gè)叫冉正萬的作家寫的,篇名叫《銀魚來》,好像是發(fā)表在《人民文學(xué)》上。我何等地敏感,回去后就趕緊找來讀。讀完后,才知道原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從此不敢再得意。
甚至,我還留下了一塊心病——《斑銅》不是好作品,我該寫出怎樣的作品才能超越《斑銅》呢?
我與王啟國就這樣交往起來了,并成為了摯友。但是,我跟他的交往,又總是透著那么幾分小心翼翼。因?yàn)椋茄芯繗v史的。或者這樣說,王啟國,是一位歷史學(xué)者。面對他,我總有一種面對歷史的感覺。
王啟國是研究曲靖地方歷史的專家。因?yàn)樗伊私饬饲傅拇蟛糠謿v史。比如,600年前的曲靖是什么樣子的,1600多年前的曲靖又是什么樣子的,爨碑的發(fā)現(xiàn)以及爨氏家族統(tǒng)治云南500年的歷史是如何輝煌的,越州“八大山人”朱耷在明末是怎樣來到曲靖并留下了怎樣的詩句……在潦滸村,王啟國一直對那兒的制陶歷史耿耿于懷,他認(rèn)為那是中國陶瓷史上輝煌的一筆。于是,他把家搬到了那兒,在那兒成立了“陶瓷文化傳習(xí)館”,建起了電窯和柴窯,親自燒制。他還告訴了我一個(gè)大秘密——我們中國制作“青花瓷”最主要的顏料,叫珠明料,產(chǎn)自曲靖。他說:“我們小時(shí)候經(jīng)常在山上看到的一個(gè)一個(gè)的坑和山洞,就是歷史上采集珠明料留下的,叫碗花洞。因?yàn)椋覀冇脕沓燥埖耐脒叺幕y,就是用這種原料燒制而成的。”
有一天,他突然打來電話,叫我去潦滸村看看。我去了,他帶著我來到一個(gè)山坡上,指著依坡而建的一排柴窯,對我說:“這是龍窯,薪火相傳了600多年。”說完這話后他看著我,問:“你不激動(dòng)?”“我激動(dòng),”我說,“我永遠(yuǎn)記住了薪火相傳600年這句話。”他說:“你該寫一部長篇小說了。”
我一直沒有寫。沒有寫的原因是怕重復(fù),萬一一動(dòng)筆,寫出第二部《斑銅》來,豈不白費(fèi)工夫?因?yàn)椋栋咩~》是寫制器的,而龍窯,也是制器,在這一點(diǎn)上,我再怎么努力,也超越不了,只好放下。我跟他說:“只有等到有一個(gè)契機(jī)。”我還找了個(gè)借口說:“歷史不是也需要契機(jī)嗎?”
王啟國不急,總是笑瞇瞇地看著我,笑瞇瞇地對待我,溫文儒雅,像個(gè)紳士。我總是在想:“歷史是不是也是這樣,笑瞇瞇地、溫文儒雅地、紳士般地看著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每次去他那兒,他總是要帶著我,在潦滸走上一圈。古街、小巷、許家大院……他帶我去看南盤江以及南盤江上的石拱橋,他指著江上略微寬闊的水面說:“潦滸的陶瓷,就是從這兒上船,運(yùn)到別處的。”
別處,就是遠(yuǎn)方。我從王啟國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更遠(yuǎn)的遠(yuǎn)方……
我知道,他一直在期待一部關(guān)于曲靖陶瓷的長篇小說的誕生,而從他對我的喋喋不休中,我感到了歷史的責(zé)任和壓力。
之后,我又去了幾次潦滸村。在他的小院里,栽種著各種蔬菜,各拔一把,就是一桌菜。要是天晴,他喜歡把飯菜端到竹林里吃。吃相和我一樣,粗糙而不文雅。這讓我想到“竹林七賢”這個(gè)詞,想起嵇康、阮籍、向秀、王戎……這些名字。王啟國當(dāng)然不是裝模作樣,他是真的喜歡這樣的心境和景致,要不然,一個(gè)人,能把家搬到那兒并住下來嗎?
可以肯定的是,王啟國在對我寫陶瓷的長篇的寬容和等待中,自己也沒有閑著。他參與了《爨文化風(fēng)采錄》《文化曲靖(綜合卷)》《文化曲靖(陸良卷)》《麒麟?yún)^(qū)文物志》《曲靖簡史》等地方歷史文獻(xiàn)的撰寫,在國內(nèi)報(bào)刊發(fā)表作品千余篇,出版學(xué)術(shù)專著《曲靖古陶志》《曲靖陶瓷史》《流淌在生命中的河流——南盤江》《曲靖史話》等。同時(shí),主持和參與云南省曲靖市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南盤江綠色經(jīng)濟(jì)帶研究》《北盤江綠色經(jīng)濟(jì)帶研究》《滇中飲水視野下牛欄江流域生態(tài)治理研究》《珠江源文化》《南盤江生態(tài)文化旅游帶研究》《曲靖古生物化石資源的保護(hù)與開發(fā)研究》《曲靖古道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等課題的研究。
除了這些,他還到處去作講座,到處去講曲靖的歷史,講越州和潦滸村的歷史。可以這樣說,曲靖沉默的歷史,是在王啟國等人不停地講解和考證中,變得喧囂和可觸摸起來。
我是說,是王啟國等這樣的一批人,告訴了我曲靖的秘密,教會了我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或者進(jìn)一步說,我因?yàn)楦麄兘煌饾u學(xué)會并習(xí)慣思考一個(gè)問題——我們該如何面對歷史?
我們該如何面對歷史?首先,我們該時(shí)刻記住幾個(gè)詞——井底之蛙、掩耳盜鈴、盲人摸象和守株待兔……在這個(gè)時(shí)代,無數(shù)的人都在重復(fù)著這幾個(gè)詞。歷史是什么?歷史是“殘酷”的代名詞,歷史是時(shí)間,是真相,是不管你怎么掩飾、偽裝,怎么往自己那張猙獰而又無恥的臉上涂脂抹粉,到時(shí)候,歷史都會把你拖到鏡子面前,拖到世人面前,清清楚楚地照出你的“妖”像來。白紙黑字,歷史會讓你一瞬間所有的企圖和所謂的努力灰飛煙滅。所以,我們每一天,都該“三省其身”,都該告訴自己,有“歷史”這個(gè)詞在,我們就該存有敬畏之心,我們就該小心翼翼,我們就該想想“恥辱”和“恥辱柱”是什么意思,我們就該說到做到,我們就該走到哪兒,不是虛張聲勢、趾高氣揚(yáng)地大聲喧嘩,而是心存敬畏地輕言細(xì)語……
因?yàn)橛型鯁蚁M约旱搅俗詈螅o我的評價(jià)是寫到做到。
我記得,在魯迅文學(xué)院上課時(shí),我的老師、《人民文學(xué)》主編施戰(zhàn)軍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歲月是河,生活是岸。”我在想,老師的這句話說的就是一種歷史觀。就是說,你的生活里,除了有“一時(shí)”,還得有“一段”。只有天生的“傻子”,才會時(shí)常去做那種“一時(shí)”的毫無敬畏之心的事,而真正的大師和大家,他們總是想到“一段”,他們總是會去想,再過10年或20年,這些“一時(shí)之事”,經(jīng)得起歲月的沖刷和拷問嗎?
歷史,永遠(yuǎn)不是圍巾,它是一條鞭子,永遠(yuǎn)會抽打出響亮的聲音……
最后說一句,我和王啟國不是經(jīng)常在一起。我們的交往方式是,很久不見,他打一個(gè)電話,我就來了……
一本書與一個(gè)人
我從來沒有見過,在一個(gè)人的葬禮上,可以發(fā)一本書。
葬禮是為了楊川舉行的,他40多歲,得了肺癌,于12月20日早上悄然去世了。書是農(nóng)民趙正云寫的,書名叫《柳葉谷的女人》。趙正云71歲了,一個(gè)人默默守在師宗縣龍慶鄉(xiāng)一個(gè)叫黑爾的地方,用另一個(gè)師宗人周茂林的話來說:“趙正云每日與山相望,與水為伴,看天高云淡,看草長鶯飛,累了,晚了,再回到小屋,伏在桌前,把那些已經(jīng)漫漶的日子,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地寫進(jìn)格子里。”
好了,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說出了這3人:楊川、趙正云、周茂林。他們3人都在師宗,都是寫小說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和我牽掛的人。半年前我就知道楊川病了,肺癌晚期,后來我又知道他做了手術(shù),再后來就沒有了音信。我一直想知道,但我一直不知道楊川小說里的那些文字是怎樣從他的手指間流淌出來的,我也一直不知道楊川是怎樣生活的,但我知道,楊川的病,是寫出來的。楊川把文學(xué)當(dāng)作自己的生命,他可以不去找工作,他可以獨(dú)守清貧,他可以每天只吃一頓飯,但是他不能不寫作。他做完手術(shù)在病床上寫,這是我在他葬禮上聽別人說的。他對別人說:“我的時(shí)間已經(jīng)不多了,我要抓緊把我想寫的寫出來。”他創(chuàng)辦了師宗甚至是曲靖第一個(gè)文學(xué)網(wǎng)站——《遠(yuǎn)方文學(xué)網(wǎng)》,他把他所有的作品和朋友的作品都放上去,因此獲得了很多快樂。我不知道曲靖文聯(lián)要出《曲靖作家文庫》的消息,會帶給他們3人怎樣的驚喜,那應(yīng)該是3個(gè)多月前的事了。周茂林想,楊川的時(shí)間不多了,應(yīng)該把這個(gè)機(jī)會讓給他。于是,他四處奔波,找來了一筆錢,要為楊川出書。楊川一聽,搖搖頭說:“還是讓趙大哥出吧!大哥已經(jīng)71歲了,要發(fā)表幾十萬字的書,作為一個(gè)農(nóng)民不容易,我們要幫他完成這個(gè)心愿。”楊川說完,就再也不說話,不管別人怎么勸,不管趙正云怎么推辭,楊川都只是搖頭。拗不過他,周茂林和趙正云含淚同意了。之后,楊川在病中收集好了趙正云所有的作品,取名《柳葉谷的女人》,交給周茂林,并囑咐周茂林寫序。再之后,因?yàn)榘┘?xì)胞轉(zhuǎn)移,楊川就真的說不出話來了。趙正云也不說什么了,從家里扛來了一口棺材,和周茂林一起,日夜守在楊川的病床邊。12月19日,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曲靖作家文庫》終于運(yùn)到曲靖,周茂林從師宗趕來,連夜把《柳葉谷的女人》帶回師宗,送到楊川的病床邊。楊川看著這本書,眼睛眨了眨,就閉下去了,再也沒有睜開。楊川走的時(shí)候,我們正在一個(gè)歌廳里唱歌,我們唱《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的鼻子犯的罪,不該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醉……”我想,這是一個(gè)時(shí)空,這是一個(gè)生與死同在的時(shí)空,這是一個(gè)高尚與庸俗并存的時(shí)空,這是一個(gè)真誠與嬌嗔呈現(xiàn)的時(shí)空。只是,到了后來,庸俗和嬌嗔都已稀釋在了寒冷的夜空中,留在我心中的,只有高尚和真誠,它們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它們在遠(yuǎn)處那盞孤獨(dú)的路燈的光暈里。12月23日,師宗下著大霧,楊川的葬禮在一塊不知道是籃球場還是停車場的地方舉行。人很少,儀式很簡單。楊川躺在趙正云扛來的棺材里,照片里的他沖我微笑著。周茂林站在楊川的妻子和女兒的身前,為楊川致悼詞,他念一段,哭幾聲,根本忍不住。念完了,他想想,指指趙正云,又說:“還沒拿到書的請來這兒拿。”那個(gè)時(shí)候,我看見瘦削的趙正云正和他的一堆《柳葉谷的女人》站在一起,默默擦淚。那個(gè)時(shí)候,我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