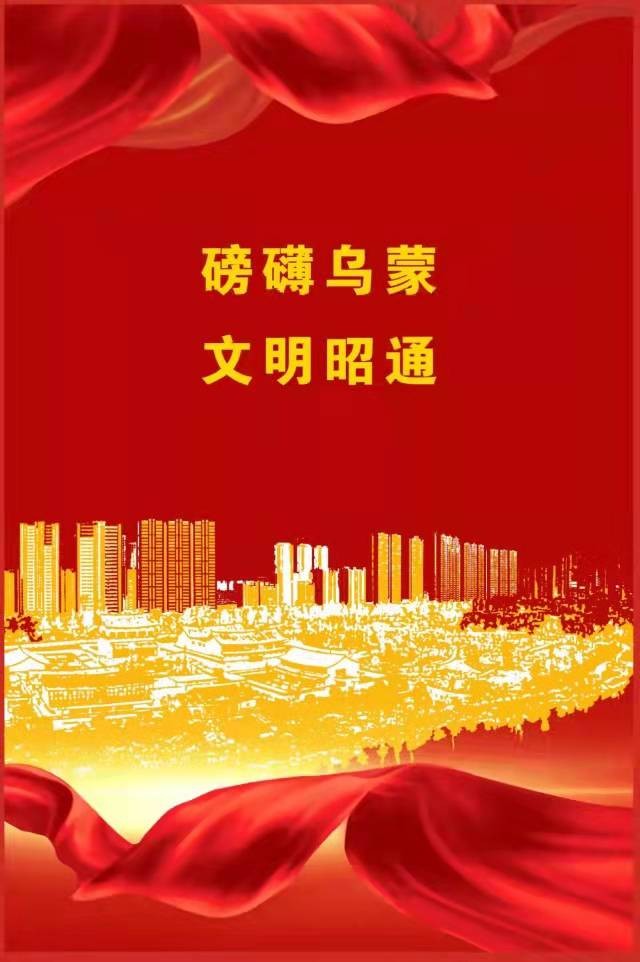2022-01-25 11:00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作者簡介:
朝 顏 女,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畢業(yè)于魯迅文學院高級研究生班。作品見于《人民文學》《青年文學》《天涯》《作品》《新華文摘》等刊物,入選《21世紀散文年選》等選本,獲得過駿馬獎、《民族文學》年度獎、丁玲文學獎、三毛散文獎等獎項。現(xiàn)已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陪審員手記》《贛地風流》。
窗外車聲喧嚷,夜色并沒有因為我的安坐陷入沉默。然而對一個作家而言,她需要學會在各種環(huán)境中開啟寫作時光。她需要耐得住寂寞,也要敵得過喧囂。
因為,選擇了文學,就沒有止步的理由。
從2009年到2021年,12年的沉浸、癡戀、執(zhí)著、堅守,一個蝸牛般緩慢攀爬的散文寫作者,方才迎來第三部散文集的問世。是的,文學幾乎消耗了我全部的熱情,但我并沒有別人想象中的高產(chǎn),也并不急于追求太多所謂的結(jié)果。也許,寫作本身對我的吸引力,更多在于那種冒險的過程。正如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所言:“沒有任何事情能像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某些時刻一樣,讓我感覺到如此幸福。”
坦率地說,寫作給予我最重要的財富,遠不是那些獎項,那些期刊上的目錄,那些一本接著一本上架的作品集。這些年,我在不停地閱讀、思考和書寫的過程中,仿佛正一點點地啄破那個困囿身心的繭,逐漸看到從未知的地方朝我涌來的光亮。它在拓寬我、改變我、打破我那些舊的觀念和思維,那些原有的對世界的認知,那些被設(shè)定的局限……或許相對于寬闊無比的世界,我仍舊蜷縮在某個小小的角落里,但文學所帶來的力量,使我有足夠的勇氣伸展肢體,繼續(xù)追逐那更加盛大的光芒。
事實上,我的寫作路徑也正經(jīng)歷著時空維度的不斷打開。從《天空下的麥菜嶺》到《陪審員手記》,再到今天捧出的《贛地風流》,正契合著從“我”到“我們”,從家族命運到家國命運,乃至人類命運的掘進過程。這其中,唯一不變的,是對文學性的追求。
作家無法選擇時代,但作家有義務(wù)記錄時代,成為時代的在場者和表達者。的確,在歷史大事件的紀念節(jié)點,文學界往往會出現(xiàn)一擁而上的現(xiàn)象,太多的眾口一詞、眾聲喧嘩,令人眼花繚亂。而我只想回歸到文學的本質(zhì),書寫所立身的這片厚土,以及跨越百年的時間中,曾經(jīng)在這里生存過、抗爭過、期盼過、熱愛過的人們,還有那些不應(yīng)被歷史遺忘的血淚悲歡。它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應(yīng)和與追隨,而是生命經(jīng)歷的累積,心血感情的噴涌。
我不會忘記,在與唯一一個用小腳走完長征路的女紅軍楊厚珍的后人交談時,內(nèi)心的痛切與震撼。她在貴州一戶農(nóng)家的牛棚里產(chǎn)下兒子,她親手將嬰兒交由陌生人帶走,她跨上馬背焦急地追趕部隊,她解開褲頭看見身子里凝固的血塊……我寫下這些,并不為著夸大或拔高一段歷史或一種信仰,而是為著銘記宏大背景下無數(shù)普通人的命運和追求。當一個原本柔弱的女子被時代的洪流漫卷,她的愛情與犧牲,她的前行和活著,便具備了某種值得祭奠的意義。
江西省社科院的評論家袁演在凌晨四點半開始了對散文集《贛地風流》的閱讀,并第一時間發(fā)來微信留言:“看完《奔跑的小腳》,感動得哭了很久。可能是同為女性的身份,你作為寫作者,我作為閱讀者,都更多了一層感同身受……”
我又想起前幾年,天津作家武歆來到瑞金,對我們講述在博物館偶然看到楊厚珍裹著小腳的照片時,心靈上經(jīng)受的強烈震蕩。他喝了一些糯米酒,在微醺中反復(fù)喃喃自語:“我淚流滿面啊,淚流滿面……”說著,他的眼淚又流了下來。由此我想到,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觸動我們的,還有特殊年代特殊群體所承受的身體和精神的極限考驗。
我也不會忘記,在清明的雨聲中,我和開國大校彭金高的嫡孫進行了整整一天的對話。那一天,習慣午睡的我并沒有感到疲倦。在百度百科里,在史書上,留給彭金高的僅僅是一小段生平簡介,而他九死一生的傳奇,他在雪山草地、槍林彈雨中的艱難與幸運,恐懼和勇氣,也許最終會成為永久的空白。他是英雄,同時也是別人的兒子、丈夫、父親、祖父……他的故事,他生命的諸多細節(jié)該如何被時間印刻,被后人回味?
是故,我希望我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個體的人,有生命的、有呼吸的人,而不是那種夸大失真的、單一扁平的英雄人物。我所呈現(xiàn)的,應(yīng)該是文學的,人性的,能引發(fā)各個時代讀者共鳴的故事和細節(jié)。如此,方能直抵人心,客觀反思歷史,映照社會生活,并釋放啟發(fā)當下的力量。
同樣,那些屬于我的生活,以及與我同時代人所親歷的命運嘩然反轉(zhuǎn),它們都應(yīng)該被烙印在歷史的進程里。我正在聽見、看見,觸摸到和感受到的一切,我想要真實地記錄萬千面孔、萬種情形、萬類話語,并在其中寄托自己的創(chuàng)作理想和精神。
100年,在浩瀚的時空中顯得如此短暫,而它留下的人類生存和追求史又如此豐富。廣義而言,所有的記錄都應(yīng)該被賦予價值,而我在盡量找尋一種可能,即《贛地風流》是可以超越地域,超越民族和超越某種旋律的。我希望,近20萬字的作品,能夠用人文的力量,抵達人心相通的部分。也許這只是一種自夸抑或妄想,但至少表明了我對文學的一種立場。
在瑞金市紅軍巷90號,我有固定的一張書桌和一臺電腦。這些年,除了吃飯、睡覺、出差,我將生命的大部分時間都寄存在這里。一個人安靜地待著,或者思考寫什么、怎么寫,或者心無旁騖地碼字,或者打開文檔進行校對和修改。我發(fā)現(xiàn),當我真正沉醉于寫作時,所有的喧嘩都會在意識里退后,只留下與電腦和鍵盤相伴的美妙時光。感謝中國作協(xié)對這部作品的厚愛,感謝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平臺,同時也感謝創(chuàng)作過程中所有給予我?guī)椭椭С值娜恕?/span>
選擇了文學,就不會停止探求。我愿意這樣活著,寫著,永不設(shè)定終點。
茶亭沉浮錄
我知道我不能再用舊時的眼光來打量眼前的這座茶亭。
長亭、古道、芳草……那些詩意的惹人遐思的畫面,已經(jīng)全然與它無關(guān)了;茶水、長椅、歇腳的人……那些鄉(xiāng)土得讓人懷念的溫情,也與它無關(guān)了。
或者應(yīng)該說,它已經(jīng)不是茶亭,充其量只能算是茶亭的遺址和廢墟而已。它是頹敗的,墻體只剩下殘缺的三面,高度不足兩米,像個遲暮的老人,向著大地矮下身去。屋頂更無從說起,一爿地豁然地向著天空敞開,任由陽光和雨露將地面上的草籽滋養(yǎng)成一團放肆糾纏的亂麻。倒塌下來的青磚和條石亦未能幸免,每一塊都爬滿了青苔與草藤。秋陽穿過殘損的瓦片,穿過僅存的一道圓拱形門,照在凌亂傾斜的杉木柱頭上。
此地名喚“楓垇里”,位于瑞金與長汀交界的山嶺間。聽說,它叫“上茶亭”,多么隨遇而安的名字,只因其坐落于山頂,與山腰的茶亭對應(yīng),便隨口叫了上茶亭。它大約建于明末年間,曾經(jīng)連接著從江西通往福建的古驛道。可以想見,在安步當車的年月里,多少人曾以此為驛站,安頓周身的疲憊;多少人曾以此為地標,等待或迎接生命中的親人。
在廣袤的贛閩粵山區(qū),驛站驛道,曾經(jīng)遍布著這樣的茶亭。它們供行走的路人遮風擋雨、歇腳休憩,故又稱涼亭、風雨亭。茶亭密集處,幾乎每隔幾里路便可見一座。修建茶亭的人,可以是官府或鄉(xiāng)紳出資,也可以由村民集資。講究些的,用青磚條石砌就,雕梁畫棟;粗糙點的,可以是土夯泥筑,茅草遮檐。但無論如何,總有幾張以資將息的長凳,總有一個將風雨烈日擋在外頭的屋頂,炎炎夏天也總有善心者燒好的茶水。過往行人多的地方,還長年有賣米酒的,賣小吃的人擺攤。那些跋山涉水挑擔行走的人,那些販貨經(jīng)商趕圩赴會的人,那些翻山越嶺走親訪友的人,總能在茶亭里獲得容留與安慰。試想,當一個人孤獨無依地走在山路上,驕陽似火,唇舌焦渴,此時得遇茶亭,是怎樣一件驚喜的事情?若遇傾盆大雨,奔進茶亭躲避一下,望著茶亭外密集的雨簾,又是怎樣一種欣慰的情狀?當然,若是囊中有幾文小錢,于茶亭里沽一壺客家的米酒,那又更是一番酣暢了。
在我的家鄉(xiāng),茶亭二字還被廣泛地運用于地名地標。譬如“新茶亭”“老茶亭”“茶亭下”“茶亭街”等。由此可見,茶亭是怎樣深刻地鍥進了尋常百姓的生活中。
其實,這些驛站的茶亭,與歷史上那些用以觀賞的亭子顯然不在一個類別上。諸如滄浪亭、醉翁亭、愛晚亭等,那是風雅之人游山玩水、吟風弄月的去處,它們與窮苦百姓的生活不大沾邊,只為點綴名山勝水、四時風景。它們的名字在文人的吟詠下披上了詩意的頭巾,文化氣息亦隨著時日的增長愈沉淀愈濃厚。如歐陽修的一篇《醉翁亭記》,便讓一座亭子名聲大噪。而大余縣的牡丹亭,則因了湯顯祖的戲劇《牡丹亭記》名貫中外。如果說那些歷史名亭是“陽春白雪”,那么這些安頓在贛閩粵山區(qū)的茶亭則是不折不扣的“下里巴人”了。
單看茶亭的名字就可發(fā)現(xiàn)端倪,如“普濟亭”“施恩亭”“積德亭”,它們拙樸如斯,甚至不需要經(jīng)過反復(fù)推敲,張口便是一個,無外乎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內(nèi)涵與外延。的確,它們關(guān)乎著仁愛、善良,關(guān)乎著烙印在中華民族骨子里的寬厚與普濟情懷。
一座平常而拙樸的茶亭,卻成了父親的救命恩人。20世紀80年代,父親是一名鄉(xiāng)村電影放映員。為了保證影片常新,他不得不每日翻越石羅嶺,去到縣城換片子。為了節(jié)省開支,父親每次騎著自行車翻坡爬嶺。忽一日,騎行至急彎陡坡處,他發(fā)現(xiàn)剎車片失靈了。這時候,人的重量加上片子的重量,形成強大的慣性,像一陣瘋狂的龍卷風,裹挾著人和車向坡底俯沖而下。車子已經(jīng)完全失去控制,隨時有可能載著父親撞車或者翻沉深淵。幸而此時陡坡邊出現(xiàn)一座茶亭,父親立即掉轉(zhuǎn)車頭,朝茶亭撞去。瘋狂的旋風在一座茶亭面前靜止下來,父親傷痕累累,卻終歸沒有生命危險。事后,父親專門找到建茶亭的人,表示了鄭重的謝意。我相信,從那以后,茶亭在父親的生命中又多了一層別樣的意義。
全家搬到市區(qū)生活后,父親回老家還要乘車從那座茶亭邊經(jīng)過。茶亭舊了,裸露著土黃色的沙墻,灰撲撲的樣子。需要它的人已經(jīng)不多,它存在的意義或者只在于一種風尚的沿襲罷了。我猜想,當父親看到那座茶亭的時候,一定會想起當年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一定會觸動一些慨嘆,并讓他銘記一份福緣。后來,我發(fā)現(xiàn)茶亭文化的印痕果真是深深地烙在了父親身上。他樂善好施,心懷悲憫,大半生都熱衷于修橋補路、捐資賑濟,為一籌莫展的村鄰出謀劃策。這些年,來自麥菜嶺的鄉(xiāng)親進城辦事,或外出打工,總喜歡在父親的家里停下,吃頓便飯、住上一晚是常有的事。父親從未嫌過麻煩,總是熱情奉迎。從某種意義上說,父親的家,于麥菜嶺的鄉(xiāng)親,如何不是一座佇立在城里的茶亭?
少年時期,我從麥菜嶺出發(fā),去往外婆家,總要在石羅嶺的茶亭里作短暫的停留,喝上一碗新鮮的涼茶水。我記得,山頂?shù)哪谴迸f屋里,曾經(jīng)住著我遠房的姑婆。多年以前,她唯一的兒子去了臺灣,從此她便守著老屋和茶亭一個人孤獨地生活。她每日挑來山泉水,燒開,放上一些曬干的魚腥草,供過往路人飲用。這樣的涼茶是不收錢的,路人想喝多少碗就喝多少碗。姑婆活到80多歲,算是高壽。人們都說,她一輩子施茶,是行善積德修來的壽年。她死后,就葬在屋旁的山上,依然日復(fù)一日地望著那座茶亭。
現(xiàn)在,石羅嶺上最后一家人也搬進城了。而我們再也不用徒步穿越荒山野嶺,再也不需要他們施舍的涼茶水了。茶亭離我們越來越遠,那些用腳力丈量大地的日子也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一條寬敞的公路環(huán)繞著石羅嶺蜿蜒而下,一些中巴車、小轎車、摩托車終日在公路上盤旋往復(fù),載著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忙忙碌碌的人,還有誰會停下腳步,在山頂?shù)牟柰硪淮斡崎e的小憩呢?一箱一箱的飲料、礦泉水走進了千家萬戶,連最偏遠閉塞的山里人家,也能拎著色彩鮮艷的橙汁或雪碧回家,還有誰需要去茶亭里喝上一碗好心人施予的水呢?
唯有被茶亭加持過的善念,還在人間一程一程地傳遞著。
相關(guān):

作者:朝 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