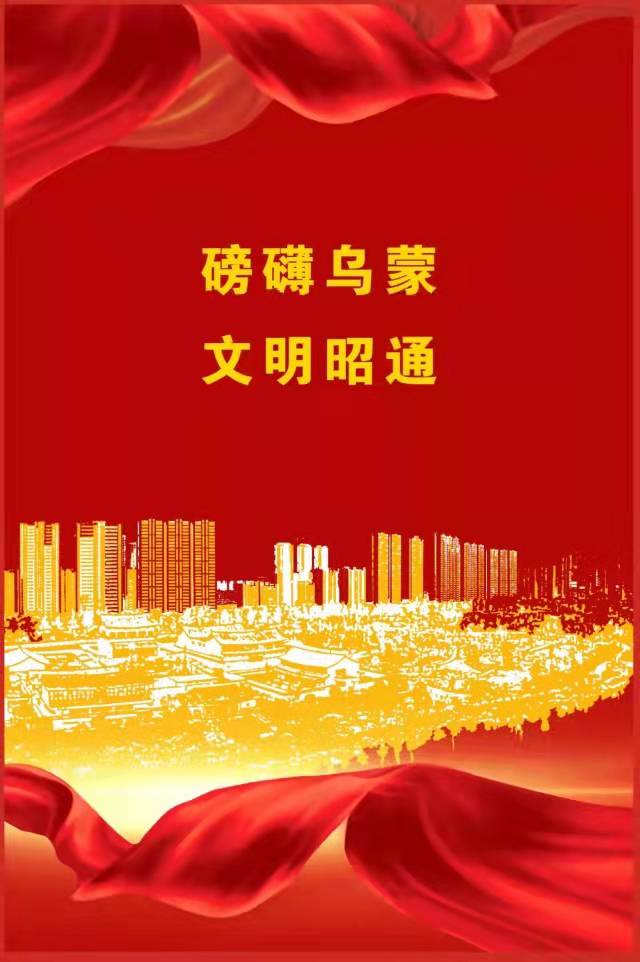2023-07-03 09:48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2015年,威信縣高田鄉(xiāng)文化站站長古祥杰開始游走在大山之上河流之側的村子,與村民拉家常,不斷講一些對于村民來說有用或者無用的那些農具的意義。如果運氣好,他會帶走一些器具,比如蘆笙、背篼、桐油燈、石磨等。
幾年之后,文化站辦公樓一樓 70多平方米的房間堆滿了從各個村子收集到的農具1300件。推開一樓展示廳的大門,猶如打開一部川滇交界處的農耕文明百科叢書。
“這是搶救性的收集,如果不及時收集,這些農具或許被隨意丟棄,也或許被付之一炬。”古祥杰說。
當各式各樣的生產(chǎn)生活用具集中出現(xiàn)在一個地方,它們的價值被走進展廳的人認同或者認知。
“每一件農具都有它的使命,當我們復原這種使命時,我們往往看到,它其實隱藏著村民的生存密碼。”2023年6月11日,古祥杰拿出一個竹編的錐形油壺,邊講解邊感嘆。
高田鄉(xiāng)地處威信縣境東部,與四川省敘永縣、興文縣接壤,地形多為二半山區(qū)摻雜部分河谷區(qū)和高二半山區(qū),境內最高海拔 1902 米,最低海拔 760 米,有大小河流9條。
山脈與河流交織,讓展廳的農具豐富多樣。
高田鄉(xiāng)下轄8個村委會,魚井村位于海拔最低處,古祥杰就出生在那里。

王銀飛老人打開柜子,在眾多的紡織服飾里,找一條裙子穿上。
一間“雜亂”的農具陳列室
6月11日,高田鄉(xiāng)新華村羅漢山村民小組的一間農家小屋。
王銀飛老人慢慢從腰間取出一串鑰匙,向小屋內最靠墻的一個老式柜子走去。柜子是木質的,表面的木漆已經(jīng)脫落,失去了原有的光澤。打開木柜子,王銀飛老人費了一番周折。因為柜子被兩把鎖——兩把農村里極為普通的舊式掛鎖鎖住。老人先是用一把鑰匙打開外面的一把鎖,再用另一把鑰匙打開另一把鎖。
老人小心翼翼地揭開柜蓋,從柜子里取出一捆一捆的東西擺放在柜子右邊的床上,慢慢展開。
像變戲法似的,從陳舊的木柜里拾出的15捆麻織品,有百褶裙、挑花圍腰、包裹得非常嚴實的蠟染、青衣、麻布……
當老人拿到一條花邊圍裙時,情不自禁地把圍裙系在腰間, 臉上也露出久違的笑容。
“這些東西,都是我用擺在文化站那臺織布機親手織出來的。”說起那臺織布機的故事,老人一臉自豪。
威信縣東北部的南廣河,發(fā)源于高田鄉(xiāng)鳳陽村海拔1902米的楊龍灣梁子,從東南往西北經(jīng)過鎢城流經(jīng)高田,造就一路山清水秀,高田鄉(xiāng)因高山上有梯田而得名——高田。
南廣河流經(jīng)高田時,兩山夾峙之間,忽然閃出一塊空地,高田鄉(xiāng)文化站就坐落在這里。
王銀飛老人念叨的那臺織布機,擺放在文化站一樓的陳列室。
陳列室面積大約75平方米,陳列的農耕器具沒有給人留下太多的參觀空間。
“這件物品是老百姓制作的蠟罐,把石蠟融化后,倒在陶罐中,把竹簽裹上草紙做成蠟簽,把蠟簽倒立放置在蠟罐中,約2秒后,蠟浸透蠟簽,反復幾次,蠟簽便裹上一層厚厚的蠟,就成了蠟燭。”
“這是倒甑,主要是用來蒸菜籽面的,與蒸飯的木甑使用方法不同,使用時,一般大口向下,小口向上。”
站在狹窄的過道上,古祥杰隨手拿起一件器具都如數(shù)家珍,各類器具似乎也在靜靜地聽他講一段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歷史。
展廳里還有苗族同胞使用過的蘆笙、嗩吶、月琴、二胡。樂器旁邊,則是用于狩獵的獵槍、獵網(wǎng),還有漁網(wǎng)。地理區(qū)域的差異性產(chǎn)生生活方式的不同性,從而也帶來生產(chǎn)生活工具的多樣性。
2015年底,脫貧攻堅戰(zhàn)開始了,古祥杰下鄉(xiāng)開展工作時發(fā)現(xiàn),老百姓拆舊房蓋新房,很多農耕用具被閑置下來,加之修通了公路,通了電,背篼、馬鞍、桐油燈、石磨、碓窩等再也派不上用場了。老百姓隨意地把這些使用多年的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具放在角落里。古祥杰意識到,這些老物件如果不抓緊收集,過些日子,就會被老百姓扔掉或燒掉,太可惜了。干了多年的文化工作,古祥杰知道這些老物件承載著很多文化信息,甚至就是村莊的一種記憶。于是,他立即行動起來,千方百計收集老物件。日積月累,積少成多,僅僅半年多的時間,各種老物件就擺滿了一屋子。
2016年夏天,古祥杰把收到的物件進行分類陳列,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農耕文化陳列室。
陳列室里最大的老物件,是苗族同胞使用的織布機。現(xiàn)在,陳列室的中間擺放著4臺織布機,其中1臺織布機上還有未織完的布匹。
織布機是苗族同胞的傳家寶,村莊和寨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身上穿的苗族服裝,都是這幾臺織布機織的。

古祥杰拿起一盞桐油燈,如數(shù)家珍般介紹桐油燈的功能、設計。
從收集第一臺織布機開始
2015年底以來,古祥杰已經(jīng)收集或征集了1300件農耕老物件。陳列室里擺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文化站里擺放的第一件老物件就是那臺還掛著半截布匹的織布機。
對征集第一件老物件時的情景,古祥杰記憶猶新。
古祥杰是苗族,家住魚井村何家咀。他的姑父熊宗銀一家住在新華村羅漢山。小時候,古祥杰常去姑父家玩,看到姑父、姑姑一年四季都在為遠鄉(xiāng)近鄰績麻織布,他對此印象很深。
古祥杰決定從他的姑父那里入手。
羅漢山距高田村18公里,海拔1350米,位于新華村,村子里全是老房子,村民全是苗族。
2015年冬天的一個陰冷的日子,天下著蒙蒙細雨。古祥杰沿著泥濘的道路抵達姑父家時,心里十分矛盾。因為那天,年邁的姑姑還在織布機上忙個不停,為村里的老鄉(xiāng)績麻。
“姑父、姑姑,高田鄉(xiāng)文化站要建一個農耕文化陳列室,你們把這臺織布機送給我嘛!”左思右想,古祥杰還是開了口。
“不給!祥杰,這臺織布機是你姑父親手制作的,跟隨我們大半輩子了,是我們的傳家寶,你以為你想拿去就拿去?”姑姑一點面子也不給。
古祥杰還是不放棄,他厚著臉皮,繼續(xù)做工作。
“姑父,現(xiàn)在生活條件好了,你看,寨子里的年輕姑娘、年輕小伙穿的衣服都是城里的織布機織的,請你們織布的已經(jīng)很少了。你就當幫我一個忙,把這臺機子送給文化站。如果你們想織,也可以到文化站去織的嘛……”
架不住古祥杰的軟磨硬泡,姑父終于軟了心,并做通姑姑的工作,兩人答應了。古祥杰擔心姑父、姑姑反悔,當即找了輛農用車,在姑父的幫助下,把織布機運到了文化站。
王銀飛老人就是古祥杰的姑姑。她在17歲時,從威信縣舊城鎮(zhèn)嫁到羅漢山,已經(jīng)51個年頭。這臺丈夫親手制作的織布機,在過去困難的時期,成為家庭經(jīng)濟收入來源,而且也得到鄉(xiāng)鄰的尊重。
“你們每年能織多少布?”
“記不清了。一般來說,一條裙子要3丈,衣服要6尺,這樣算,一天可以織兩三丈。”
“來找你們織布的人多嗎?”
“以前很多。村里有52戶人家,每年都會送麻來給我們織,甚至外村的也有送麻來織的,多的時候,一次要織10多丈。一年四季都忙不過來。”
“你們做一次要收多少錢?”
“我們基本沒有收錢。以前,大家都窮。鄉(xiāng)親們有時帶點小東西來,當時值10多元,相當于現(xiàn)在的一兩百元。”
“織布機送給文化站,你后悔嗎?”
“后悔!”
頓了一頓,老人又說:“這臺織布機陪伴了我們大半輩子。后來,城里有了新的織布機、縫紉機,績麻的年輕人少了。自從織布機搬走后,我到文化站去織了3次。后來,再也沒有去織了。但每次到高田趕場,我都要去文化站看一看那臺機子。即便古祥杰不在,我也要站到窗子外,隔著窗簾看一看。”

冒鼓苗寨。
山川與河流造就農耕智慧
高田鄉(xiāng)距威信縣城28公里,轄鳳陽、大灣、鎢城、高田、坡上、魚井、馬家、新華8個行政村163個村民小組7373戶31927人。
古祥杰,1999年參加工作。2003年12月,任高田鄉(xiāng)文化站站長。
從征集到第一臺織布機起,古祥杰一邊參與脫貧攻堅工作,一邊著手收集農耕器具。古祥杰走到每一個村子,都會留意每戶村民有沒有閑置下來的老物件,發(fā)現(xiàn)有比較獨特或者之前沒有收集到的物品,他都要停下來,與老鄉(xiāng)們商量,請老鄉(xiāng)把物件送給文化站,如果老物件是大件或者老鄉(xiāng)們不情愿送的,他就會軟磨硬泡,對方實在不愿意,他會主動買一兩條煙或者打點酒來與主人家交換,直到對方把老物件捐出來。
當脫貧攻堅全面推進時,古祥杰也同步加快了收集老物件的進度。收集老物件最多的一次是在大灣村的冒鼓苗寨。
冒鼓苗寨是一個自然村,分上鼓苗寨、中鼓苗寨、下鼓苗寨,是高田鄉(xiāng)最遠的一個自然村,就在文化站對面的高山上,由于山高谷深,需要從山的這一面繞到山的另一面才能到達,有25公里的路程。
冒鼓苗寨實際上應該是木鼓苗寨,因為寨子里有一棵兩三百年樹齡的楠木,被全寨的人稱為神樹。這棵楠木現(xiàn)有30多米高,枝繁葉茂,最奇特的是,距樹根2米高的地方,楠木中空,用手或木頭拍打樹干,會發(fā)出“咚咚”的響聲,因此,老百姓稱之為木鼓樹,而這幾個苗寨也被稱為木鼓苗寨,因當?shù)厝藭涯咀帜顬椤懊啊保枚弥脱葑優(yōu)椤懊肮拿缯薄?/p>
海拔1330米的冒鼓苗寨,村民小組長陶文發(fā)居住的房子多少保留有古建筑的影子,而他使用了多年的一些用具,當脫貧攻堅改變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他把它們送給了高田鄉(xiāng)文化站。
除了把家里大斗、大木盆還有馬鞍捐給文化站,陶文發(fā)同時動員村民把不用的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具捐給文化站。古祥杰說,他在冒鼓苗寨收到的老物件最多,除了生產(chǎn)工具,還有砂鍋、油罐、木桶、箱子、柜子、碓窩等,占文化站至今收集到的老物件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當時,裝了滿滿一車。
陶文發(fā)說,每次看到捐贈的馬鞍、油燈,就會想起沒有修通公路之前的日子。那時,從苗寨到鄉(xiāng)上,走的是山路,到山上種莊稼,到煤廠運煤,都離不開人背馬馱。以前,各家各戶都點煤油燈,晚上看小人書,燈光微弱,看也看不清楚。現(xiàn)在好了,電通了,電燈亮了,煤油燈也用不著了。
6月12日中午,離開冒古苗寨時,古祥杰告訴陶文發(fā),過幾天,他要上來把今年的花山節(jié)組織好,同時,再到村子里去看一看,對那些保存著鄉(xiāng)村文化符號的老物件再進行收集。
古祥杰最近一次收到的老物件,是幾件蓑衣。高田鄉(xiāng)水田多,20世紀80年代,全鄉(xiāng)有上萬畝,現(xiàn)在,也還有5000多畝。他發(fā)現(xiàn),陳列室里缺少農村最常見的避雨工具——稻草蓑衣。2022年秋天,他到收完稻谷的田里,背上幾捆稻草,請已經(jīng)90歲的楊文強做了一件稻草蓑衣。
“當這些老藝人‘走’后,這種稻草蓑衣就再也找不到了。”古祥杰說。
“正月荷包繡起頭,繡起荷包想送郎。你要荷包你拿來,五顏六色繡龍頭。”6月12日上午,高田鄉(xiāng)文化站二樓,馬家村65歲的張如富帶領鄰近幾個村的隊員演唱民間小調《荷包歌》。

高田鄉(xiāng)文化站民族聲樂隊能演奏的民間小調近50余首。
2014年,古祥杰開始收集高田的民間小調,成立了高田鄉(xiāng)文化站民族聲樂隊,一人獨唱、兩人對唱,四人伴奏,民間小調得以傳承下來。
古祥杰認為,不管是對農耕器物的收集,還是對民間小調的挖掘,都寄托了老百姓對村莊的依戀。其實,他最初只是想收集糧票、布票,后來,發(fā)現(xiàn)村子里每一件東西都是有用的。2017年,他在大灣村收到一個竹瓶,把竹子剖開,用細藤編織成瓶狀,用來裝南瓜籽,瓶口則就地取材,用玉米芯來封塞。老百姓如此心靈手巧,小作品中有大智慧。
在高田鄉(xiāng)文化站一樓的農耕文化陳列室里,隱約可以聽見二樓傳來的音樂聲,1300件農耕用具和50余首民間小調相呼應,告訴每一個到來的人,在生產(chǎn)力落后的時代,世居村莊的村民,在靜止的山脈和奔騰的河流間,如何依靠智慧而生存,如何創(chuàng)造出農耕文明的溫暖。

昭通日報記者:曹阜金 汪舒 通訊員 申麗琴 文/圖/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