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0 11:00 來源:昭通新聞網(wǎ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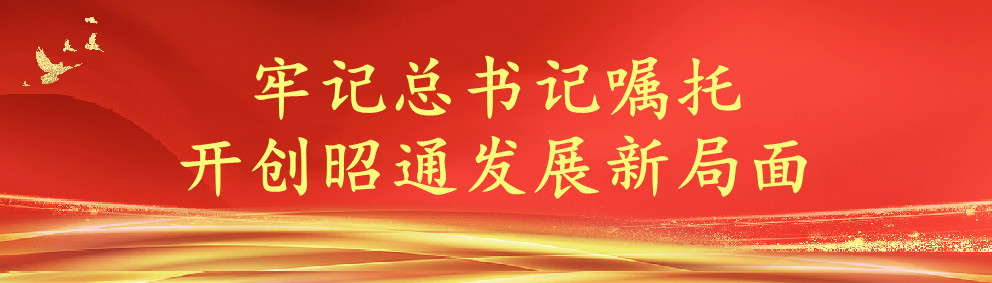


在滇東北烏蒙大地的褶皺里,鎮(zhèn)雄縣城以一種粗糲的溫柔包裹著萬千滋味。這里的地脈風物,在亞熱帶季風氣候與紅壤的共舞中,孕育出豐饒的物產(chǎn)。
鎮(zhèn)雄世居居民與外來居民飲食習慣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創(chuàng)造了獨具特色的鎮(zhèn)雄美食,也積淀了豐富多彩的美食文化。酒事也好,宴席也罷,箱子街、鹽行街、董家灣……這些令人魂牽夢縈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小攤子林立,食客們目光交匯,桌上杯盤橫斜,說得出名字和說不出名字的各種美食,都有一段難忘的故事。
正是這方被自然偏愛的土地,讓鎮(zhèn)雄人的餐桌成了山河歲月的具象化表達。
“九大碗”里的百年時光
鎮(zhèn)雄菜有烏蒙腹地陰雨彌漫中的粗獷和隱忍,是時光發(fā)酵后的提煉與深化。“九大碗”是鎮(zhèn)雄民間酒事的特定符號,是婚喪嫁娶等諸多酒席中最美麗的盛宴,也是鎮(zhèn)雄最傳統(tǒng)的筵席。
顧名思義,“九大碗”就是9個裝在大碗里的菜。但實際上,廚師會根據(jù)菜品的分量,靈活選用大碗、中碗、小碗或大盤、小盤等餐具,不過菜品數(shù)量不得少于9個。
婚喪嫁娶是人生大事,用“九大碗”招待客人,是最有面子的事。民間酒席往往是全村總動員,主人家會邀請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幫忙。在稍微寬敞的地方搭起簡易廚房,支好案桌和案板,就開始埋鍋造飯。燃得很旺的爐灶上,架著大大的鐵鍋、高高的蒸籠,眾人七手八腳地做起菜來。
鎮(zhèn)雄“九大碗”既充分發(fā)揮了廚師的創(chuàng)造性,又兼顧了主人家的經(jīng)濟實力。由于各家經(jīng)濟狀況不同,提供的食材也各有差異,廚師們會根據(jù)主人家的安排和食材來烹飪菜肴。因此,各家辦的“九大碗”都不盡相同,但墩子肉和扣肉是必不可少的,這是“九大碗”的標準之一。
鎮(zhèn)雄“九大碗”是鎮(zhèn)雄廚師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鎮(zhèn)雄味道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深受鎮(zhèn)雄人的喜愛和推崇,能滿足不同人群的口味,一般包括干盤菜、涼菜、蒸菜、炒菜、湯菜等。干盤菜通常有炸花生米、炸洋芋片、炸蝦片等,屬于下酒菜;涼菜分葷素,葷的有鹵豬耳朵、豬香嘴、豬肝等,素的有涼拌折耳根、白蘿卜絲、涼三絲等,屬餐前小吃,是激發(fā)客人食欲的。上蒸菜時,會先上一個蓋面菜,最早是碗底放豆芽,上面用切片的豆腐干或者酥肉蓋住。接著就上墩子肉和扣肉。墩子肉和扣肉是宴席中的高檔菜肴,做法比較考究,工序較多。做好的墩子肉和扣肉香氣撲鼻,客人早已按捺不住,神速下筷,吃得嘴角流油。
除了墩子肉和扣肉,民間酒席中最高大上的菜肴當數(shù)“膀”,即豬的前腿上肉質最細膩的部分,通常專門給接親和送親的主客吃,屬于額外加菜。吃過“膀”的人,大多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回味其絲滑爽口的味道。蒸菜中還有蒸小酥,深受孩子們喜愛。炒菜有瘦肉炒胡蘿卜絲、蒜薹炒肉、木耳炒肉、麻婆豆腐等家常菜,百吃不厭。湯菜比較豐富,有海帶湯、胡蘿卜粉絲湯、蹄花湯、排骨湯、三鮮湯、圓子湯、紅豆酸菜湯、苦菜湯、白菜湯等。
“九大碗”是與時俱進的。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九大碗”的食材更豐富,做法不斷改進,檔次和品味也不斷提升。如今“,膀”不再是稀罕物,雞、鴨、魚、牛肉、羊肉等食材走進尋常百姓家。涼菜更注重品質,有口水雞、涼拌雞、烤鴨等,還有牛、羊肉制品,更多的是把多種涼菜做成拼盤,形態(tài)美觀、花樣翻新、品種豐富,色香味俱全,客人看著就很有食欲,也吃得高興、滿意。
蒸,能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味道、形態(tài)和營養(yǎng),所以“九大碗”如今主要采用蒸的烹調(diào)方式。不僅雞、鴨、魚變成了蒸菜,而且蹄花、豬肘等湯類也是蒸出來的。這些蒸菜含水量高、軟糯滋潤、營養(yǎng)豐富、口味純正、原汁原味、味鮮湯清,充分體現(xiàn)了“九大碗”的特色。曾經(jīng)的王牌蒸菜墩子肉和扣肉,現(xiàn)在食材已經(jīng)引進五花肉來做了。五花肉肥瘦相間,肥肉遇熱易化,瘦肉久煮不柴,吃起來讓人回味無窮。炒菜在原有基礎上,食材更加豐富,新增了肚條炒萵筍、牛肉炒芹菜、油炸大蝦等。湯菜做法變化大,現(xiàn)在流行大酥湯、蹄花湯、排骨湯、圓子湯、紅豆酸菜湯。大酥湯顏色金黃,湯鮮、肉酥、味醇香,有時還加入新鮮蔬菜,極具鎮(zhèn)雄特色。
以前,吃“九大碗”是一件很期待、很幸福、很自豪的事情。記憶中的炸花生米、炸洋芋片、炸蝦片,在那個沒有零食的年代,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墩子肉和扣肉是客人們最期待的菜肴,它們一抬上桌,香味便撲面而來,讓人忍不住下筷。
吃“九大碗”是鎮(zhèn)雄社交聚會的一種形式,以前稱作“打牙祭”。如今,“九大碗”的蒸菜里多了鮮甜的海鮮,炒菜中多了松茸的身影,但最讓人念念不忘的,仍是墩子肉在齒間化開的豐腴,以及海帶湯的甘甜。當游子在異鄉(xiāng)的餐館點上一桌改良版“九大碗”,當網(wǎng)商將鏡頭對準翻騰的蒸籠,鎮(zhèn)雄味道正以全新的姿態(tài),在時光的長河里泛起新的浪花。這桌盛滿人間煙火的筵席,滋養(yǎng)著一代又一代鎮(zhèn)雄人的味蕾與鄉(xiāng)愁。
三鮮米線里的鄉(xiāng)愁
曾有離鄉(xiāng)多年的鎮(zhèn)雄人在日志中寫道:故鄉(xiāng)的米線,是我剪不斷的鄉(xiāng)愁。鎮(zhèn)雄人對米線的依戀近乎固執(zhí),就像蜜蜂依戀花朵一樣。米線成了大多數(shù)鎮(zhèn)雄人的驕傲,不管在什么地方,鎮(zhèn)雄人最想尋找的,就是一碗熱氣騰騰的三鮮米線。
鎮(zhèn)雄米線絲滑柔軟,韌性十足,不易折斷。其獨特的質地,曾讓一些外地人懷疑米線作坊在制作過程中添加了特殊的膠水。后經(jīng)質監(jiān)部門實地查驗,這一說法被證實純屬謠言。
早在20世紀80年代,縣城西門口的“魯家米線”就享譽鎮(zhèn)雄。清晨,上班的人們陸續(xù)涌入“魯家米線”館,找一張空桌坐下,然后喊道:“來個中碗。”灶臺旁,一位系著圍裙的中年婦女回答:“要得。”幾分鐘后,米線便端上了桌。客人放些蔥花、芫荽,又加入少許醬油和醋后,拿起筷子攪了攪,便大口吃起來,吃得滿頭大汗。吃完米線的人擦擦嘴,付了錢,連忙起身讓出座位。站在門外等候的人群中,立刻有人“嗖”地沖進來,一屁股坐在余溫未散的凳子上,高聲喊道:“我要一份大碗米線,加1元的肉……”
“魯家米線”是鎮(zhèn)雄的老牌三鮮米線。縣城擴建時,米線鋪子被迫拆除,魯氏不愿再經(jīng)營,便關閉了米線館。沒過多久,縣城里開起了很多家三鮮米線店,其食材、配方、做法均與“魯家米線”一樣,但吃起來卻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米線雖為小吃,但鎮(zhèn)雄人卻把它當成主食,有的人甚至吃上了癮,早上米線,中午米線,晚上還是米線。從灶臺到餐桌,一碗米線的制作只需兩三分鐘;而經(jīng)常吃米線的人,吃完一碗也才四五分鐘。如此一來,他們便能節(jié)省出大把的時間,去為生活奔波忙碌。長期吃米線的人大多互相認識,當三五好友聚在一起,有人提議:“走,甩一碗米線去。”大家便來到常去的米線店,邊吃邊分享著縣城里發(fā)生的稀奇事。
三鮮米線的做法看似簡單,實則相當復雜。其湯汁很考究,要選用當日新鮮的豬骨頭,再加入草果、丁香和八角等作料,這樣熬出來的湯汁清澈透明,表面浮著一層油,香氣撲鼻。
米線是鎮(zhèn)雄本土的作坊生產(chǎn)的,原料考究,做工精細。制作好的米線被一圈圈地卷成蒲團般的形狀,擺在案板上。生意火爆的米線店,不僅頭天晚上要進米線,清晨也要補貨。
食客進店,報了份數(shù),店家隨即吩咐煮米線的工人“幾個大碗、幾個中碗、幾個小碗”。熬好的湯汁放在灶臺邊,煮米線時,工人先舀一瓢湯倒入一個大鐵勺中,再將鐵勺置于爐口,火焰瞬間將湯汁燒得滾沸。只見工人一手從大小不等的鋁鍋里抓出切好的配菜放進鐵勺里,一手從碗里拈起一坨剁細的肉泥,也放進鐵勺里,再拿一圈米線蓋在上面。不一會兒,沸水漫過勺沿,工人用筷子在勺內(nèi)攪動幾下,再煮幾秒,便從爐口端下,倒進一個大碗中。工人轉頭問客人:“辣椒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客人回答:“適中就行。”工人按需放入辣椒,接著從另一個爐口上的小鐵鍋里舀一勺滾燙的豬油,澆在辣椒上,“滋”的一聲,辣椒的香味瞬間彌漫開來。因為這種鐵勺形似小鍋,所以很多三鮮米線也叫“小鍋米線”。
在鎮(zhèn)雄縣城的每一條背街小巷,都能聽到那熟悉的聲音:吃米線的食客們嘴里發(fā)出“呼嚕嚕”的聲音,吃得酣暢淋漓,吃出了屬于鎮(zhèn)雄的獨特味道。
炊煙腌臘醉豆豉
年關將至,白雪爬上山頭,雞犬紛紛歸巢。從上午9時起,炊煙裊裊升起,勾勒出鄉(xiāng)村蓬勃的生機。此時的炊煙,已不僅僅是農(nóng)人埋鍋造飯的煙火氣,還夾雜著鄉(xiāng)村人家熏制臘肉時升起的團團煙霧。
農(nóng)村畜圈里的豬,躲過了臘月初一,卻終究沒躲過臘月十五。那些被喂得白白胖胖的豬,在圈里發(fā)出吃飽喝足后的“哼哼”聲。第二天清晨,主人把柴火燒得旺旺的,大鐵鍋里的熱水“咕嘟咕嘟”地沸騰著。姓張的、姓王的,或是姓周的屠夫,挺直腰板,喊一聲“趕快把豬拖出來,我先宰了,你們慢慢剮毛,弄完了我再過來開膛剖肚”。眾人奔向豬圈,把鐵鉤塞進肥豬的嘴里,一人拉鐵鉤,其余人則在后面揪尾巴、提豬腿、推豬身,三下五除二,肥豬就被抬到了案板上。屠夫把豬宰殺好,隨后把豬肉切成大小均勻的肉塊。吃完“刨湯”,剩下的肉會被熏制成臘肉。
農(nóng)人熏制臘肉的方法雖然簡單,但卻是一件耗時的事。一塊塊經(jīng)過鹽腌制的豬肉被整齊地擺放在灶臺上,灶孔里放入玉米核、干枯的柏樹枝條、松枝條和蘇麻稈。火要燒得很小,讓煙霧一團一團地冒出來,這些煙霧先是在豬肉上縈繞,然后慢慢升向天空。熏上一天,待豬肉表面鋪上一層黑色的塵埃后,主人便將肉收回屋內(nèi)。第二天清晨,主人又重新將肉擺上灶臺,再次生火熏烤。這一次,柴火要添得更旺一些,要看得見火苗。幾個小時后,灶上的豬肉開始流油,主人便要為豬肉翻身,確保每一部分都能得到柴火的熏烤。如此反復熏烤幾遍,直到天黑,臘肉就做成了。熏制好的臘肉呈土黃色,被吊在農(nóng)家屋角的竹竿上,想吃的時候就去取下一坨來。
鎮(zhèn)雄人吃臘肉,喜歡搭配豆豉一起吃。豆豉是用上好的黃豆做成的,剛出袋時會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制作時,農(nóng)人先將黃豆炒至微黃,然后放入溫水中泡上幾個小時,接著用大鍋煮熟。煮好的黃豆放在簸箕里攤開,待水分完全蒸發(fā)后,用一個麻袋裝好,扎緊袋口,放在火爐旁,任由它慢慢發(fā)酵。四五天后,農(nóng)人將發(fā)酵好的豆豉倒入簸箕中,加入辣椒面、鹽、花椒粉,攪拌均勻后,用手捏成一坨一坨的,再用粽葉包裹好,掛在屋角的竹竿上,想吃的時候就去取下一坨來。
豆豉不僅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多種氨基酸,還含有多種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美味芳香、營養(yǎng)豐富、開胃健脾、增加食欲的特點。鎮(zhèn)雄人將豆豉與臘肉一起炒或蒸,香味獨特,令人回味無窮。
鎮(zhèn)雄人走進餐館吃飯,首先必點的就是豆豉炒臘肉或豆豉蒸臘肉。然而,鎮(zhèn)雄人在其他地方,即便采用相同的食材和烹飪方法,也很難做出家鄉(xiāng)的味道。究其原因,或許是異鄉(xiāng)的廚房里,少了那一縷從鎮(zhèn)雄農(nóng)家灶臺升起的炊煙。
箱子街的舌尖非遺傳奇
相傳,在鎮(zhèn)雄縣城的箱子街,有一對母子相依為命,日子靠兒子外出打短工維持。一天,兒子做工時,雇主賞了他一塊豆腐,他舍不得吃,就帶回家孝敬母親。母親捧著兒子帶回來的豆腐,也舍不得吃,就把這塊豆腐煮熱,然后用稻草掩蓋起來,存放在枕頭下,打算等兒子回來時一起吃。過了幾天,兒子回來了,母親高高興興地把豆腐取了出來,打算犒勞辛苦歸家的兒子。誰知她拿出豆腐一看,表面竟長了一層絨毛,還散發(fā)出淡淡的臭味,母親難過得流下眼淚。兒子連忙安慰母親,說自己喜歡吃帶臭味的東西,隨手把豆腐放在火爐上,便去料理家務。不一會兒,簡陋的屋子里散發(fā)出一股奇怪的香味。兒子一看,原來豆腐上的絨毛被烤焦了,變得金黃誘人。他趕緊把另一面翻過來烤。烤好后,他嘗了一口,覺得十分美味,就把剩下的全部都給母親吃。母親邊吃豆腐邊流淚,吃完后對兒子說:“歷來五谷莫亂扔,豆腐也能變黃金。”從那天起,兒子不再外出打短工,而是在家門口支起一個炭爐,做起了把豆腐變成“黃金”的生意。
箱子街是一條窄窄的小巷,長度不過100米。在箱子街,能看見一個個疊放在各家門口的豆腐箱。林家臭豆腐作坊每天總是碼著十幾個空豆腐箱,散發(fā)出一縷縷獨特的味道,征服了整座城市的味蕾。
林家老漢每天都要在陽光下的一口大鍋里浸泡黃豆。待黃豆泡好后,經(jīng)過磨漿、燒毛漿、濾漿、點漿、包豆腐、壓豆腐、剝豆腐等工序,將豆腐切成小拇指厚、半巴掌寬的塊狀,放進豆腐箱,再在上面鋪上一層稻草。裝進箱子里的豆腐,像一個個美麗的蜂房,在小屋里散發(fā)出一股淡淡的霉臭味。發(fā)酵時間一到,還沒等林家老漢開箱查看,就有人連同箱子一起買走。
箱子街邊,每隔一米就擺著一個賣烤臭豆腐的小攤。包著頭巾的大娘站在爐邊,不緊不慢地用小刀在豆腐中間劃開一道小口,舀上一小勺調(diào)好的辣椒面放進去,合攏后遞給坐在火爐邊小木凳上的食客,輕聲說道:“趕緊吃,冷了,味道就散了。”
鎮(zhèn)雄人對臭豆腐濃烈的臭味有著與生俱來的偏愛。少女們穿梭于街巷,一旦衣袂間沾染上豆香與辣香,就會陡然生出吃一塊臭豆腐的念頭。近年來,鎮(zhèn)雄臭豆腐走俏市場,常有四面八方的食客慕名而來。有人靈機一動,將臭豆腐掛到網(wǎng)上,開起了網(wǎng)店。小小的鎮(zhèn)雄臭豆腐,一時“臭名遠揚”,既勾起了更多在外游子的鄉(xiāng)愁,也征服了外地人的味蕾。
箱子街在時光中漸漸老去,但臭豆腐依然排列在那一口口抹了菜籽油的鐵鍋上,高溫煎烙的嗞嗞響聲也不曾散去,那軟綿綿、熱辣辣的舌尖體驗,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食客。

